《漫長的告別》
作者: (美)錢德勒 著,宋碧雲 譯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編輯推薦
 《漫長的告別》
《漫長的告別》雷蒙德·錢德勒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名字之一,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寫入經典文學史冊的偵探小說大師。他的作品被收錄到權威的《美國文庫》中。他是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WA)票選150年偵探小說創作史上最優秀作家中的第一名。
他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編劇之一,他是好萊塢黑色電影的締造者,他與希區柯克、比利·懷爾德、羅伯特·艾特曼等大牌導演合作,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都只能給他當助手。
“雷蒙德·錢德勒是我的崇拜對象。我讀了十幾遍《漫長的告別》。”——村上春樹(2006年村上春樹親自把《漫長的告別》譯成日文出版)
“雷蒙德·錢德勒,每頁都有閃電。”——比利·懷爾德
內容簡介
錢德勒語錄:
我猜我們都是上帝眼中的罪人。
他說:“我始終生活在虛無的邊緣。”
有錢人從來沒有特別想要一樣東西,也許別人的老婆除外。
她突然精神煥發,說道:“噢——到拉斯維加斯?他真多情。那是我們結婚的地方。”我說:“我猜他已經忘了。否則,他寧可到別的地方。”
我目送計程車消失。我回到台階上,走進浴室,把床鋪整個弄亂重新鋪。其中一個枕頭上有一根淺黑色長髮。我的胃裡好像沉著一塊重重的鉛。法國人有一句話形容那種感覺。那些雜種們對任何事都有個說法,而且永遠是對的。告別就是死亡一點點。
作者簡介
錢德勒,他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名字之一,他的作品被收錄到權威的《美國文庫》中。
他是以偵探小說而被載入經典文學史冊的大師。他是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WA)票選150年偵探小說創作史上最優秀作家中的第一名。
他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編劇之一,他與比利·懷爾德合作的《雙重賠償》被稱為黑色電影的教科書。
1942年到1947年,他的4部小說6次被好萊塢搬上銀幕,參與編劇的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似乎至今還沒有哪個作家享受到好萊塢如此的厚愛。
他筆下的馬洛被公認為是最具魅力的男人、“有著黃金般色澤心靈的騎士”,在四十年代,好萊塢男演員以能扮演菲利普·馬洛為榮耀,其中亨弗萊·鮑嘉塑造的最為成功。
他想寫一部“人人都在作品裡無憂無慮地散步”的小說。
他描述自己的性格是“表面的缺乏自信和內里的傲慢自大的不協調的混合物”。
他當過兵,參加過一戰,經歷過苦難與孤獨。認為自己“始終活在虛無的邊緣”。
他不喜歡看大海,因為海里有太多的水和太多淹死的人。
他是個酒鬼。他認為“一個男人,每年至少要酩酊大醉兩次。這是個原則”。
他菸斗從不離嘴。與比利·懷爾德一起編劇,被煙燻得忍無可忍的比利經常跑到廁所里躲避,他竟懷疑比利的生殖器有問題。
他瞧不上海明威。曾在小說里給一個警察起名叫海明威,稱之為“一個老是重複同樣的話,直到讓大家相信那話一定很精彩的傢伙”。
他拒絕任何獎項。假如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他也必定會拒絕。原因有二:一、他不會跑到瑞典去接受獎項,還要穿上晚禮服發表演講;二、諾貝爾獎曾頒給太多的二三流作家,而許多實力遠勝於他們的優秀作家卻未獲獎。
他孤零零地死在異地他鄉。只有17個人參加了他的葬禮。
他說:“我是個沒有家的人……到現在。還是。”
書摘插圖
 《漫長的告別》
《漫長的告別》我第一次看見特里·倫諾克斯時,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輛勞斯萊斯銀色幽靈上。停車場的服務員把車子開出來,一直扶著敞開的車門等著,因為特里·倫諾克斯左腳懸在車外,仿佛已經忘了有這么一條腿。他相貌年輕,卻天生少白頭。你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經醉得一塌糊塗了,除此之外他跟那些穿著晚宴裝、在銷金窟一擲千金的大好青年沒什麼兩樣。
他身邊有一位姑娘,頭髮呈迷人的暗紅色,嘴角掛著淡漠的笑容,肩上披著一件藍貂皮,差一點兒讓勞斯萊斯車黯然失色。當然不至於如此。也不可能。
服務員就是尋常的半吊子小混混兒,身穿白外套,胸前縫有紅色的飯館名字。他一副受夠了的樣子。
“你瞧,先生,”他尖刻地說,“你能不能把腳縮進車裡,好讓我關門?還是我乾脆把門打開,讓你滾下來?”
那個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進他的身體,再從後背透出四英寸來。他根本沒放在心上,一點兒也不驚慌。如果你以為花大把錢打高爾夫球能讓你顯得人格高尚,舞者酒吧雇有一種人專門會戳破你的這種幻覺。
一輛外國敞篷跑車減速掉頭開進停車場,有個男人下了車,用打火機點燃一根長香菸。他身穿套頭格子襯衫、黃色長褲和馬靴,在裊裊煙圈中慢慢走遠,連看都沒看勞斯萊斯一眼,可能覺得平淡無奇吧。在通往露台的階梯前,他停下戴上了一個單眼鏡片。
姑娘突然魅力十足地說:“親愛的,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何不搭計程車到你那兒,把你的敞篷車開出來?今夜沿著海岸開車到蒙蒂塞托一定很棒。我在那邊有幾個熟人正在開池畔舞會。”
白髮青年彬彬有禮地說:“真抱歉,那輛車已經不屬於我了。我不得不把它賣掉。”聽他的口氣和語調,你會以為他只喝橘子水沒喝過酒呢。
“賣了,親愛的?你是什麼意思?”她輕輕挪開,坐得離他遠遠的,但是聲音好像挪得更遠。
“我是說不得不賣。”他說,“為了吃飯錢。”
“噢,我明白了。”語氣冷淡得連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
服務員將白髮青年列為自己可以廁身其中的低收入階層。“喂,夥計,”他說,“我得去停一輛車。改天再見——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放手讓車門盪開。醉漢立即滑下座位,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馬路上。於是我走過去,及時伸出援手。我猜跟酒鬼打交道永遠是一個錯誤。就算他認識你而且喜歡你,還是會隨時出手打你嘴巴一拳。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扶他站起來。
“太謝謝了。”他客客氣氣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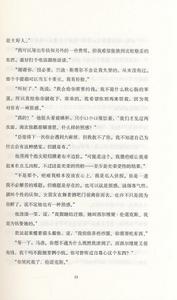 《漫長的告別》
《漫長的告別》“我來把他扶進后座。”我說。
“真抱歉,我赴約要遲到了。”她踩下油門,勞斯萊斯開始滑動。她冷靜地微笑著說:“他只是一條迷路的狗。也許你可以幫他找個家。他能定點大小便——可以這么說。”
勞斯萊斯順著車道開上日落大道,向右轉,就此消失。我正目送她,服務員回來了。我還扶著那個男人,他現在睡得正香。
“這也算是一種做法。”我對白外套說。
“當然。”他冷嘲熱諷地說,“何必為一個酒鬼傷神?他們都麻煩得要命。”
“你認識他?”
“我聽見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則擺在運牛車上我也認不得他。而且我才來兩個禮拜。”
“把我的車子開過來,謝謝。”我把停車券交給他。
等他把我的奧茲莫爾比開過來時,我感覺自己就像扛著一袋鉛。白外套幫我把他扶上前座。貴客睜開一隻眼睛謝謝我們,然後又睡著了。
“他是我見過的最有禮貌的酒鬼。”我對白外套說。
他說:“什麼樣體形、樣貌和舉止的酒鬼都有。他們全都是癟三。看來這一位曾動過整容手術。”
“是啊。”我給他一元小費,他謝謝我。整容的事他說得不錯。我這位新朋友的右半邊臉僵硬,比較白,有幾道細疤,疤痕旁邊的皮膚發亮。他動過整容手術,而且是非常大的手術。
“你打算怎么處置他?”
“帶他回家,讓他醒醒酒,說出他住在什麼地方。”
白外套對我咧嘴一笑,說:“好吧,你這個倒霉催的。要是我,我就把他扔進水溝,儘管走。這些酒膩子只會給別人添麻煩。我對付這些傢伙很有一套。現在競爭這么激烈,人得省點兒力氣,在緊要關頭保護自己。”
“看得出來你從中獲益匪淺。”我說。他先是一副不解的樣子,然後發起脾氣來,但那時候我已上車啟動了。
當然他說的也有點兒道理。特里·倫諾克斯給我惹來好多麻煩。不過這畢竟是我的本行呀。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亞卡大道一幢山坡上的小房子裡,位於一條死巷的盡頭,前門有長長的紅木台階,對面有個小尤加利樹林。房子帶著家具,屋主是一位婦人,目前到愛達荷州孀居的女兒家暫住去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為屋主希望能隨時一通知就搬回來住,一半是因為那些台階。她年歲漸大,實在受不了每次回家都得面對長長的台階。
我總算把酒鬼扶上了台階。他很想幫忙,但兩條腿像橡皮做的一樣不聽使喚,抱歉的話說到一半他就睡著了。我開了門,把他拖進屋內。他癱在長沙發上,我給他蓋了一條毯子,讓他繼續睡。他打鼾打了一個鐘頭,鼾聲就像大海豚發出的。然後他突然醒來,要上廁所。如廁出來後,他斜著眼睛偷看我,想知道他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他。他自稱特里·倫諾克斯,住在韋斯特伍德,家裡沒人給他留門。他的聲音響亮而清楚。
他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我端出來,他小心翼翼地端著托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會在這兒?”他四處張望。
“你在舞者酒吧門外醉倒在一輛勞斯萊斯車上。女朋友丟下你走了。”
“不錯,”他說,“她百分之百占理。”
“你是英國人?”
“我在那兒住過,不過不是在那兒出生的。如果能叫到計程車,我馬上走。”
“有輛現成的車在等著。”
他自己走下台階。前往韋斯特伍德的路上他沒多少話,只是向我致謝,還抱歉自己這么惹人嫌。他可能對很多人說過很多次這種話,順嘴就溜出來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悶,一點兒溫馨的感覺都沒有,如果以為他是那天下午才搬進去的也不為過。綠色硬沙發前的茶几上有一個半空的蘇格蘭威士忌酒瓶、一碗融化的冰、三個空汽水瓶和兩隻玻璃杯,玻璃菸灰缸堆滿了菸蒂,有些沾著口紅印,有些沒有。屋裡沒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這問房子應該是租來開會或餞別、喝幾杯聊聊天、睡睡覺的旅館房間,不像人長住的地方。
他請我喝一杯,我謝絕了。我沒多待。我走前他又謝了我幾句,那種感謝的程度既不像我曾為他兩肋插刀,也不像我什麼都沒有為他做過,就是那種說沒有也有,說有但不明顯的樣子。他有點兒戰慄,有點兒害羞,卻客氣得要命。他站在敞開的門口,等電梯上來,我進了電梯。不管他有什麼缺點,他至少很有禮貌。
他沒再提那位姑娘,也不提自己沒有工作,沒有前途,最後一張鈔票已為一個高級蕩婦付了舞者酒吧的賬,而她競不能多逗留一會兒,確保他不會被巡邏警察關進牢房,或者被一個粗暴的計程車司機捲走,甩到外面的空地去。
搭電梯下樓時,我恨不得回樓上搶走他那瓶蘇格蘭威士忌。但事不關己,而且不會有用的。酒鬼想喝,總會想法子弄到酒。
我咬著嘴唇開車回家。我算是硬漢,可是這個人有讓我動心的地方。除了白髮、疤痕臉、響亮的聲音和彬彬有禮的態度,我不知道是什麼。也許這幾點就夠了。我再見到他的可能性不大。正如那位姑娘所說的,他只是一條迷路的狗。
2
我再次見到他,是感恩節後的那個禮拜。好萊塢大道沿線的店鋪已經開始擺出定價過高的聖誕節禮物,報紙開始天天疾呼:如果你不早點兒採購聖誕節商品,情況會很可怕。其實,不管怎么樣都很可怕。向來如此。
在離我那棟辦公大樓大約幾條街的地方,我看見一輛警車並排停車,車上的兩個警察正瞪著人行道上一家店鋪櫥窗邊的什麼。目標原來是特里‘倫諾克斯——不如說是他的肉身——他看來實在不雅觀。
他倚著一家店鋪的門面。他不得不倚著點兒什麼東西。他的襯衫髒乎乎的,領口敞開,有一半垂在夾克外面。他已經四五天沒刮鬍子了,鼻子皺著,皮膚慘白,臉上長長的細疤幾乎看不出來,眼睛像雪堆里的兩個洞。巡邏警車上的兩個警察顯然正打算動手抓他,於是我快步走過去,抓住他的胳臂。
“站直,往前走。”我做出粗暴的樣子,並從側面向他眨眨眼。“辦得到嗎?你是不是喝醉了?”
他茫茫然看了我一眼,露出他特有的半邊微笑,吸口氣說:“我剛才醉了。我猜我現在只是有一點兒——空虛。”
“好吧,抬腳走路。你眼看就要被抓進醉漢牢房了。”
他努力抬起腳,讓我扶他穿過人行道上的遊民,來到護欄邊。那邊停著計程車,我拉開車門。
“他先。”司機用大拇指指指前面的計程車。他轉過頭來,看見了特里。“如果他肯去的話。”他說。
“情況緊急。我的朋友病了。”
“是啊。”司機說,“他到別的地方也照病不誤。”
“五塊錢,”我說,“讓我們看看那美麗的笑臉。”
“那,好吧。”他說著把一本封面有火星人的雜誌塞到鏡子後面。我伸手從裡面打開門,把特里·倫諾克斯弄上車,警察巡邏車的陰影遮住了另一側的車窗。一位白髮警員下車走過來。我繞過計程車,迎上前去。
“等一下,麥克。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這個衣服髒乎乎的先生真是你的密友嗎?”
“對我來說足夠親密啦,我知道他需要朋友。他沒醉。”
“一定是為了錢。”警察說。他伸出手來,我把執照放在他手上。他看了看,遞迴來。“喔——喔,”他說,“原來是私人偵探來撿客戶呢。”他語氣變得很不友好。“馬洛先生,執照上寫了你的一些資料。他呢?”
“他叫特里·倫諾克斯,在電影公司工作。”
“不錯嘛。”他探頭到計程車內,仔細看坐在一角的特里。“我敢說他最近這一段時間沒有工作過;我敢說他最近這段時間沒有在屋裡睡過覺;我甚至敢說他是個無賴。我們該逮捕他。”
“你不會沒抓過幾個人吧?”我說,“在好萊塢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望著車上的特里,問:“你那位朋友叫什麼名字,老兄?”
特里慢慢地說:“菲利普·馬洛。他住在月桂谷亞卡大道。”
警察把腦袋由視窗縮回來,轉身做了個手勢,說:“可能你剛剛才告訴他的。”
“有可能,但是我沒有。”
他盯著我一兩秒鐘,說:“這回我信你一次。可是你把他弄走,別在街上混。”他上了警車,絕塵而去。
我上了計程車,走了三條街遠,到停車場換乘我的車。我拿出五美元鈔票給計程車司機。他面部僵硬地看了我一眼,搖搖頭。
“照表算就行了,如果你願意,給個一塊錢整數也可以。我也落魄過。在番市。沒有計程車肯載我。鐵石心腸的城市。”
“舊金山。”我不由自主地說。
“我叫它番市。”他說,“去他的少數族裔。謝了。”他接下一塊錢鈔票,把車開走了。
我們來到一家免下車餐館,裡面做的漢堡不像別家那樣連狗都不肯吃。我讓特里·倫諾克斯吃了兩個漢堡,喝了一瓶啤酒,然後帶他回家。他爬台階還是很吃力,但他咧著嘴笑,氣喘吁吁地往上爬。一個鐘頭後,他剃過鬍子,洗過澡,看起來又像正常人了。我們坐下來喝了一杯很淡的調和酒。
“幸虧你記得我的名字。”我說。
“我特意記的。”他說,“我還查了你的資料。這個事情我還是能做到的。”
“何不打個電話給我呢?我一直住在這裡。我還有個辦公室。”
“我何必打擾你?”
“看樣子你有必要打擾別人。看樣子你的朋友不多。”
他說:“噢,我有朋友,某一類的。”他轉動著茶几上的玻璃杯。“向人求援並不容易——何況一切都怪自己不好。”他抬頭露出疲憊的笑容。“也許有一天我會戒酒。他們都這么說,對吧?”
“要花三年左右的時間。”
“三年?”他顯得很震驚。
“通常要。那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你必須習慣色彩變得黯淡,聲音微弱下來。你必須酌情留出復發的空間。所有你以前熟識的人都會變得有點兒陌生。你甚至會不喜歡大部分老朋友,他們也不會太喜歡你。”
“那不算多大的改變,”他說,回頭看看鐘。“我有個價值兩百美元的手提箱寄放在好萊塢公車站。如果能保出來,我可以買個便宜貨,把現在寄放的那個當了,換一筆路費搭車到拉斯維加斯。我在那邊可以找到工作。”
我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點頭,坐在一旁慢慢喝我的酒。
“你在想我早該有這個念頭。”他平靜地說。
“我在想其中必有文章,但不關我的事。工作是有把握,還是只有希望而已?”
“有把握。我的軍中密友在那兒開了一家大俱樂部,泥龜俱樂部。當然啦,他可能算是地痞流氓,他們都是——另一方面卻又是大好人。”
“我可以籌出車錢和另外的一些費用。但我希望能換到比較穩妥的東西。最好打個電話跟他談談。”
“謝謝你,沒必要。蘭迪·斯塔爾不會讓我失望的。從來沒有過。那個手提箱可以當五十美元。我有經驗。”
“聽好了,”我說,“我會給你需要的錢。我不是什麼軟心腸的笨蛋。所以我給你你就收下,乖乖的。我希望你別再來煩我,因為我對你有一種預感。”
“真的?”他低頭看玻璃杯,只小口小口啜飲著。“我們才見過兩次面,兩次你都很夠意思。什麼樣的預感?”
“總覺得下一次你會遇到大麻煩,但我救不了你。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但就是有。”
他用兩個指尖輕輕摸著右半邊臉。“可能是這個。我猜疤痕讓我看起來有點兒兇相。不過這是光榮的傷疤——至少是光榮受傷的結果。”
“不是那個。疤痕我根本沒放在心上。我是私人偵探。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難題。但難題是存在的。也可以說是預感。說得客氣些,就叫個性的認知。女朋友在舞者酒吧門前離你而去,也許不只是因為你醉了。說不定她也有一種預感。”
他淡淡一笑,說:“我跟她結過婚。她叫西爾維婭.倫諾克斯。我是為錢娶她的。”
我站起來蹙著眉頭看他,說:“我給你弄些炒蛋。你需要吃東西。”
“等一下,馬洛。你想不通為什麼既然我潦倒了,而西爾維婭又很有錢,我幹嗎不跟她要倆小錢。你可曾聽過自尊心這個東西?”
“你笑死我了,倫諾克斯。”
同名影片概述
 中文片名:漫長的告別
中文片名:漫長的告別外文片名:Dolgie provody
導演:Kira Muratova
主演:
類 型:動作
首映日期:1987-01-01
所屬分類:歐美動作
日劇
中文名:漫長的告別集數:5
片長:58分鐘
類型:懸疑
導演:堀切園健太郎
編劇:渡辺あや/雷蒙德·錢德勒(原作)
國家:日本
首映:2014年4月19日
劇情介紹
2014年NHK春日劇《漫長的告別》決定。該劇發生在50年代中期的東京,出道25年的淺野忠信首次出演電視劇,擔當私家偵探一角。改編自硬漢派小說家雷蒙德·錢德勒原作,堀切園健太郎執導。編劇渡邊彩自《康乃馨》時隔2年後再出山。配樂則邀請大熱的大友良英擔當分享者影視。綾野剛、小雪、古田新太、太田莉菜等共演。女演員原田志津香的丈夫保因殺妻嫌疑逃往台灣自殺。保的好友私家偵探增澤磐二對他的死心存疑問,但這一案件卻被當時在媒體中擁有廣泛影響力的掌權者原田平藏暗中掩蓋。其後,磐二和原田家的鄰居,酗酒小說家上井戶讓治、出版社編輯等一同被捲入了一樁事件中,並最終追查到了掌握著案件關鍵的美女亞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