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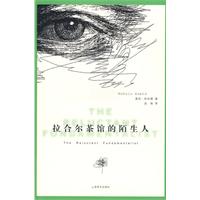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全球22個國家和地區聯袂推出的國際暢銷書。顛覆一代青年“美國夢”的黑色懸疑小說《紐約時報》、《出版家周刊》年度好書英國文學大獎布克獎決選作品。
多倫多《環球郵報》、悉尼《晨報》年度好書《紐約客》、《巴黎評論》、《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力薦文學佳作堪比加繆《墮落》和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諷喻小說。
在拉合爾一家茶館的桌邊,一位滿臉絡腮鬍的巴基斯坦男子與一位不安的陌生美國人交談著。從午後到黃昏再到深夜,巴基斯坦男子講述著他自己的故事,正是這個故事使他們如同命運安排好的一般在此相逢……
昌蓋茲從巴基斯坦來到美國尋夢。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的他成績優異,在班上名列榜首,畢業時被極富盛名的評估行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一眼相中。充滿活力的紐約使他如魚得水,與氣質優雅、容貌出眾的艾麗卡之間漸漸綻放的戀情更使他看到了踏入曼哈頓上流社會的希望,而這樣的財富和地位正是他自己的家族當年在拉合爾曾經享有過的。孰料,隨著911事件的爆發,昌蓋茲發現他在紐約這個他所棲身的城市中的地位急轉直下,而他與艾麗卡的戀情也隨著艾麗卡心中被喚醒的舊日傷痛而從指縫中流走。昌蓋茲對自己身份的感知經受著巨大的震撼,對祖國的忠誠漸漸超越了金錢、權力,甚至愛情。
內容簡介
這本由莫欣·哈米德花費六年心血幾經修改創作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通過一位巴基斯坦男子在茶館向一位美國男性遊客講述自己在美國的經歷,來展現和揭露了美國社會金玉其身卻弊病累累的現實,這當然體現在其遭受9·11恐怖事件後所作出的反映。一個學業出類拔萃且在一流團體中風頭強勁的年青人,本來前途無量,卻因為這次恐怖事件後,在身處的這個社會環境中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身份,那種孤立無援致使其一度迷失自我。是繼續為這個學習工作生活了十幾年的國家“奴役制”的打工,還是回到祖國與親人同心攜力來抵禦炮彈的襲擊?這顯然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必選題,尤其是要面對這個既是
作者簡介
莫欣·哈米德(1971-),出生於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爾,後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公共與國際事務,畢業後入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一九九七年獲得法律博士學位。之後在紐約曼哈頓的財務管理公司擔任管理顧問。現居倫敦。二○○○年出版處女作《蛾煙》(MothSmoke),獲得貝蒂·特拉斯克獎併入圍美國筆會海明威文學獎,被《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好書。二○○七年出版《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入圍布克獎最終決選。
寫作背景
這本書的內容,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巴基斯坦青年追尋美國夢而最終破滅的經歷。要知道,美國文學史上以批判美國夢為主題的作品中最偉大的就得數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了。然而與這本描寫同一主題的經典之作相比,作者在思考的廣度上顯然有了新的突破。這其實也是時代的變化使然。爵士樂時代的美國還只是關起門來紙醉金迷,而世紀之交的美國已經揮舞著大棒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憑藉著雄厚的綜合實力,美國在各個領域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於是,以追求個人成功為核心內容的美國夢不僅依然是美國青年人的夢想,還隨著美國對其文化與價值觀的推銷,大踏步地走出國門,成為了全球無數年輕人,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年輕人追求的目標。眼下,每年都有許多第三世界的年輕人到歐美已開發國家去留學,去追尋成功的夢想。有人成功了,有人失敗了,失敗的總是多些,這是常理。但即便有很多人失敗了,也總會有更多的人前仆後繼,繼續追夢。失敗的人要么怪自己時乖運蹇,要么怨社會競爭激烈,卻很少有人對自己追求的這個夢想進行深刻的思考。然而,這樣的思考與批判究竟該由怎樣身份的人來進行才能取得最佳的批判效果呢?這裡,人們似乎面臨了一個“測不準定理”的悖論。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對美國夢的追求而對其進行批判,則一來沒有深刻的身心體驗,二來也難逃空洞說教的嫌疑,難以服人。然而一旦親身涉入其間,再想要保持批判距離又談何容易?姑且不論有的人根本就因此而喪失了客觀公正地進行批判的能力,即便他還能夠進行批評,旁人又會怎樣看待他的批評呢?追夢失敗的人如果對夢想發表批評,旁人會覺得他有酸葡萄情結;而功成名就的人的批評,又會令人覺得他得了便宜還賣乖。由是看來,只有一種人能承擔起這樣的批評重任,那就是先取得成功,為自己贏取話語權,再選擇放棄或與這種狀態刻意保持疏離。這樣一想,覺得菲茨傑拉德還真是偉大,一面自己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一面還能像潛伏在自己生活中的臥底那樣向外人提供清晰準確的情報。難怪世紀之交時,美國人評選二十世紀百部最偉大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能高居第二呢。莫欣·哈米德扮演的顯然也是這樣一種從內部對某種文化給予批判的角色。然而比菲茨傑拉德更具優勢的是他畢竟有著異族的身份,這使得他在批判美國夢時可以從外部獲得更多的力量。表現在小說里就是昌蓋茲一度志得意滿,以為自己融入了紐約,融入了美國的主流社會,他在到馬尼拉出差時對當地人也幾乎以美國人自居了,但他的這種地位與純正的白種美國人相比要不穩定得多,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其與後者之間的鴻溝凸顯無遺。無論是從自己的家人,還是從同為第三世界人士的智利老人胡安·巴蒂斯塔那裡,他都獲得了批判所需的參照系和外部力量,這些最終促成了他對美國夢的批判,也在心靈上完成了對自己文化身份的回歸。與莫欣·哈米德和昌蓋茲相比,無論是現實中的菲茨傑拉德還是小說中的蓋茨比都要更為不幸,他們在夢醒之後也無處逃逸,等待他們的只有徹底的沉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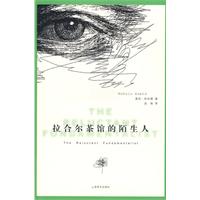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
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