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我那遙遠的清平灣》,短篇小說,當代著名作家史鐵生著。在文章中,作者用平實而浪漫的筆法描繪了一幅令人憧憬的插隊生活的畫卷,並從清平灣這片古老而貧瘠的土地中,發掘出了整個民族生存的底蘊。本文感情深厚,娓娓敘來,令人回味無窮。
小說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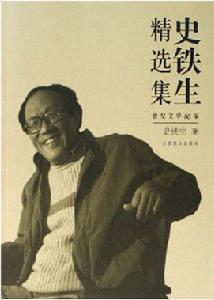 史鐵生著作
史鐵生著作北方的黃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川牛和南陽牛最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華北牛和蒙古牛雜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彎去,頂架也厲害,而且皮實、好養。對北方的黃牛,我多少懂一點。這么說吧:現在要是有誰想買牛,我擔保能給他挑頭好的。看體形,看牙口,看精神兒,這誰都知道;光憑這些也許能挑到一頭不壞的,可未必能挑到一頭真正的好牛。關鍵是得看脾氣,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聲,好牛就會瞪圓了眼睛,左蹦右跳。這樣的牛乾起活來下死勁,走得歡。疲牛呢?聽見鞭子響準是把腰往下一塌,閉一下眼睛。忍了。這樣的牛,別要。我插隊的時候餵過兩年牛,那是在陝北的一個小山村兒——清平灣。
我們那個地方雖然也還算是黃土高原,卻只有黃土,見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於洪水年年吞噬,塬地總在塌方,順著溝、渠、小河,流進了黃河。從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黃的山峁或一道道黃的山樑,綿延不斷。樹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幾棵什麼樹,老鄉們都記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時候,才放倒一、兩棵。碗口粗的柏樹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誰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兒就都佩服,方圓幾十里內都會傳開。
在山上攔牛的時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黃土山都是谷堆、麥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溝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樹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總是“唏溜唏溜”地抽著旱菸,笑笑說:“那可就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材。”
秋天,在山裡攔牛簡直是一種享受。莊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禿禿的,山窪、溝掌里的荒草卻長得茂盛。把牛往溝里一轟,可以躺在溝門上睡覺;或是把牛趕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書。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單調:半崖上小灌木的葉子紅了,杜梨樹的葉子黃了,酸棗棵子綴滿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棗……尤其是山坡上綻開了一叢叢野花,淡藍色的,一叢挨著一叢,霧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從黃土坷垃後面探頭探腦;野鴿子從懸崖上的洞裡鑽出來,“撲楞楞”飛上天;野雞“咕咕嘎嘎”地叫,時而出現在崖頂上,時而又鑽進了草叢……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沒人逮食這些小動物。也許是因為沒有槍,也許是因為這些鳥太小也太少,不過多半還是因為別的。譬如:春天燕子飛來時,家家都把窗戶打開,希望燕子到窯里來作窩;很多家窯里都住著一窩燕兒,沒人傷害它們。誰要是說燕子的肉也能吃,老鄉們就會露出驚訝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兒嘛!”仿佛那無異於褻瀆了神靈。
種完了麥子,牛就都閒下了,我和破老漢整天在山裡攔牛。老漢閒不著,把牛趕到地方,跟我交待幾句就不見了。有時忽然見他出現在半崖上,奮力地劈砍著一棵小灌木。吃的難,燒的也難,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懸崖。老漢說,過去不是這樣,過去人少,山裡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鑽不進去。老人們最懷戀的是紅軍剛到陝北的時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單幹。“老紅了⑿那陣兒,吃也有得吃,燒也有得燒,這咋會兒,做過啦⒀!”老鄉們都這么說。真是,“這咋會兒”,迷信活動倒死灰復燃。有一回,傳說從黃河東來了神神,有些老鄉到十幾里外的一個破廟去禱告,許願。破老漢不去。我問他為什麼,他皺著眉頭不說,又哼哼起《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那是才紅了那陣兒的歌。過了半天,使勁磕磕菸袋鍋,嘆了口氣:“都是那號婆姨鬧的!”“哪號?”我有點明知故問。他用菸袋指指天,搖搖頭,撇撇嘴:“那號婆姨,我一照就曉得……”如此算來,破老漢反“四人幫”要比“四·五”運動早好幾年呢!
在山裡,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個人,也並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著那些牛,它們的一舉一動都意味著什麼,我全懂。平時,牛不愛叫,只有奶著犢子的生牛才愛叫。太陽偏西,奶著犢兒的生牛就急著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讓它回,它就“哞——哞——”地叫個不停,急得團團轉,無心再吃草。
“不,不是這。”破老漢說,“那一年村裡的牛死的死,殺的殺(他沒說是那年),快光了。全憑好歹留下來的這頭黑牛和那頭老生牛,村裡的牛才又多起來。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運吧!”破老漢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對它分外敬重。“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漢說。可是,老黑牛最終還是被人拖到河灘上殺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斷了腿。牛被殺的時候要流淚,是真的。只有破老漢和我沒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處處飄著肉香。老漢呆坐在老黑牛空蕩蕩的槽前,只是一個勁抽菸。
我至今還記得這么件事:有天夜裡,我幾次起來給牛添草,都發現老黑牛站著,不臥下。別的牛都累得早早地臥下睡了,只有它喘著粗氣,站著。我以為它病了。走進牛棚,摸摸它的耳朵,這才發現,在它肚皮底下臥著一隻牛不老。小牛犢正睡得香,響著均勻的鼾聲。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臥下,就會把小牛犢壓壞。我把小牛犢趕開(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聲臥倒了。它看著我,我看著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誰應該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勁兒了,回到北京不久,兩條腿都開始萎縮。
鑑賞
經歷過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們中間,湧現出了一批善於反思、勤于思考的作家,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值得記載,頗有建樹的新文學流派——知青文學。其中有以描寫知青為主體的《今夜有暴風雪》、《蹉跎歲月》等,以其轟轟烈烈、悲悲愴愴的效果憾動人心。寫出了這些動盪年代中的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精神與肉體的衝撞中的迷惘、苦悶、執著等多種心態,對這場波及全國,使千千萬萬人投身其中的運動進行了藝術的闡釋。與此同時,另一些從這條路上走過的人們,把視角轉向了他們曾經灑過汗水和淚水的那片土地上至今仍默默生存著的人們,而將知青作為媒介,從他們的眼中觀察這片古老而貧瘠的土地,發掘出了整個民族生存的底蘊。從而將知青文學的觸角探伸得更遠,使這一部分的創作在經歷了重複的危機之後又寫出了新意,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史鐵生這篇《我那遙遠的清平灣》就是跳出了以往的舊框子,經過十年的積澱,終於將這些不能忘卻的記憶寫出來。正如史鐵生所說,刻意想寫插隊的生活,編排了一些情節,反到弄巧成拙,被人懷疑他是否插過隊。“倒是每每說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的人都聽得入神、感動;說到最後,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恩”。或許這就是生活的真實中所蘊藏的藝術的美感吧?作者雖將小說取名為“遙遠的清平灣”,但讀罷令人感到,清平灣實在並不遙遠,它就在作者的心裡,在讀者的眼前。那一道道的黃土高坡,那一群群慢慢行進的牛群,那一孔孔窯洞中住著的婆姨娃娃,那整天價唱個不停的破老漢,都讓人覺得那么親近,甚至嗅到了那裡的黃土味兒。破老漢是個為新中國的建立出過力的人,他曾跟著隊伍一直打到廣州,若不是戀著家鄉的窯洞,他就不是現在這個撅一很樹枝趕著牛,走一路唱一路的破老漢了,也不會讓他的留小兒吃不上白肉,穿不上條絨襖了。這些當年老革命根據地的鄉親們仍過著窮日子,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棺材。”留小兒羨慕城裡人啥時想吃肉就吃,不明白為什麼北京人不愛吃白肉。難得熱鬧一回的事情就是兩個瞎子來說書,雖然把李玉和、伍子胥、主席語錄、姜太公都攪到一塊兒,什麼也聽不清楚,可人們還是愛聽那調調,喜歡那個氣氛。陝北說書是彈著三弦、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訴,人們就被這調調吸引了,似乎抒發了胸中那么一股子悶氣。作者用充滿感情的筆觸寫了陝北的古風。那裡保留著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承襲著勤勞質樸的品德,人們沒有過多的奢望和要求,心裡熬煎得受不住了,就放開嗓門唱一段。用他們的話說“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陝北的民歌都有一種憂傷的調子,什麼時候才唱得紅紅火火、快快活活的呢?這是讓讀者深思的問題。破老漢不是那種混混沌沌、只知幹活吃飯睏覺的老式農民,他懷念當年紅軍到陝北的日子,曉得現今上頭的事“都是那號婆姨鬧的!”他將所想所思,所煩所惱還有所愛所戀,都變成了一曲曲《信天游》,時不時的就哼上一兩句,人也就變得快活一些兒。十年過去,留小兒——這黃土高原的新一代,能攢夠了盤纏上北京,還給爺爺買了一把新二胡。日子好過了,破老漢還是成天價瞎唱,大概這調調要一直唱到老吧?它已變成了破老漢思想的代言者了。讀罷全篇,仍覺耳邊迴蕩著破老漢唱出的民歌,那調兒是深沉的、厚重的,有一份悲哀也有一份雄渾。那裡的土地和那裡的人民,就像小說里寫到的老黑牛一樣,為了讓臥在身下熟睡的小牛犢睡得更香甜,在勞累了一天之後,仍然掙扎著喘著粗氣站立著。這就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脊樑。
史鐵生拋掉了個人的苦悶和感傷,從清平灣那些平凡的農民身上看到了美好、純樸的情感,看到了他們從苦難中自尋其樂的精神寄託,看到了堅韌不拔的毅力和頑強的生命力。使那些還沉湎在個人創傷中,咀嚼著生活曾一度帶給他們的苦果,將那場運動單純地視為煉獄般的苦難的知青們,從舊日的傷口上面抬起頭來,思考一下生活的錘鍊畢竟還留給我們一些別人永遠無法悟到的真諦;為那些祖祖輩輩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幾億農民想想,我們是否應該為此做些什麼?即使有些遙遠。這就是史鐵生的清平灣帶給我們的一些聯想。
人物形象
破老漢是個為新中國的建立出過力的人,他曾跟著隊伍一直打到廣州,若不是戀著家鄉的窯洞,他就不是現在這個撅一根樹枝趕著牛,走一路唱一路的破老漢了,也不會讓他的留小兒吃不上白肉,穿不上條絨襖了。這些當年老革命根據地的鄉親們仍過著窮日子,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一股勁兒吃白饃饃了。老漢兒家、老婆兒家都睡一口好棺材。“留小兒羨慕城裡人啥時想吃肉就吃,不明白為什麼北京人不愛吃白肉。
難得熱鬧一回的事情就是兩個瞎子來說書,雖然把李玉和、伍子胥、主席語錄、姜太公都攪到一塊兒,什麼也聽不清楚,可人們還是愛聽那調調,喜歡那個氣氛。陝北說書是彈著三弦、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訴,人們就就這調調吸引了,似乎抒發了胸中那么一股子悶氣。作者用充滿感情的筆觸寫了陝北的古風。那裡保留著2000 多年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奉襲著勤勞質樸的品德,人們沒有過多的奢望和要求,心裡熬煎得受不住了,就放開嗓門唱一段。用他們的話說”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陝北的民歌都有一種憂傷的調子,什麼時候才唱得紅紅火火、快快活活的呢?這是讓讀者深思的問題。破老漢不是那種混混沌沌、只知幹活吃飯睏覺的老式農民,他懷念當年紅軍到陝北的日子,曉得現今上頭的事”都是那號婆姨鬧的!“他將所想所思,所煩所惱還有所愛所戀,都變成了一曲曲《信天游》,時不時的就哼上一兩句,人也就變得快活一些兒。十年過去,留小兒--這黃土高原的新一代,能攢夠了盤纏上北京,還給爺爺買了一把新二胡。日子好過了,破老漢還是成天價瞎唱,大概這調調要一直唱到老吧?它已變成了破老漢思想的代言者了。
讀罷全篇,仍覺耳邊迴蕩著破老漢唱出的民歌,那調兒是深沉的、厚重的,有一份悲哀也有一份雄渾。那裡的土地和那裡的人民,就像小說里寫到的老黑牛一樣,為了讓臥在身下熟睡的小牛犢睡得更香甜,在勞累了一天之後,仍然掙扎著喘著粗氣站立著。這就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脊樑。史鐵生拋掉了個人的苦悶和感傷,從清平灣那些平凡的農民身上看到了美好、純樸的情感,看到了他們從苦難中自尋其樂的精神寄託,看到了堅韌不拔的毅力和頑強的生命力。使那些還沉湎在個人創傷中,咀嚼著生活曾一度帶給他們的苦果,將那場運動單純地視為煉獄般的苦難的知青們,從舊日的傷口上面抬起頭來,思考一下生活的錘鍊畢竟還留給我們一些別人永遠無法悟到的真諦,為那些祖祖輩輩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幾億農民想想,我們是否應該為此做些什麼?即使有些遙遠。這就是史鐵生的清平灣帶給我們的一些聯想。
獲得獎項
《我那遙遠的清平灣》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作者
 史鐵生
史鐵生簡介
史鐵生(1951-),北京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思想家。1958年如北京市東城區王大人國小讀書,1967年畢業已清華附中國中部。而後,於1969年到陝北延安地區“插隊”。三年後因雙腿癱瘓回到北京,在北新橋街道工廠工作,後因病情加重回家療養。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
生平
史鐵生七歲上國小,十三歲上中學,國中二年未盡文化革命開始,自此與上學無緣。十八歲時上山下鄉運動展開,自願去陝北農村插隊,種一年地,餵兩年牛,衣既不豐食且難足,與農民過一樣的日子,才見了一個全面的中國。三年後雙腿癱瘓,轉回北京;住院一年有半,治療結束之時即輪椅生涯開始之日。身殘志且不堅,幾度盼念死神,幸有親人好友愛護備至,又得幽默大師卓別林指點迷律,方信死是一件最不必急於成的事。二十三歲到一家街道工廠做臨時工,七年。工余自學英語,但口譯、筆譯均告無門,徹底忘光。又學畫彩蛋,終非興趣所在,半途而廢。然後想起了寫作。據說不能四處去深入生活者,操此行當無異自取滅亡,雖心中憂恐,一時也就不顧。莽莽撞撞走上寫作這條路,算來已近載,雖時感力不從心,但“上賊船容易不賊船難”,況且於生命之河上漂泊,好歹總是要有條船。三十歲上舊病殃及雙腎,不能勝任街道工廠的工作,謝職回家。一九七九年後相繼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命若琴弦》《我與地壇》《務虛筆記》等小說與散文發表。一九九八年終致尿毒症,隔日“透析”至今。“透析”後有隨筆集《病隙碎筆》和散文集《記憶與印象》出版。作品多次獲獎。現為北京作協契約製作家。
評價
史鐵生是當代中國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寫作與他的生命完全同構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寫作之夜”,史鐵生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他的《病隙碎筆》作為二OO二年度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收穫,一如既往地思考著生與死、殘缺與愛情、苦難與信仰、寫作與藝術等重大問題,並解答了“我”如何在場、如何活出意義來這些普遍性的精神難題。當多數作家在消費主義時代里放棄面對人的基本狀況時,史鐵生卻居住在自己的內心,仍舊苦苦追索人之為人的價值和光輝,仍舊堅定地向存在的荒涼地帶進發,堅定地與未明事物作鬥爭,這種勇氣和執著,深深地喚起了我們對自身所處境遇的警醒和關懷。
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我與地壇》、《秋天的懷念》、《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隊的故事》、《務虛筆記》、《法學教授及其夫人》、《老屋小記》、《奶奶的星星》、《來到人間》、《合歡樹》、《病隙碎筆》、《命若琴弦》、《原罪·宿命》、《鐘聲》、《我的丁一之旅》、《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猜法》、《中篇1或短篇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