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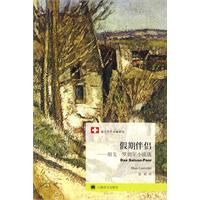 封面
封面瑞士作家胡戈·羅切爾(HugoLoetscher, 1929-2009),生於蘇黎世一個機械師之家,曾在蘇黎世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哲學、社會學和文學,195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早年在報社和雜誌社擔任文學評論員和文學編輯。1969年起成為自由職業作家。1986-1989年,羅切爾擔任瑞士作家協會主席,並任職達姆施塔特德國語言與文學創作研究院。
羅切爾著有長篇小說《污水》、《編花圈的女工》、《挪亞》等;短篇小說集《洗衣房的鑰匙》,《有免疫力的人》、《蒼蠅和湯》、《駝背》等;文藝短評集《閱讀而非攀登》;詩集《曾有這樣一個世界》。羅切爾以精湛的文學創作榮獲康拉德·費迪南德·邁耶爾獎(1966)、蘇黎世市頒發的文學獎(1972)、席勒獎(1985),瑞士席勒基金會頒發的偉大席勒獎(1992)等。
作品簡介
本書由13則短篇小說組成。
《洗衣房的鑰匙》,在獨具匠心的故事情節中,一把洗衣房的鑰匙不單單只是一件開門的工具,更是一種行使“房主”權力的標誌;作者用一把普通的洗衣房鑰匙打開了瑞士人保守而隱秘的內心世界。
《第三十八號工蟻》、《蒼蠅和湯》、《金魚、貓、狗、青蛙和鸛》選自短篇小說集《蒼蠅和湯,以及33個情景中的其他33種動物》,小說對動物體態、技能和生存環境細緻入微的觀察,惟妙惟肖的描寫,細膩感人的情懷,別具一格的構思,無不令人動容。每個動物的故事都是一則深刻的現實寓言,隱含著強大的道德助推力。
《枕頭鵝——叔叔講給小侄女的晚安故事》選自自傳體短篇小說集《有免疫力的人》,小說以無暇的想像素描了一幅淒涼唯美的畫面:一隻被人類拔光了毛的醜鵝,被神奇般地賦予了想像的翅膀,於是它便再次振翅高飛,翱翔天空,將愛灑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令讀者感受到淒涼的悲愴和溫暖的震撼。選自該小說集的代表作還有《重重幕簾》、《母親的長柄勺》、《離開這裡,沿著亞馬遜河順流而上》。
《駝背》、《上校》、《假期伴侶》均選自小說集《駝背》,講述了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忍辱負重的“侏儒”、渾渾噩噩的醉鬼“上校”、情不投意不合的“假期伴侶”等,為深陷認同危機的後現代社會繪製了一幅萎靡蹉跎的人物畫卷。同樣選自該小說集的《樓管的謀殺計畫》是一部出色的謀殺欲念小說,講述了一位普通的樓管員處心積慮、一心想幹掉鄰居房客施奈貝利、卻最終反遭暗算的一則極具諷刺意味的兇殺故事。
《清朝官員的眼睛》節選自同名長篇小說,小說虛擬了一位清朝官員與歐洲人帕斯特之間跨時代、跨地域的對話,文化間的交融與差異不禁發人深思。
書評
讀《假期伴侶》
書中譯者序所言:這是一位充滿世界性情懷的作家,他的思考與文字所指,其廣度與深度不受國界限制。瑞士人說:“瑞士之所以成為瑞士,是因為有些德意志人不願做德國人;有些法蘭西人不願做法國人;有些義大利人不願做義大利人。”這樣的瑞士產生羅切爾這樣視野開闊的作家理所當然。長篇小說首先需要的是耐心與體力,而短篇小說成功的關鍵則在於智力,這包括洞察力、敏捷性、直感,以及更熟練的語言操縱能力。《假期伴侶》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可以說是意味深長的小品,精巧精煉,但又不同於歐·亨利、契訶夫這些短篇前輩所擁有的敘事傳統,它們的故事性已經被削弱,文體具備豐富的實驗性,在多風格的嘗試下,最終被嚴重突出的是事物與人的“核”,那位於表象之下,某些事物荒謬的本質以及因真實而顯得可悲可笑的人,所帶給讀者的閱讀感受,可以超越一時一地,放之四海而皆準。
胡戈·羅切爾的筆端流瀉著諷刺,他對中產階層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階層人們生活中的虛偽、造作、僵化、無趣等毫不留情,大加嘲弄,《洗衣服的鑰匙》、《假期伴侶》就是這類作品。
胡戈·羅切爾於去年8月去世,他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不知道在瑞士文壇是否後繼有人。但對於寫作者來說,人類的情感與心靈永遠是共通並駛的,不管具體面臨的社會現實如何,直面相對,不迴避不失語,才是文學的希望所在——這也是我從這本書里得到的啟示。
寫作背景
說到瑞士的德語文學,我們很快就會想起在蘇黎世家喻戶曉的高特弗里特·凱勒,想到他的《綠衣亨利》和《馬丁·薩蘭德》。凱勒在他的小說中,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向世界展現了位於阿爾卑斯山中心地帶這個小小的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歷史畫卷,描述了個體在社會形態變異中的歷程。凱勒19世紀就已經為瑞士德語文學奠定了在整個德語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的瑞士德語文學群星燦爛。他們中間不僅湧現出了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施皮德勒、黑塞那樣的經世作家,也蘊藏著像羅伯特·瓦爾澤那樣鮮為人知、卻又充滿神秘和狡詭的現代主義文學家。著名的文學雙子座迪倫馬特和弗里施更是為瑞士德語文學增添了絢麗的色彩。這些作家在中國都有廣泛的譯介,深受中國的外國文學愛好者的喜愛。然而,我在這裡使用的“瑞士德語文學”概念卻蘊含著某種悖論,因為這個概念本身說明了瑞士德語文學在存在中的不存在,或者說是在不存在中的存在。
我們若用羅伯特·瓦爾澤語調來說,假如有一種文學叫做瑞士德語文學,那么它就像這個國家一樣,渺小得幾乎就像片片飄逸的雪花,然而正是這片片雪花所含有的巨大力量,染白了雄偉的阿爾卑斯山脈。對於任何—個瑞士人來說,地球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二都是國外,因此毫不奇怪,20世紀以來的瑞士德語作家幾乎都必須融入整個德語地區,或者融人整個世界。洛桑的文學理論家彼得·馮·馬特曾經說過,瑞士德語文學是一種語言區域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某種效應,瑞士籍的德語作家若要成功,那么他們必須在其他德語國家得到認同,在那裡摘取文學的桂冠。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僅有五百萬德語人口的瑞士無法為德語文學的接受提供足夠的疆土和閱讀人口,如果說要對瑞士德語文學做一個定義的話,那么它首先是屬於德語的,其次是屬於德語國家的,再者是屬於歐洲的,最後則是歌德意義上屬於“世界文學”的,因此它也是屬於瑞士的。之所以這么說,那是因為近當代瑞士德語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他們創作的視角、涉及的主題以及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情感世界、生活和命運都遠遠地超越了瑞士的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