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人與超人》
《人與超人》作者簡介
 蕭伯納
蕭伯納藝術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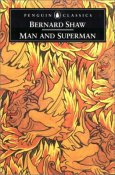 《人與超人》
《人與超人》第二,描寫了中產階級一代人的軟弱。這一代人不像自己的父輩,是通過奮鬥掙扎才從社會底層爬上來的。他們從小生活在優裕環境裡,具有良好教養,懂得區分高雅與鄙俗,甚至接觸到了進步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的思潮。他們往往會對自己的父輩和社會提出各種批評,表示不滿甚或蔑視。但充其量也就僅止於此。由於割不斷的血緣聯繫,在資本主義的金錢法則面前,他們很快就動搖、屈服、妥協,最終表現出一種左右為難的尷尬。《鰥夫的房產》和《華倫夫人的職業》中的年輕一代屈蘭奇與薇薇是典型的代表,“愉快的戲劇”之一《康蒂泰》的同名女主人公和《人與超人》中的坦納也都帶著同樣印記。這也是蕭伯納本人改良主義思想的反映。
 《人與超人》
《人與超人》第三,思考了更有普遍意義的人生態度與人性問題。蕭伯納的諷刺鋒芒不僅指向社會現實,也指向更根本的人類的本性。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人性的醜陋方面,譏嘲以浪漫情調看待人與人生的處世觀點。早期的劇本《戰爭與人》通過一個少女在戰爭經歷中的成長,肯定了現實清醒的人生觀。晚期蕭伯納在《聖女貞德》中,又通過再現法國農家愛國少女貞德的悲喜劇,深入揭示了人類天性的悖謬,即人類在實質上是畏懼自己的英雄和聖者的,並因此經常殘殺他們,直到他們的美德變成了人皆有之的品質為止,才開始崇敬他們。但蕭伯納對人類和人性並不悲觀,相信人類的進步,他有不少劇作探討了人性由惡向善的轉變,並在讚美人的生命力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創造進化”哲學。《人和超人》的“唐璜在地獄”部分是關於“創造進化”哲學的詳細闡述,《回到梅瑟色拉》則是展示這一哲學的歷史畫卷。在這部時間跨度從創世紀開始到這公元三萬二千年的幻想劇中,蕭伯納發揮恢宏瑰麗的想像力,試圖通過人的生命永恆不息的綿延與創造,來糾正人類的錯誤與缺點,具體說明人類生命的創造進化問題。
內容提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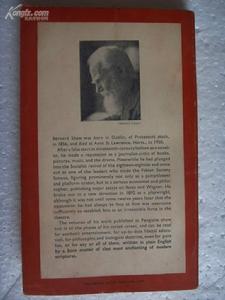 《人與超人》
《人與超人》……不要祈禱,如果你祈禱,你就枉費在這裡的大優點了,這裡的大門上寫著:“你們這些來這裡的人把一切希望都喔遺忘了吧!”你想那是一種多么好的解脫!到底什麼是希望呢?就是一種道德責任的形式。這裡沒有希望,所以就沒有責任,不用工作,沒有用祈禱可以得到的東西,也沒有因你任性非為而失去的東西。地獄,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使自己快樂,什麼事也不必做的地方。……
……地獄是現實的主人的老家——天國,和現實的奴隸的老家——世間惟一的避難所。世間是一個訓練所,在那裡男人和女人扮演著男主角和女主角,聖人和罪人的角色,但被肉體拖累,他們從愚蠢者的樂園落了下去:饑渴、寒冷、年老、衰弱和疾病,尤其是死亡,使他們做現實的奴隸。一日必須吃三次,消化三次;一世紀要繁衍三代;許多年代的信仰、小說、科學,最後都被歸納成一句祈禱詞:“讓我成為一個健康的動物。”但在這裡,你可以免除肉體的橫虐,因為在這裡你不是一個動物,你是一個幽靈、影子、幻相和一個固習的概念,沒有死,沒有年齡,總而言之,就是無肉體。這裡沒有社會問題,沒有政治問題,沒有宗教問題,而最好的,或許就是沒有衛生問題。在這裡你可以稱你的外貌為美,稱你的感情為愛,稱你的情緒為英勇,稱你的抱負為美德,和你在世間的稱呼一樣。但這裡沒有反駁你的正確事實,沒有把你的要求和藉口作為諷刺的對照,沒有人間的喜劇,什麼都沒有,只有永久的浪漫和宇宙的歌劇。正和我們的德國詩人朋友歌德在詩里說的一樣:“在這裡無聊的荒謬的也成為有意義的:永恆的女性也可引導我們向上”……
……人是有生命組織中最高的奇蹟,是宇宙萬物中最強烈地生存著的東西,是一切有機體中最具意識的,但是他的頭腦是多么差勁啊!愚蠢的人們從現實中的勞苦和貧窮,學習到貪婪和殘忍。他們的想像力寧可去餓死,卻不願面對現實,於是堆起各種幻相來隱藏現實,而自以為聰明,自以為天才!而彼此又互相攻訐,“愚蠢”罵“想像”痴憨:“想像”罵“愚蠢”無知。然而,天啊!讓“愚蠢”擁有一切的知識,而“想像”擁有一切的智慧型!
那么它們間就鬧得一團糟了。所以我在處理浮士德的事情時就說過:人類的理性所能為人做的,只是人弄成比野獸更具獸性罷了。一個強壯的身體,勝過一百個消化不良、腸胃氣脹的哲學家的頭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