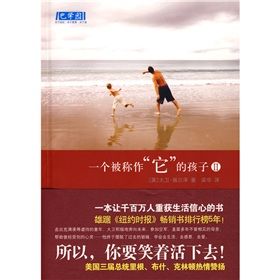編輯推薦
一本讓千百萬人重獲生活信心的書,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5年!大衛遭受了我和很多人都無法經受的虐待和苦難,但他永遠對社會充滿責任和使命、對世間充滿愛與感恩。美國版《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編輯、大衛的妻子瑪莎·佩爾澤
“你不擇手段打擊我.我犯過錯、瑟縮過,但決不怨天尤人。我會為自己闖出一片天地。”這是大衛·佩爾澤八歲時立下的誓言:在他的童年時代,母親無所不用其極地虐待他,天天打他、餓他,用火燒他、用刀扎他,逼他喝氨水……獲救多年,他活在內心的掙扎中。不堪的回憶糾纏著他,他似乎仍然是被關在地下室的、遍體鱗傷的“它”。
大衛渴望有一番成就。他決心承受挫折,從逆境中獲得力量他參加美國空軍,為臨終的父親送行,與兄弟團聚,直面多年都不曾見過的母親……他經歷了艱辛的婚姻,開創了似乎難以完成的事業,嘗試著去拯救無數與他一樣曾經受創的心靈。
大衛終於擺脫了過去的鎖鏈,學會去生活、去感恩、去愛。
本書出版後,長期雄踞各大暢銷書排行榜前列,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均創造了暢銷奇蹟,被普遍讚譽為“人類堅強靈魂的奇蹟”、“最激勵人的書”。
本書講述大衛長大成人後的故事,也是關於人類的希望與救贖、獲得愛與接受,尤其是最終學會報答與感恩的真實經歷。他希望通過親身經歷和心靈之旅,告訴人們這樣一個真理:即使是最黑暗的夜空中,也始終有最燦爛的星光在閃爍。
內容簡介
《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2》講述了大衛童年時斯罕見經歷。在那段日子裡,他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到母親的殘酷虐待,母親天天打他、餓他,逼他喝氨水,將他的胳膊燒得皮開肉綻,在他肚子上扎出一個大洞……每一天,他的生命都受到嚴重威脅,多次瀕臨絕境然而,強烈的求生願望和永不屈服的堅韌心靈給了他生存的動力,最終使他戰勝了遠比自己強大百倍的對手。作者簡介
大衛·佩爾澤,享譽國際的美國暢銷書作家。童年時代曾遭到親殘酷虐待,是20世紀美國加州歷史上最嚴重的三起虐待兒童案中唯一存活下來的人。於美國空軍服役期間開始參與少年救援計畫,常到各地演講,給人帶來希望和力量,受到里根、布希、柯林頓總統高度讚揚。1994年因致力防止兒童受虐而入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為唯一獲此殊榮的美國人。目錄
結束飛走
一封家書
渴望
逃走
重組
愚蠢的行動
改變
上帝的恩賜
根源
參與救助活動
永別了
最後的抉擇
訣別
美好的事
尾聲
附錄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結束1973年3月4日,加利福尼亞州達里鎮。
我嚇壞了,雙腳冰涼,肚子餓得要命。我豎起耳朵,透過車庫的黑暗,捕捉著樓上臥室里母親翻身時,床鋪發出的最微小的聲音。我甚至可以從母親的乾咳中,判斷出她是在熟睡還是正準備上床。我祈禱母親千萬不要把她自己咳醒。我祈禱我還有點兒時間。就在幾分鐘之前,苦難的一天又開始了。我緊閉雙眼,飛快地喃喃祈禱著,不過我覺得上帝是恨我的。
因為沒有資格成為“那個家庭”中的一員,我躺在一張破舊的行軍床上,連毯子也沒有。我蜷縮成一團,儘量讓自己暖和一點兒。我用襯衫的上半截蓋住腦袋,希望呼出的熱氣會讓臉和耳朵暖和點兒,還把雙手夾在雙腿間或者放在腋下。確信母親已經沉沉睡去後,我就大著膽子,從一堆髒兮兮的破爛里偷出一塊抹布,緊緊地裹在腳上。為了保暖,我什麼都可以乾。
保持體溫,是為了生存。
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幾個月來,我只有在夢中才會得到一些解脫。雖然我很努力地想睡著,但還是不能再次入睡。我太冷了,膝蓋禁不住瑟瑟發抖。我小心翼翼地摩擦著雙腳,即使弄出一點點聲響,也害怕母親會聽到。沒有母親的命令,我什麼也不能做。就算我知道她已經在兄弟臥室的下鋪睡著了,也依然能感覺到她在控制我。
母親一直控制著我。
盡力回想過去的時候,我的大腦開始運轉起來。我知道,要怎么活下去,答案全在我的過去里。除了食物、熱量和活下去之外,弄明白母親為什麼要那么對待我,占據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對母親的第一個回憶就是“謹慎”和“敬畏”。當我還是一個四歲小孩的時候,就能從母親的聲音里揣測出有怎樣的一天在等著我。當母親變得耐心、親切的時候,她是我的“媽咪”。但當她變得易怒、暴躁不安的時候,我的“媽咪”就變成了“母親”——一個冷酷、邪惡、會出其不意地對我施行暴力的人。我很快變得恐慌,害怕會招致母親的攻擊。在沒有得到母親允許的情況下,我甚至連洗手間都不敢去。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她酒喝得越多,“媽咪”的成分就越少,“母親”的成分就越多。我滿五歲前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母親酒後發瘋,竟意外地把我的胳膊弄得脫臼了。那一刻,母親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一樣:她也知道自己做得太過分了,已經失控了。這一次傷害的嚴重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她以往打我的臉、扎我的身體或者把我扔下樓梯。
但是剛剛回過頭來,母親就編造了一個謊言,用來掩蓋那次事故。第二天早晨,母親開車帶我去醫院,向醫生哭訴說,我夜裡從床鋪上掉下來了;接著還說,她是如何竭盡全力地想接住我,又是多么不能原諒自己動作太慢了。醫生似乎也覺得奇怪。回家以後,我的父親——一個接受過救護培訓的消防隊員,對母親編造的故事居然沒有任何懷疑。
後來,當母親把我抱在胸前的時候,我知道,我決不能說出這個秘密。儘管如此,不知道為什麼,我仍然覺得會回到以前和媽咪在一起的好日子。我確信她會從酒醉中醒來,把那個“母親”永遠拋棄掉。作為一個應該在母親臂彎里撒嬌的四歲小孩,我覺得最壞的日子已經到頭了,母親會變好的。
但是,唯一有改變的就是母親發怒的程度,以及我與她之間的秘密。到了我八歲的時候,她不允許別人再叫我的名字,她已經把“大衛”換成了“男孩”。很快,她覺得男孩聽起來太人性化了,於是決定叫我“它”。因為不再是那個家庭中的一員,我被禁止在家裡居住,只能睡在車庫裡。如果我不是把雙手放在屁股下,坐在樓梯底下,就一定像奴隸一樣在做家務。如果沒有在母親規定的時間內幹完活兒,我不僅要遭到毒打,還要挨餓。母親會一個多星期都不給我吃的,這不止一次了。在母親的“遊戲”中,她把食物作為致命武器來對付我這叫她感到非常得意。
母親對我所做的事情越是怪異,她就越覺得自己會僥倖地逃脫懲罰。她把我的胳膊放在煤氣爐上燙,然後對驚呆的老師說,是我玩火柴燒到了自己。刺傷我的胸部以後,她告訴我那些嚇壞了的兄弟,是我攻擊了她。
多年來,我竭盡全力地事事想在前面,力圖用我的智慧來戰勝她。在母親打我之前,我就先繃緊身體的某些部位。如果母親不給我吃的,我會盡力偷些食物殘渣。母親在我嘴裡灌滿清洗碗盤用的粉紅色肥皂水,我會含著它,直到母親看不到了,再吐到車庫的垃圾桶里。無論以何種方式打敗母親,都意味著我的勝利。這些小小的勝利支撐著我活了下來。
我唯一的解脫方式就是做夢。當我朝後仰著頭,坐在樓梯底下的時候,我看到自己就像英雄超人一樣,在空中飛翔。我相信我和超人一樣,有兩重身份。在這個冰冷的家裡,我的身份就是那個被叫作“它”的孩子——個被拋棄的、從垃圾桶里撿吃的、讓人恥笑的、沒有發育好的孩子。當我趴在廚房地板上不能動彈的時候,我就擁有超人的身體。我知道自己的身體裡有一股力量,我有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秘密身份。我開始相信,如果母親朝我開槍,子彈會從我的胸口彈回。無論母親發明了什麼“遊戲”,也不論她對我的攻擊有多么嚴重,我都要贏。我要活下去。當我不能忍受疼痛和孤獨時,就會閉上雙眼,展臂飛翔。
我過完十二歲生日,又過了幾個星期,母親和父親分開了。超人消失了。我體內的力量也喪失了。那天,我覺得,母親一定會殺了我——就算不是在那個星期六,那日子也不遠了。由於父親的離去,母親變得更加肆無忌憚。雖然多年來,當母親強迫我吞下一勺勺氨水的時候,父親只是一邊啜酒一邊神情沮喪地看著;當母親痛打我的時候,父親只是聳聳肩膀。但是,只要他在那個房子裡,我就會覺得安全些。然而,當母親把屬於父親的那點東西扔上車,車開走後,我緊緊地合上雙手,低聲禱告:“也許有一天,他會帶我離開這個地獄。阿門。”
這大概是兩個月前的事情了,上帝從來都不會回應我。現在,我繼續在黑暗的車庫裡戰慄,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我為自己沒有勇氣和力量反抗而哭泣。我太累了。八年來連續不斷的折磨已經把我生存的力量吮吸殆盡。我雙手合十,禱告著,如果母親要殺死我,就請她仁慈些,趕快來吧。
我開始覺得頭暈,越是祈禱,就越是覺得自己飄忽忽地進了夢鄉。我的膝蓋不再顫抖,那瘦骨嶙峋的指關節慢慢舒展開來。在沉沉睡去之前,我對自己說:“上帝,如果你能聽到,可以帶我離開這裡嗎?請你帶我走吧,今天就帶我走。”
突然,我挺直了上半身。我聽到樓上的地板在母親的重壓下發出的聲音,緊接著,是她那令人窒息的咳嗽聲。我幾乎可以想到,她彎著腰、快要把肺咳出來的樣子,這是多年來她不停地抽菸和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天啊,我多么痛恨她的咳嗽。
睡意很快就消失了,一陣寒氣襲進了我的身體。我還是想睡,想永遠地睡下去。我漸漸清醒過來,詛咒上帝沒把我從睡夢中帶走,可上帝從來就不聽我的禱告。我多么希望自己已經死了。我連在這個“房子”里多活一天的力氣也沒有了。我無法想像滿是母親和她那險惡遊戲的一天。我崩潰了,痛哭起來,淚如泉湧。過去我是很堅強的,只是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
母親磕磕絆絆的聲音把我帶回了淒涼的現實。我擦乾鼻涕和眼淚——不能,決不能流露出一絲軟弱。我深深地吸了口氣,盯著上面。在退回殼裡之前,我把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為什麼?我嘆了口氣。如果你是上帝,有什麼理由?我實在……實在很想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我還活著?
母親搖搖晃晃地走出臥室。起來!我腦袋裡尖叫著,快起來,只有幾秒鐘的時間……我本該在一個小時前就起來幹家務。
我站起來:在黑暗中摸索著,想找到車庫的電燈開關。一條腿絆到了行軍床上,我條件反射地伸出手,想緩衝一下,但是太遲了。瞬間,我的臉撞到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晶瑩的淚珠模糊了我的視線,我雙手拍打著地面。我實在是太想睡去了,不想再醒過來。
聽到母親的腳步聲朝著洗手間方向去了,我從水泥地上爬起來,打開電燈,抓起掃帚,跑上了樓梯。如果我可以在被母親抓到之前打掃完樓梯,她就不會知道我起晚了。我能贏的,我笑著對自己說,來,小子,快點!我都快喘不過氣了,大腦在超音速地運轉著,但身體的反應卻很慢,雙腳像水泥塊一樣,手指尖凍得發麻。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么慢,過去,我像閃電一樣快呀!
我不假思索地伸出左手去夠木頭扶手,扶著扶手爬上了樓梯。就要贏了,我對自己說,真的就要贏了!我聽到了上面洗手間裡汩汩的流水聲。我加快腳步,朝扶手伸長了胳膊。我心裡在笑——就要打敗她了!突然間,我的手抓空了,心猛地一沉,身體開始搖晃。扶手!抓住該死的扶手!雖然我儘量集中精力,但手就是不聽使喚。
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我眼冒金星,腦袋懵懵的。我能分辨出,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中站著一個身影。“那是……什麼東西?”
我努力搖晃著腦袋,想讓自己清醒一點兒。有一陣子,我以為自己正注視著上帝派來的、要接我去天堂的天使。
然而,母親病態的咳嗽很快擊碎了我的美夢。“我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她的聲音嚇得我差點尿褲子。為了不把其他的孩子吵醒,母親用一種柔軟卻帶有幾分邪惡的聲音說著:“讓我看看,有多快……把你身後那個可憐的小東西拿到這兒來……開始!”母親打了一個響指,表示開始。
把掃帚放在樓梯底下時,我的身體在瑟瑟地發抖。
“噢,不!”母親微笑著,“帶上你的‘朋友’一起來。”
我弄不明白母親的意思,朝四周看了看,然後抬起頭望著她。
“掃帚,笨蛋。帶上掃帚。”
每上一個台階,我都在盤算著,怎樣才能逃脫母親妨礙我按時完成家務的罪惡遊戲。我警告自己要集中精力。我知道她打算用掃帚做武器,打我的胸或臉。有時候,就剩我們倆單獨在一塊兒時,母親喜歡用掃帚根兒直接戳我的胭窩。如果跟著她進了廚房,我就死定了,就不能走著去學校,更別說跑了。如果母親讓我留在樓梯上,我知道她只會打我的上半身。
一到樓梯頂,我很自覺地擺出了“受訓的姿勢”:身體挺得直直的,頭彎得低低的,雙手緊貼在身體兩側。我不能動一塊肌肉,也不能眨一下眼,更不能看她。沒有母親的允許,我連氣兒都不能喘。
“說!說‘我是笨蛋’。”母親彎下腰,在我耳邊說。我退縮著,以為她會擰我的耳朵。這只是遊戲的一部分,她是在看我會不會退縮。我不敢抬頭,也不敢再往後退。我的腳後跟已經懸在了樓梯的邊緣。我禱告著,今天,千萬不要把我推下去。
“來,說呀。請說。”母親乞求著。她的聲音有些變了,似乎很靜,沒有威脅性。我的大腦運轉著,弄不清母親僅僅想讓我說話,還是想讓我做些什麼。不妨說,我掉到了她的陷阱里。我把全身的能量都集中在了腳尖上,但越是集中精力,身體就越想搖晃。
突然,母親把一根手指伸到我的下巴底下,抬起我的臉對著她。她腐臭的呼吸讓我直想吐。我努力讓自己不被她的惡臭熏倒。她不讓我在家裡戴眼鏡,但我還是怒視著她那張膨脹發紅的臉。她那曾經閃亮的頭發現在變得油膩膩的,貼在臉上。
“說!你到底覺得我有多愚蠢?說實話,你是不是覺得我很愚蠢?”
我膽怯地仰著頭,說:“媽媽……”
我的臉一陣刺痛。
“誰讓你說話了?不許看著我!”母親嘶嘶地說。
我猛地低下頭,迅速把痛苦壓下去。上帝啊,我對自己說,我居然沒有看到她過來,我這是怎么了?每次她打我的時候,我都能先看見她掄起胳膊。我不知道自己今天為什麼這么慢。該死,大衛,集中精力思考!
“它該開始做它的家務了!”母親怒吼著,“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你覺得我很愚蠢,是不是?你認為你能僥倖地逃脫,是不是?”她搖著頭說:“傷害你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你選擇了你的行為。你知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你知道你來這個家是乾什麼的。”
“如果它想吃飽,那么,很簡單,它必須按照要求去做。如果它不想受到懲罰,那就別惹麻煩。它應該知道規則。我不會把它和其他人區別對待。它只不過是不聽話。”母親停下來,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喘息,似乎陷入了困境。我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只希望她走上來打我。“我該做什麼?”她提高了嗓門,“我應該睡覺,但是沒有,我得在這兒陪著你。可惡的狗東西!該死的雜種!你知道你是乾什麼的。你不是人,而是……任我支配的東西。明白嗎?我說清楚了嗎?要不再來一遍?”母親咆哮著。
母親的話在我心底迴響著。多少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地聽著同樣的話。多少年來,我一直就是任她擺布的機器人,像一個能讓她隨意開關的玩具。
我內心幾近崩潰,身軀開始戰慄,再也無法忍受了!我對自己喊著,快來吧!殺了我吧!快點!我的視野猛然間變得清晰了。憤怒涌上心頭,我的內心不再害怕,也不再感到徹骨的寒冷。我使勁地搖著頭,緊盯著母親的身體,右手緊緊地攥著掃帚把。然後,我慢慢地舒了一口氣,眼睛直瞪著母親,嘶嘶地說:“別管我……母狗!”
母親變得有點癱軟。我聚精會神,想看透她的金絲邊眼鏡和那雙發紅的眼睛。我要把過去八年的苦痛和孤獨全部還給母親。
母親的臉變得慘白。她明白了,她清楚地知道了我現在的感受。我告訴自己,這起作用了。母親想逃開我的怒視,她輕輕把頭轉向了左邊。我緊盯著母親的一舉一動,她逃不了。母親的目光游移不定,我揚起腦袋,目光更加犀利了。我笑著,心底里升起一股暖流。現在,控制者是我。
在意識深處,我聽到了咯咯的笑聲。有一陣兒,我還以為是自己在嘲笑母親,向下一看,卻見母親在假惺惺地笑著。她呼出的腐臭氣息打斷了我的思路。母親越是笑,我的身體就越是緊張。她把頭轉向燈光。此刻,我告訴自己:她過來了!來吧!快點,乾吧!我倒是要看看她能幹出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