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其中本紀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立了史書新體例“紀傳體”。
一、本紀
 《史記》
《史記》“本紀”是全書提綱,以王朝的更替為體,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其中記載先秦歷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記載秦漢歷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項羽,漢高祖劉邦,高后呂雉,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和漢武帝劉徹。
二、表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三、書
“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
四、世家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跡。
五、列傳
“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少數民族的傳記。
《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記述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國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確鑿無疑。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作品目錄
| 卷數 | 內容 |
| 【本紀】 | |
| 史記卷一 | 五帝本紀第一 |
| 史記卷二 | 夏本紀第二 |
| 史記卷三 | 殷本紀第三 |
| 史記卷四 | 周本紀第四 |
| 史記卷五 | 秦本紀第五 |
| 史記卷六 | 秦始皇本紀第六 |
| 史記卷七 | 項羽本紀第七 |
| 史記卷八 | 高祖本紀第八 |
| 史記卷九 | 呂太后本紀第九① |
| 史記卷十 | 孝文本紀第十 |
| 史記卷十一 | 孝景本紀第十一 |
| 史記卷十二 | 孝武本紀第十二 |
| 三皇本紀 | |
| 【表】 | |
| 史記卷十三 | 三代世表第一 |
| 史記卷十四 |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
| 史記卷十五 | 六國年表第三 |
| 史記卷十六 |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
| 史記卷十七 |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
| 史記卷十八 |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
| 史記卷十九 |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
| 史記卷二十 |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
| 史記卷二十一 |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
| 史記卷二十二 |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
| 【書】 | |
| 史記卷二十三 | 禮書第一② |
| 史記卷二十四 | 樂書第二③ |
| 史記卷二十五 | 律書第三 |
| 史記卷二十六 | 曆書第四 |
| 史記卷二十七 | 天官書第五 |
| 史記卷二十八 | 封禪書第六 |
| 史記卷二十九 | 河渠書第七 |
| 史記卷三十 | 平準書第八 |
| 【世家】 | |
| 史記卷三十一 | 吳太伯世家第一 |
| 史記卷三十二 | 齊太公世家第二 |
| 史記卷三十三 | 魯周公世家第三 |
| 史記卷三十四 | 燕召公世家第四 |
| 史記卷三十五 | 管蔡世家第五 |
| 史記卷三十六 | 陳杞世家第六 |
| 史記卷三十七 | 衛康叔世家第七 |
| 史記卷三十八 | 宋微子世家第八 |
| 史記卷三十九 | 晉世家第九 |
| 史記卷四十 | 楚世家第十 |
| 史記卷四十一 |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
| 史記卷四十二 | 鄭世家第十二 |
| 史記卷四十三 | 趙世家第十三 |
| 史記卷四十四 | 魏世家第十四 |
| 史記卷四十五 | 韓世家第十五 |
| 史記卷四十六 |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
| 史記卷四十七 | 孔子世家第十七 |
| 史記卷四十 | 陳涉世家第十八 |
| 史記卷四十九 | 外戚世家第十九 |
| 史記卷五十 |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
| 史記卷五十一 |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
| 史記卷五十二 |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
| 史記卷五十三 |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
| 史記卷五十四 |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
| 史記卷五十五 |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 史記卷五十六 |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
| 史記卷五十七 |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
| 史記卷五十八 |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
| 史記卷五十九 |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
| 史記卷六十 | 三王世家第三十 |
| 【列傳】 | |
| 史記卷六十一 | 伯夷列傳第一 |
| 史記卷六十二 | 管晏列傳第二 |
| 史記卷六十三 |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
| 史記卷六十四 |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
| 史記卷六十五 |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
| 史記卷六十六 | 伍子胥列傳第六 |
| 史記卷六十七 |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
| 史記卷六十八 | 商君列傳第八 |
| 史記卷六十九 | 蘇秦列傳第九 |
| 史記卷七十 | 張儀列傳第十 |
| 史記卷七十一 |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
| 史記卷七十二 | 穰侯列傳第十二 |
| 史記卷七十三 |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
| 史記卷七十四 |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
| 史記卷七十五 |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
| 史記卷七十六 |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
| 史記卷七十七 |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
| 史記卷七十八 |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
| 史記卷七十九 |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
| 史記卷八十 | 樂毅列傳第二十 |
| 史記卷八十一 |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
| 史記卷八十二 |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
| 史記卷八十三 |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
| 史記卷八十四 |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
| 史記卷八十五 |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
| 史記卷八十六 |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
| 史記卷八十七 |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
| 史記卷八十八 |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
| 史記卷八十九 | 張耳陳余列傳第二十九 |
| 史記卷九十 |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
| 史記卷九十一 |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
| 史記卷九十二 |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
| 史記卷九十三 |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
| 史記卷九十四 |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
| 史記卷九十五 |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
| 史記卷九十六 |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
| 史記卷九十七 |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
| 史記卷九十八 |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
| 史記卷九十九 |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
| 史記卷一百 |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
| 史記卷一百一 |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
| 史記卷一百二 |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
| 史記卷一百三 |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
| 史記卷一百四 |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
| 史記卷一百五 |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
| 史記卷一百六 |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
| 史記卷一百七 |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
| 史記卷一百八 |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
| 史記卷一百九 |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
| 史記卷一百十 | 匈奴列傳第五十 |
| 史記卷一百十一 |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
| 史記卷一百十二 |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
| 史記卷一百十三 |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
| 史記卷一百十四 |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
| 史記卷一百十五 |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
| 史記卷一百十六 |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
| 史記卷一百十七 |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
| 史記卷一百十八 |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
| 史記卷一百十九 |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
| 史記卷一百二十 | 汲鄭列傳第六十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
|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 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
|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④ |
|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
|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
| 史記卷一百三十 |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
註:
①不列名義上的天子漢惠帝本紀,以呂太后有實際統率,理由與項羽同
②已殘,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禮論》及《議兵》來代替正文
③已殘,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禮記》《樂記》代替正文
④未闡述諸侯國之俗,僅記司馬季主之事
成書過程
名稱來由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此前“史記”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創作背景
東周時期王道廢弛,秦朝毀棄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貴圖書典籍散失錯亂。漢朝建立後,蕭何修訂法律,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立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品學兼優的文學之士逐漸進用,《詩》《書》等被毀棄的古書亦不斷在各地被愛好文學的人士搜尋並獻出。
取材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如不列沒有實據的三皇,以五帝作為本紀開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創作過程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整理和論述歷史。《隋書·經籍志》載:“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將修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可惜壯志未酬。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
司馬遷子承父志,繼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漢三年(前98年),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辯護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並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給了他巨大的創傷。出獄後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前後經歷了14年,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傳承增補
傳承
 司馬遷畫像
司馬遷畫像《史記》經過司馬遷外孫楊惲的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卷,篇數跟司馬遷自序所說的相符。但《漢書·司馬遷傳》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魏張晏註:“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余篇”,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馮商所續《史記》七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 ,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泄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唐朝時,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
增補
《史記》在流傳過程中,也竄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記》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馬遷所撰寫,明顯有補竄痕跡,如《司馬相如列傳》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語,《公孫弘傳》中有漢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語,《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語,等等。而對於《史記》缺篇的補寫,裴駰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國時張晏的話,說《史記》亡十篇,“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續,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認為褚少孫補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張守節《龜策列傳·正義》則認為褚少孫補十篇,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也認為褚少孫補十篇。但是,據《漢書·藝文志》、《論衡·須頌篇》、《後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漢後期補續《史記》的多達17家。張大可認為真正補續的只有褚少孫一人,其餘均為續寫西漢史,大都單獨別行,與褚少孫續補附驥《史記》而行不同 。趙生群則根據有關資料,認為真正補續《史記》的除褚少孫之外,還有馮商,《漢書·藝文志》對馮商所續《太史公》保留七篇,當是補亡之作;刪除四篇,應是續《史記》之文。
《史記》中哪些屬於竄入文字,古今以來的學者也有許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適,他在《史記探源》中認為,《史記》屬於今文學,由於劉歆的竄亂,乃雜有古文說。劉歆偽造《左傳》,凡《史記》中出於《左傳》的內容,皆為劉歆所竄入。而且,崔適列舉八條理由證明《史記》斷限止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後的記載皆為竄入。他認為,《史記》中有29篇為後人所補和妄人所續,它們是:《文帝紀》《武帝紀》《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書(8篇)《三王世家》《張蒼傳》《南越傳》《東越傳》《朝鮮傳》《西南夷傳》《循吏傳》《汲鄭傳》《酷吏傳》《大宛傳》《佞幸傳》《日者傳》《龜策傳》。崔適還認為《年表》五至九為褚少孫所補,其餘妄人所續 。崔適的一些觀點頗有偏激之處,朱東潤《史記考索》附《史記百三十篇偽竄考》一文 ,對“十篇亡佚”和崔適提出的29篇補續及其他說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進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駁前人者。
據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總論》“史記附益條”,涉及《史記》補竄的篇目有34篇,分別是:
本紀2篇:《秦始皇本紀》《今上本紀》。
表6篇:《三代世表》《漢興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書8篇:《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世家7篇:《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傳13篇:《賈生列傳》《酈商列傳》《張丞相列傳》《酈生陸賈列傳》《田叔列傳》《李將軍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司馬相如列傳》《酷吏列傳》《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
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孫所補,有些則是後人補竄。今人張大可經過詳細考釋,認為竄補篇目除以上34篇外,還有《孔子世家》《韓信盧綰列傳》《匈奴列傳》《大宛列傳》,並將所有補竄篇目內容分為四類:褚少孫等續史篇目內容、好事者補亡篇目內容、讀史者增竄篇目內容、司馬遷附記太初以後事篇目內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後記事,凡22人,是司馬遷對歷史變遷“綜其終始”的簡略附記,總計1541字,這些人和事集中在兩件大事上,一為巫蠱案,一為李陵案 。趙生群則認為,《史記》記事迄於太初,太初以後所記載的事件,是後人補竄。
作品鑑賞
敘事藝術
史記獨特的敘事藝術,非常注重對事件因果關係的更深層次的探究,綜合前代的各種史書,成一家之言,縱向以十二本紀和十表為代表,敘寫了西漢中期以前的各個歷史時代,橫向以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為代表,統攝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領域和行業,形成縱橫交錯的舒適結構。
另外,《史記》的章法、句式、用詞都有很多獨到之處,別出心裁,不循常規,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生獨特的效果。
《項羽本紀》是《史記》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從歷史上說,具體記錄了楚漢相爭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風雲,從文學上說,本文是中國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藝術傑作,文中描繪的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戰爭畫卷,塑造的項羽經典的悲劇英雄形象,對後世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人物編排名實兼顧,以類相從。《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在聯繫,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即:同樣一件事涉及好幾個人物時,在一處詳敘,在別處就略而不敘,有時以“語在某某事中”標出。這不僅避免了重複,對於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人物刻畫
一、注重語言,細節描寫
《廉頗藺相如列傳》藺相如所講的“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個性化的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性格,是作者司馬遷提煉的,最能表現藺相如思想境界的內在美的精粹語言,是藺相如精神品質的升華,是他一切行為思想基礎,是全篇中最關重要的一名話。司馬遷為了突出這句話,先寫廉頗的驕橫以與藺相如的忍讓映襯。但沒有交代藺相如這么做的動機,作一跌宕,從而引出舍人的規諫,以舍人的狹窄心胸反襯藺相如的坦蕩襟懷,又作一跌宕;藺相如的答話,先將廉頗與秦王比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著指出連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將軍?又一宕;接著分析趙國的安全系“吾兩人”,不能兩虎相鬥,又一宕;幾經騰挪跌宕,作了許多鋪墊,到最緊要最醒目的地方,才點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這句話來,這確實是畫龍點睛之筆。這個睛一“點”,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讀者面前聳立起來了。
在《高祖本紀》、《項羽本紀》里,司馬遷用了許多細節語言來刻劃人物,這些語言很具有個性。例如項羽見到秦始皇南巡時脫口說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劉邦道歉時說“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足見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劉邦觀秦始皇喟然太息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話說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寫出他雖氣象不凡,但寬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鴻門宴上召項莊舞劍刺沛公時說:“……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後來當劉邦脫逃時又說:“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表現了他老謀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特寫相結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記》中,司馬遷刻畫人物,更多的採用了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相結合的寫法。比如項羽殺卿子冠軍宋義一節,這是發生在起義軍內部的一場鬥爭,這場戰爭關係到反秦鬥爭的成敗。宋義作為起義軍的將領在關鍵時刻卻不去救趙,理由冠冕堂皇,實際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圖謀。作為次將的項羽看穿了他的意圖,當機立斷,斬殺宋義,奪取軍權,扭轉了局勢。在司馬遷的筆下,項羽表現了他的卓識和果斷,表現了他關懷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負國家安危重任的志氣。又有“項羽最得意之戰”——巨鹿之戰,項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再看看諸侯軍的反應,“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這一仗,寫出了項羽不畏強敵的精神、無比旺盛的鬥志,莫敢縱兵、人人惴恐的諸侯軍,更是襯托出了他的英雄氣概。
三、運用對比映襯的方法
《史記》中的《李將軍列傳》描寫李廣就是用的這種手法。司馬遷為了突出李廣帶兵特點,附帶寫了程不識帶兵的作風。李廣帶兵的特點是寬緩簡易“行無部伍行陣”,“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近乎無為而治。程不識帶兵卻非常嚴謹,“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乃是一絲不苟。在程不識的映襯下,紅花綠葉,李廣帶兵的特點就格外顯眼、突出。寬緩與嚴謹只是治軍的作風不同,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從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傾向性,讀者對李廣的敬慕之情也不覺油然而生。在《李將軍列傳》中,要寫李廣毫不相干的程不識就是為了襯托李廣。
寫李廣的不幸遭遇,司馬遷又是把李蔡與李廣對比:“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其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廣的從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論人屬第八等,沒有什麼能耐,可他青雲直上,官運亨通,爵封樂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廣為抗擊匈奴,馳騁疆場四十餘年,身經七十餘戰,立下過許多汗馬功勞,連匈奴人也敬畏而稱之為“漢之飛將軍”。可是這樣一位名將卻“不得爵邑,”甚至還受到誣陷,終於被迫自刎。兩相對比之下,李廣的可悲命運就具體寫出來了,當時用人制度,獎懲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來了。
四、在矛盾衝突中表現人物。
司馬遷生動具體的寫出了人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再現出緊張多變的場面,人物置身於其中,將各自的個性發揮到了極致。如《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作者選擇表面平靜,實際殺機四伏的鴻門場面,讓眾多人物在明爭暗鬥和彼此映襯中展示出了各自鮮明的個性。劉邦的圓滑奸詐,項羽的率直寡謀,張良的深謀從容,范增的偏狹與急躁,樊噲的粗獷豪放,項伯的善良與愚昧,傳神盡相,如在眼前。
《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將“完璧歸趙”、“澠池之會”中緊張的場面與尖銳的矛盾衝突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對秦王意欲毀約的狀況,藺相如隨機應變、足智多謀,在面對面的鬥爭中計謀百出,將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裡。澠池之會上,秦王借著國力強大,肆意侮辱趙王,藺相如寸步不讓,嚴辭厲色,為維護國家尊嚴,置生死於度外。面對廉頗的步步緊逼,藺相如隱忍退讓,這一點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充分表現了藺相如熾熱的愛國情懷,不怕犧牲,甘受委屈,豁達大度,能為常人所不敢為、不願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備的形象。
五、互見法的運用。
司馬遷寫《史記》,既要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歷史的真實,在安排材料上他採用了“互見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幾乎交織在一起,司馬遷按描寫人物的需要,或詳或略,或補或刪,描寫人物各具性格,記述史實則互相補足,這就是“互見法”。
如《魏公子列傳》,主要是表現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並不是時時都能堅持做到這一點。魏相魏齊曾將范雎一頓暴打,後來范雎做了秦相,要報仇,魏齊無藏身之所。趙相虞卿為了救魏齊,解去相印與魏齊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懼秦國,未及時接見他們,結果魏齊“怒而自刎”。如果將這件事寫進《魏公子列傳》里,必然會對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損害。因此,司馬遷將它寫進了《范雎蔡澤傳》中。這樣,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點,又不損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歷史的真實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隱惡”。
六、個性化的語言,凸顯人物風姿。
《高祖本紀》中,司馬遷在刻畫劉邦這個人物形象的時候,較多的使用了語言描寫的方法,用極富個性的語言,將劉邦的形象生動的展現讀者面前。《高祖本紀》中有一段話,陳述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能“與天下同利”,並且善於用人。層疊排比,滔滔而下,顯出劉邦在取得勝利之後的志得意滿。張良、蕭何與韓信,都是傑出的人物,俱能為劉邦所用,則劉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劉邦表面謙遜,實際上很自負。
在《史記》的其他篇章里,司馬遷也多次使用個性化的語言描寫,將人物性格刻畫的惟妙惟肖。
《史記》中的“紀”、“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活動而再現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重要人物數百名。《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有如此廣大的覆蓋面,和司馬遷進步的歷史觀及開闊的視野密不可分。司馬遷本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報任安書》),希望藉助於《史記》一書而揚名後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於這種心態,司馬遷對那些在歷史上雖有卓越表現、終因無人獎掖而難以揚名的布衣平民懷有深切的同情,為他們鳴不平。司馬遷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夠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業績有關,同時也和是否有人宣揚提攜密不可分。在司馬遷看來,戰國四公子或憑藉王者親屬的血緣優勢,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備,他們顯名諸侯猶如順風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司馬遷對儒墨等學派由於門戶之見排斥這些出自平民的俠客而深感不公。司馬遷在按照慣例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同時,也把許多下層人物寫入書中,其中包括刺客、遊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記》所收的人物非常廣泛,並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徵。不但不同類型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風貌。同為戰國策士,蘇秦主要是一位發奮者的形象,而張儀身上更多的卻是狡詐權謀。張良、陳平同是劉邦的重要謀士,但司馬遷筆下的張良令人莫測高深,帶有幾分神異;而陳平這位智囊卻富有人情味,沒有張良那種仙風道氣。《史記》同類人物形象之間尚有如此明顯的區別,不同類型人物形象之間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鮮明的對照,人物的個性在差異、區別中得到充分的顯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能準確地把握表現對象的基本特徵加以渲染,使許多人物形象的個性非常突出。《萬石張叔列傳》突出石奮祖孫三代的謹小慎微,唯命是從。《樊酈滕灌列傳》寫到夏侯嬰時,主要敘述他對劉邦一家的精心呵護,他和劉邦家庭的特殊關係,多次提到他的太僕之職。《李將軍列傳》在描寫李廣時著意表現他高超的祖傳射藝,他射匈奴射鵰者、射白馬將、射追擊者、射獵、射石、射敵方裨將,百發百中,矢能飲羽。《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風采,就在於司馬遷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個性特徵。
司馬遷在表現人物的個性特徵時,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家庭出身、文化教養、社會經歷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給以表現,不但展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徵,而且對形成人物個性特徵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顯示,有時一開始就為人物性格的發展作了鋪墊。蕭何是刀筆吏出身,故能謹守管鑰,因勢奉法。陳平年青時貧而好學,所以始終有讀書人的氣質,見識高遠,在皇帝面前對答如流;周勃最初從事雜藝,沒有什麼學問,執政之後就顯露出知識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噲發跡前以屠狗為業,成為將軍以後保留那種莽撞豪爽之氣,他大塊吃肉,大杯飲酒,對劉邦、項羽也敢於直言直語、大聲大氣。竇嬰是一副老年失勢的窘態,寫田蚡則是少年得志的猖狂。總之,影響人物個性的許多重要因素,司馬遷都充分注意到,《史記》中的人物都是按各自的方式說話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齡、身份和教養。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風貌,各有性格,同時,他們身上還表現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得到社會廣泛認可、並對後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某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史記》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德。蘇秦之於宗族、朋友,劉邦之於蕭何,陳平之於魏無知,韓信之於漂母、亭長,王陵之於張蒼,都是受人之惠而報人之恩。類似這樣知恩圖報的人物在《史記》中有一大批,他們百倍、千倍地報償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負人。
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這是和知恩圖報、以德報德相對應的一種行為,伍子胥之於楚平王,李廣之於霸陵尉、主父偃之於昆弟賓客,採取的都是這種做法。
三是士為知己者死,為報答知遇之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知恩圖報的升華,是它的極端形式。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他本人是贊成這一信條的。《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人都是為知己者死;《孟嘗君列傳》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張耳陳余列傳》中的貫高,也都是為知己者而死。《史記》人物形象還普遍存在寶貴還鄉的想法,這是他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記》描寫了許多人衣錦還鄉的場面,蘇秦、劉邦、司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傳記都有這方面的記載。
《史記》中的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與個性完美的結合。有許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樣去做,卻是各有選擇,各有方式。同是衣錦還鄉,韓信顯得雍容大度,不計私仇,主父偃卻心胸狹小,報復心極強。同是知恩圖報,豫讓、貫高先是忍辱負重,頑強地活下去,關鍵時刻又死得極其壯烈;而侯贏、田光等義士,卻是痛快地以自殺相謝。人物的共性寓於鮮明的個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採用多維透視的方法,筆下人物顯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徵,有血有肉,生動豐滿。李斯這個人物,司馬遷反覆刻畫他外似剛愎而內實游移的矛盾狀態: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形勢下,他想知難而退,卻又貪戀富貴,下不了決心;在趙高廢立之際,開始像是要以身殉國,經趙高勸之以利害,馬上退縮妥協;對於秦二世的無道,本想犯顏直諫,一旦二世責問,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雙重人格表現得非常充分,一個內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躍然紙上。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徵,同時對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多側面地展現人物的精神風貌。
風格特徵
深邃意蘊的敘事和生動鮮活的人物的描寫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使《史記》形成一種雄深雅健的獨特風格。《史記》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並富有傳奇色彩。
《史記》的敘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司馬遷雖然也從瑣碎的生活細事寫起,但絕大多數的人物傳記最終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中展開,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間。司馬遷不是一般地描述歷史進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是對歷史規律和人物命運進行深刻的思考,透過表象去發掘本質,通過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規律。這就使得《史記》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蘊,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格。
思想感情
司馬遷善於把筆下的人物置於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表現,在敘述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展示個人命運偶然性中所體現的歷史必然性。在《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對於戰國諸侯間微妙複雜的利害關係反覆和予以演示,以七國爭雄為背景展開了廣闊的畫面。蘇秦、張儀準確地把握了當時形勢的特點,抓住了機遇,相繼乾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成為當時的傾危之士。陳平年輕時就胸懷大志,足智多謀,適逢秦末動亂和楚漢相爭,大顯身手,屢獻奇計。他設計離間項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亞父”這位謀士。滎陽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東城門迷惑楚軍,劉邦得以出西城門脫險。是他暗示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以穩定形勢,又是他建議劉邦的偽游雲夢澤而藉機擒韓信。劉邦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七日,又是陳平出奇計化險為夷。陳平所獻五計,無一不是關係到劉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天下的興衰安危。陳平這位謀士的形象,也就在駕馭歷史風雲的過程中日益豐滿。《史記》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瑣、或偉岸;有的先榮後辱,有的先辱後榮;有的事業成功,人生幸運,也有的雖然事業成功卻命運悲慘。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演、演員,又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產兒,通過描寫、敘述他們對時勢、潮流的順應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把握與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筆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廓畫面,點出其中蘊含的哲理。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多種類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論,有些悲劇主人公身上體現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這類悲劇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行動具有超前性。儘管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但由於當時條件還不成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變法的吳起、商鞅,主張削籓的賈誼、晁錯,都是這類悲劇英雄。還有一類悲劇人物儘管死得非常壯烈,但他們的悲劇性不是體現了無法實現的歷史必然要求,而是他們相信舊制度的合理。田橫兵敗之後不願意投降漢朝而自殺,其隨從和東海五百義士也相繼殉難,湧現出的是一個悲劇群體。從本質上看,田橫所要維持的不過是諸侯稱雄、列國割據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橫相信已經過時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並為之而奮鬥拼搏,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為悲劇人物。《史記》中許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諸侯王,都屬於這類相信舊制度合理性的悲劇人物。《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按其品格劃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兩類。《趙世家》中為保護趙氏孤兒而付出巨大犧牲的義士公孫杵臼、程嬰,《刺客列傳》、《遊俠列傳》中的刺客遊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獻身精神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無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劇英雄。還有一些悲劇人物的品格存在明顯的弱點,由這些弱點而導致的失誤最終毀滅了自身。但由於他們終歸是英雄,所以其毀滅也是悲劇性的。這類缺失型悲劇英雄以項羽為代表,他生前戰功赫赫,死得慷慨壯烈,他的弱點也暴露得非常明顯,自身沒有意識到本身的缺欠。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為眾多悲劇人物立傳,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讚揚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後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筆下的虞卿、范雎、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窮愁中著書立說,或歷經磨難而愈加堅強,或身被刑戮而自負其材,欲有所用。所述這些苦難的經歷都帶有悲劇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馬遷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根源時,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以及命運不可捉摸、難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傳》中慨嘆“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覆強調“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豈非命也哉!”對於像蕭何、陳平那樣的幸運兒,司馬遷認為他們的人生偶然性中體現出歷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對歷史潮流的順應使他們扮演英雄的角色,命運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是難解的謎。而從那些悲劇人物身上,司馬遷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和人生的不確定、不公平和難以理解。司馬遷還通過為悲劇人物立傳。揭示了異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吳起為了當上魯國將軍而殺妻,未為卿相而母死不歸,名韁利鎖把他變成一個刻暴少恩之人,最終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績與人性的嚴重異化形成直接衝突。張耳、陳余早年為刎頸之交,後來卻反目為仇,也是利慾把他們拆開。
《史記》富有傳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跡,穿插許多怪異反常的事情,以及神靈的出沒,用以預示秦帝國末日的到來。寫漢高祖發跡,則用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醉斬巨蛇等傳說顯示其靈異。除了荒誕不經的傳說之外,《史記》所寫的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為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身不復見,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張良是位傳奇人物,文中出現的商山四皓同樣來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記》中的許多故事都疏離常規,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傳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貴,竇姬本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卻陰錯陽差成了皇后。這些宮廷故事也是表現人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但它釀成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田單列傳》的傳主田單是一位智謀之士,這篇傳記寫了一系列的奇謀奇計,尤其是用火牛陣大破齊軍一節,更是精彩絕妙。傳記贊語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跡,可謂奇上加奇。《史記》的傳奇性還源於司馬遷敘事寫人的筆法。司馬遷為文疏盪多變,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起滅轉接,令人莫測端倪。《伯夷列傳》是為伯夷、叔齊作傳,但卻以議論開篇,又引許由、卞隨、務光等人為伯夷、叔齊作陪襯,幾乎使人不辨賓主。敘伯夷、叔齊事跡後,在議論中引出顏淵、盜跖,從正反兩方面說開。結尾點題,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才能流傳後世。通篇意到筆隨,縱橫變化,煙雲繚繞,撲朔迷離。《史記》的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特之處,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迴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生傳奇效果。
學術研究
研究概況
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與論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
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後,《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著作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南朝(宋)時裴駰(裴松之子)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史記正義》(唐張守節)。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採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注》、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注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宋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
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注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後刊行的。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隻附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注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注優越。
 《史記探源》(清朝·崔適)
《史記探源》(清朝·崔適)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
近人陳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穫尤多。
匯集《史記》各家注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台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注》稿本。
《史記》工具書,以《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鍾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辭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其他考訂
| 書名 | 作者 | 時間 | 刻本 |
| 史記探源八卷 | 崔適 | 清宣統二年(1910年) | 刻本1 |
| 校刊史記集解索引正義札記五卷 | 張文虎 |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 金陵書局刻本2 |
|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 | 李蔚芬 | 民國 | 刻本3 |
| 史記訂補八卷 | 李笠 | 民國十三年(1924年) | 刻本4 |
| 史記瑣言(諸史瑣言卷一至三) | 沈家本 | 清 | 沈寄簃先生叢書本5 |
| 學古堂日記·史記 | 雷浚 等編 | 清光緒 | 刻本6 |
| 史記校二卷 | 王筠 |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 |
| 史記識誤三卷 | 周尚木 | 民國十七年(1928年) | 石印本7 |
| 史記考證七卷 | 杭世駿 | 民國時期 | 《道古堂外集》刻本8 |
| 史記正訛 | 王元啟 |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 刻本9 |
| 史記校注 | 佚名 | 民國 | 影印本10 |
| 史記拾遺 | 林茂春 | 清 | 稿本11 |
| 史記注補正 | 方苞 | 清 | 廣雅書局刊本12 |
| 史表功比說 | 張錫瑜 | 清 | 廣雅書局刊本13 |
| 景佑本史記校勘記 | 龍良棟 | 台灣影印本14 | |
| 史記毛本正誤 | 丁晏 | 清 | 廣雅書局刊本15 |
後世影響
史學影響
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榜樣,仿效這種體裁修史相繼而起。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里,附在《春秋》之後。自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後世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西晉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將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國小,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鍊,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 。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將相和》。
文學影響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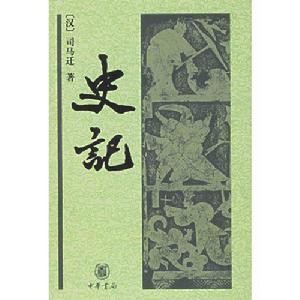 《史記》 中華書局版
《史記》 中華書局版《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後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國縱橫》。
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
作品評價
西漢·劉向、揚雄:然自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西晉·華嶠:遷文直而事核。
西晉·張輔: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唐代·韓愈: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唐代·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十國·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
明代·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明末清初·傑出的點評家金聖歎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
清代·史學家、思想家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梁啓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啓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魯迅:《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毛澤東:“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
近代史學家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現代作家、文學史家鄭振鐸: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路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路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中央編譯局局長師哲: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現在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版本信息
《史記》版本大致分出4系。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img/e/852/nBnauM3X3YDO2ETNzQDNwIT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0QzL3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img/d/3ee/nBnauM3X0AzNwITO4UDO4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g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 第二系:約有4種,分別為南宋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間建陽刊本;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紹興年間淮南東路轉運使司刻九行本。 |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img/3/099/nBnauM3X1QzMyQDNzQDNwIT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0QzL3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 第三系:為集解索隱二家注本,現存2種,一種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張杅刻本,一種則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耿秉重刻張杅本。 |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img/9/fc7/nBnauM3X3QzN3UDO2EDNwUD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xQzL3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史記>>[司馬遷著紀傳體歷史著作] | 第四系:現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夢弼刻二家注本,此後又分為2支。 第一支: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建陽黃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鎧刻本、明柯維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間崇文書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張文虎校本。 第二支較為複雜,這一支的起頭是蒙元中統二年(1261年)刻本,由中統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陽慎獨齋刻本、明建寧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間刻本。而從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國子監刻本和北京國子監刻本。而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則從北監本出。 此外還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閣十七史本,此本為單集解本,據說源自宋刻,但具體底本不詳,據此本重刻的則有清同治年間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書局刻)。 |
作者簡介
司馬遷(前145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 。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