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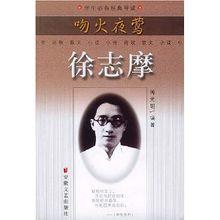 kissing the fire
kissing the fire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那雙銀灰色的眸子,其實他的眸子當然不是銀灰色的,可是我每次看見他那種驚奇的眼神,好像正在猜人生的謎,又好像正在一頁一頁揭開宇宙的神秘,我就覺得他的眼睛真帶了一些銀灰色。他的眼睛又有點像希臘雕像那兩片光滑的,仿佛含有無窮情調的眼睛,我所說銀灰色的感覺也就是這個意思罷。他好像時時刻刻都在驚奇著。人世的悲歡,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瑣事,他都覺得是那么有興致,就是說出悲哀的話時,也不是垂頭喪氣,厭倦於一切了,卻是發現了一朵“惡習之華”,在那兒驚奇著。
三年前,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拿著一根紙菸向一位朋友點燃的紙菸取火,他說道:“kissing the fire”這句話真可以代表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人世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是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過個暗淡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的光輝,數十年的光陰就在計算怎么樣才會不上當裡面消逝去了,結果上了個大當。他卻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為神奇,遍地開滿了春花,難怪他天天驚異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是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
這一回在半空中他對於人世的火焰作最後的一吻了。
故事來源
徐志摩曾經有一次拿著一根紙菸向一位朋友點燃的紙菸取火,他說到:“KISSING THE FIRE。”梁遇春後來在它的同名文章中讚嘆道:“他卻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的烈火,火光依照,化腐臭為神奇。遍地開滿了春花,難怪他天天驚異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是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
 kissing the fire
kissing the fire兩個都結著濃濃憂鬱的文人,華年早逝的驚世才子。一個在天空中與人世的火焰作了驚艷的最後一吻,一個在火光中高誦著讚美詩,把一切後來這擋在了下面。那是一座火焰山!我冒險寫下這個題目時,我無法別闢新徑,別出新意。我無法從這堆火,這座山前繞開。我寧願委身其下,炙身為火,同歌同舞,同歡同慶。我喜歡這兩個人。當我妄圖從沉默的夏蟲,嬌羞的水蓮花中去取出火種,奢想從春雨春草叢淚與笑中去尋覓火的激情時,我失敗了。那火非來自凝固已久的文字本身,而是兩個已化泥土的先人的人格的照耀。一種自由的照耀,“生命的確是像一朵火焰,來去無蹤,無時不是動著。忽然揚焰高飛,忽然銷沉將熄,最後煙消火滅,留下一點殘灰。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來了。”
火焰再也燃不起來了,往著不可諫,後望者為先人哭!
人生若一次過客,來去匆匆。“認識這玲瓏的生,朦朧的死“。然而又有幾人能將浮生若火一樣燃燒,聽那軀體,思想在火中畢剝地響,恣意地唱。浮生若花,浮生若茶,莫不是於一種禪境中覓求一種超脫,而禪的力量卻正是虛無。“無語而來,無語而去了嗎?”能夠浮生若火倒不是說要轟轟烈烈,卻是要明明白白,自由自在。“星火焰這樣無拘無束,順著自己的意志狂奔,才會有生氣,有趣味。” 精神“如火焰一般的飄忽不定,只受裡面的熱力的指揮,衝倒習俗,成見,道德種種和藩籬。一直恣意乾去,任情飛舞,彩繪迸出火花,幻出五彩的美焰。”浮生若火,便是要以一種不確定來對抗既定的秩序,來啟動自我,啟動新生,把自己燃燒的火勢沖天,向洪水猛獸一樣的沖向死板的高山,規矩的房屋,老朽的樹木.火焰飛舞,是節日的禮花,是人性的禮花!
然而願意燒掉自己的人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多的人明明白白地’知曉自己在不明不白地活著.既當走時,還有沒說完的話,如花,零落成泥;如茶,潑灑入土.活只有在夢中,在劇中才會一次次燃起.像普羅米修斯被啄的心臟.火把殘缺不全,映紅的是現實不再的切格瓦拉的眼.
李莫愁在火中狂笑而歌:”問人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那無畏而憾的聲音讓每一個混事的男子汗顏.活本該是男子硬朗的臉,在黑夜時給世界以溫暖.但在這日光燈充斥的世界裡,再也不卻白晝,卻再也沒有了夢想,殘存的幾縷也被流浪者的西風瘦馬馱去了天涯.
傳說中國的火神是祝融.在那場著名的戰爭後,”共工怒而觸不周山”,而祝融也在神話里少了蹤影.他腳下的土地多災多難,烽火曾連天.那沸騰的熱度如果不曾將他喚醒,莫不如宣告他已死亡.而這片土地將新生.在魯迅的菸斗將熄滅的那一剎,在徐志摩的座機爆炸的那一剎,在瞿秋白將去另一世界覓渡的那一剎,在孤島上的詩人瘋狂的那一剎,這片土地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我將替眾先人”kissing the fire”,替愛與恨,替淚與笑,替自由與青春”kissing the fire”.願一切在火中重生!上帝在上,願一切各得其所!
今夜,願那火的呼嘯之聲會穿窗入室.燃盡夜的平庸,伴我入夢!Kissing the fire!
賞析
徐志摩是著名的詩人、學者,“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其意外死亡曾引起巨大反響,在文學界、教育界和新聞界都引發了聲勢浩大的悼念活動。《新月》月刊、《詩刊》等雜誌先後推出過《志摩紀念號》專刊。甚至對新文學頗有成見的《學衡》雜誌也出版過紀念專輯。陸小曼、胡適、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楊振聲、韓湘君、方令孺、儲安平、何家槐、趙景深、張若谷、陳夢家、方瑋德、梁鎮、朱湘、程鼎鑫、虞岫雲、陸費逵、舒新城等眾多作家都發表過悼念文章或哀辭輓聯,以不同方式紀念這位“新月派”的靈魂人物。胡適的《悼念志摩》、凌叔華的《志摩真的不回來了嗎?》都是其中頗具影響的代表性文章。
 徐志摩
徐志摩從相關資料來看,梁遇春和徐志摩似乎並無非常密切的交往,他的悼念文章卻另闢新徑,別具一格,從數量極為可觀的“悼徐”文章中脫穎而出,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這與作者獨特的角度選擇、 超的藝術功力是分不開的。在短短五百多字的篇幅中,作者既沒有詳細、全面地敘述徐志摩的生平事跡,也沒有濃墨重彩地書寫與詩人交往的重大事件,而是通過精選兩個最能體現詩人個性氣質的“特寫鏡頭”,即其“驚奇”的眼神和“吻火”的動作,傳神地勾勒出徐志摩的個性靈魂和精神風貌,表現了作者對詩人親吻人生火焰的人生態度和人格追求的高度讚美。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作者寫人首選眼睛:“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那雙銀灰色的眸子。”文章開篇即告訴我們,作者是通過對與詩人交往的所有情景進行篩選後,才把聚光鏡頭對準了詩人眼睛的。那么詩人的眼睛究竟有何魅力呢?作者先說詩人的眼睛是“銀灰色的”,緊接著又予以否定。其實,這既是作者的錯覺,又是作者最真實的感覺。參詳人生真諦、探索宇宙奧秘的“驚奇的眼神”是詩人眼睛的“神韻”,也是導致作者產生錯覺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對“人世的悲歡”“自然的美景”還是“日常的瑣事”,詩人都對其充滿“驚奇”,這是詩人不同於常人之處。接著,作者又從記憶的倉庫出提取出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動作:吻火。這本是詩人玩笑時的幽默語言。作者卻慧眼獨具,認為“這句話真可以代表他對於人生的態度”,這就是詩人親“吻”生活之“火”、投身生活烈焰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態度。
對詩人而言,“驚奇”的態度和“吻火”的行為是互為表里相互依存的,“驚奇”是“吻火”的原動力,“吻火”則是“驚奇”最徹底的表現。正如文中所寫:“難怪他天天驚奇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是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了,歌唱出人生的神奇。”沒有充滿“驚奇”的迷人之眼,就沒有“吻火”的驚人之舉。最後一節,作者以極為奇特的想像,為第三節的理性思考做出了最佳註腳,把意外失事的悲慘事件想像為徐志摩詩意人生的最壯麗的升華和最徹底的“圓滿”, 表現了對徐志摩人生態度的高度讚美。
問題探究
 kissing the fire
kissing the fire一、本文在表達情感方面有何特色? 與眾多懷念親友的文章有所不同,本文在表達情感方面比較克制。如1931年凌叔華在《晨報·學園》發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來了嗎?》有這樣的文字:“我就不信,志摩,像你這樣一個人肯在這時候撇下我們走了的。平空飛落下來解脫得這般輕靈,直像一朵紅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辭了枝柯,在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許你會選擇這一個,可是,不該是這時候!莫非你(我想在雲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個我們不肯承認他是萬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卻因為不忍甩下我們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動,像久米仙人那樣跌落下來了?我猜對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來了嗎?”凌叔華的文章表現了對痛失好友的錐心之疼和刻骨之思,情感色彩相當濃郁。與凌文相比,本文的情感表現則是克制的和內斂的。 可以肯定,徐志摩的意外死亡對作者的震撼也是很強烈的,否則他不會撰文紀念。但作者在文章中卻仿佛要做“冷血動物”,並沒有放任內心情感自由流淌,只是以素樸無華的筆墨“不動聲色”地刻畫了徐志摩的眼睛和動作,並以此來透視詩人的個性風采和精神靈魂,實現了與詩人心靈的共鳴和深層次溝通,表現了一位精神知音對徐志摩的特殊情感。古語云:“情到深處,每說不出。”(沈德潛《說詩晬語》)本文正收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 二、本文在選材方面有何特色? 本文短小精悍,採用了遺形取神的速寫式技巧來表現人物,筆法洗鍊簡潔而富含表現力。 作者在選材方面顯然是經過縝密思考的,既沒有描寫徐志摩的外在形象,也沒有醉心於詩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是精選了兩個典型的側面──“驚奇”的眼睛和“吻火”的動作,來展示詩人的靈魂和風采。另外,文章在通過細節描寫表現人物性格方面也很成功。“Kissing the fire”是徐志摩在日常生活中脫口而出的幽默玩笑語言,卻能很好地展示徐志摩的個性風采,如出洋留學時間較長,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比較“洋化”,對英語造詣頗高,從口頭到文字時常穿插英文等等,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徐志摩瀟灑自如的生活和風度。 三、文章在結構方面有何特點? 文章結構嚴謹,構思嚴密。簡言之,文章前兩節主要寫詩人的眼睛,後兩節主要寫“吻火”的動作。對詩人徐志摩而言,“驚奇”的眼睛和“吻火”的行為是互為表里的,對人生的“驚奇”是“吻火”的動力,“吻火”的行動是“驚奇”最徹底的表現。沒有“驚奇”的眼睛,就沒有“吻火”的驚人之舉。文章前後兩部分在“人生態度”的層面上實現了有機“對接”。
語言品味
語言質樸無華,平實自然,這是本文在語言方面的最大特色。
《貞一齋詩話》云:“詩求文理能通者,為初學言之也;詩貴修飾能工者,為未成家言之也。其實詩到高妙處,何止於通?到神化處,何嘗求工?”這個觀點很有見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是詩歌語言的追求,也是散文語言的高境界。謝榛《四溟詩話》曰:“自然妙者為上,精工者次之。”本文的語言質樸無華,平實自然,遣詞造句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詞語,但這絲毫沒有妨礙文章的表達效果。作者創作此文時,還只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卻在語言方面達到如此境界,可謂筆墨老辣,造詣不俗。正應了巴金先生那句名言:“文學的最高技巧是無技巧。”從更深層次而言,本文這種平實自然的語言風格與徐志摩自然天真、了無心機的生活風格倒是非常吻合的。
作者簡介
 梁遇春
梁遇春梁遇春(1904-1932),福建福州人。1924年入北京大學英文系,1928年畢業後任教於上海暨南大學、北京大學。大學期間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有譯作二十餘種,其中《英國小品文選》《英國詩歌選》尤為當時青年讀者所喜愛。同時寫作散文,結集出版有《春醪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淚與笑》(上海開明書店1934)。其作品多致力於人生探索與內心世界的剖析,既對現實的黑暗和靈魂的墮落充滿憤慨,又熱忱地追求理想的境界與健全的人性。雖因生活與思想的局限,試圖以淚中的笑面對人世而陷於更深的苦悶,但其批判現實、探索人生的態度始終嚴肅而執著。為文善於捕捉生活中的點滴感受,以博聞強識為根基,馳騁才思,恣意放談;同時注重獨立思辨,敢於標新立異,從人們熟悉的事物中開掘出不同流俗的見地。文體上頗受英國隨筆體散文尤其是蘭姆作品的影響,常以娓娓而談的形式立論駁謬,思辨闡新,展開議論時兼用記敘、描寫、抒情、對話、想像、聯想等藝術手段,且佐以旁徵博引、援古道今,洋洋灑灑而開闔自如,言旨歸一。筆致活潑恣肆而不乏詩意與哲理。唐弢評他走的是“一條快談、縱談、放談的路”,稱之為“文體家”,並贊曰:“文苑裡難得有像他那樣的才氣,像他那樣的聰明絕頂,像他那樣的顧盼多姿的風格。”(《晦庵書話·兩本散文》)而廢名評其散文“玲瓏多態,繁華足媚,其蕪雜亦相當”(《淚與笑·序一》),均為中肯之論。
賞析
 吻火
吻火本篇在梁遇春所有的散文中是最短的,而且不屬於純議論性的散文,它是為追悼一個朋友、追悼一個作家所寫的特殊的文字。 為此,我們必須了解一點兒作者與被記寫人之間的關係。梁遇春同徐志摩好像並無很深的來往。從年紀上看,兩人相差有十歲光景。梁遇春還在念書的時候,徐志摩已經是聲名顯赫的詩人。這本身就決定了當全國的文人圈子,或者具體地說是文學界、新聞界、教育界被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郊外党家莊附近的開山失事的訊息所震驚,後來,胡適、梁實秋甚至沈從文都寫有較長的回憶文時,梁遇春卻只能寫如此短短的悼文。梁遇春散文的發表刊物主要是《語絲》《駱駝草》和《新月》三家。單是為《新月》,他在1928年到1929年間就寫了20篇左右的東西,關係不能說不密。徐志摩在上海擔任《新月》的第一任主編也正是1928年3月至1929年7月期間。本文提到“三年前,在上海的時候”,他們兩人的見面即是《新月》在中間扯的線,並且能說明寫《吻火》時梁遇春已經離開上海回到北平了。回憶往往因“距離”而增添色彩,這是一個證明。梁遇春病故是在1932年6月25日,兩人只有半年的睽隔,之後,梁的靈魂也飛升去吻天了。 但是在所有悼念徐志摩的文章里,梁遇春此篇永遠為人注目。文章一共只四段。上來就寫“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那雙銀灰色的眸子”。明明中國人是沒有銀灰色眼珠的,作者緊接著也否定了,但偏偏這么說,使你不能不注意到徐志摩給人的第一印象:他對人生保持的那份“驚奇”和“探索”的目光。他總是充滿天真,要揭開宇宙間的一切“神秘”。“銀灰色”似乎是一種迷茫的、幻想的顏色,正帶有詩意。作者再加上一個比喻來強化這一印象,說徐志摩的眼睛像希臘雕像眼睛,“兩片光滑”,這真是空靈的、含無窮情調的味道。第二段是進一步延伸,既然“時時刻刻都在驚奇著”,他就天天有“興致”。這是徐志摩的生活風格,開朗,明麗,富生氣。悲哀的時候就是悲哀,也不會垂頭喪氣,不會表示厭倦。就是面對醜惡,也不缺少探索的、要弄清究竟的精神。“惡之華”,即“惡之花”,由於我們曾將波特萊爾的著名詩集翻譯成《惡之華》,這裡也是一種借喻。醜的、惡的、悲的、哀的,都用勃勃的朝氣去對待,讓人想起魯迅說的即便是“頹唐”也是“活人的頹唐”那句名言來。到第三段,點出“吻火”的題目。從眼神到處事,再到人生的態度,一層層排進。“吻火”的詞語,得之於作者的親歷,他聽到徐志摩向人借火的時候說出來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現在拿來作徐志摩“人生態度”的一個代表。把人生比做“火”,看似平常,實在包含了深意。因為“火”不僅象徵了人世的明亮、溫暖、熱烈、轟轟烈烈的一面,還有燒灼、破壞、毀滅的一面。所以,作者說有兩種對待“火”(人生)的態度:一種是害怕它灼傷自己,於是“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結果過的是“暗淡的生活”;一種是投身於火,“肯親自吻著這團生龍活虎般的烈火”,結果是生活中哪怕遇到“腐臭”,烈火也會化它為神奇,人生就會“開滿了春花”。徐志摩是肯“吻”人生之火的人,所以他天生“驚奇”,眼睛像希臘雕像的眼睛,同前面的兩段意思作了總的照應。這裡讚美的顯然已經超出了徐志摩,而是包括一切達到如此人生境界的人。 文章寫到這裡,雖然漂亮,究竟許多人也是可以寫得出的。惟有最後一段別人想不到,而且只一句:“這一回在半空中他對於人世的火焰作最後的一吻了。”突然作結,仿佛留下了繞樑的餘音,久久不息。這確實是一種奇想,借火抽菸是與火親近,用嘴用舌,現在是轟隆一聲巨響,徐志摩全身在烈火中騰空而起,是與火融為一體了!這種壯烈的場面,如果作者不是一樣具有“吻火”精神的人,那就單見火葬的酷烈,哪裡能聯想出人生的神奇,鋪陳出這樣一篇火熱的文字呢。 全文建築在“吻火”這一比喻之上。借紀念徐志摩,讚頌一種人生精神。梁遇春對徐志摩的印象和感覺,純是他個人的。是別人心裡能感應到的徐志摩,卻不是人人能寫出的徐志摩。而且這裡的徐志摩,並不是他的完整的人格,現實生活里的徐志摩,我們現在根據有關的傳記材料,可以描繪出比本文複雜得多的一個詩人的面目來。比如徐志摩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他的重友情和廣交朋友的性格,富同情心,隨和,對女性的浪漫主義和想像力等等。但梁遇春這篇紀念文字取其一點,不及其餘,單寫他與“火”的關係,單寫他的積極的人生態度(應當說,徐志摩的人生態度也不是那么單純、單一的),構成一篇美麗的足夠傳世的散文。在散文的運思方面,表層上似乎是記寫人物,實際也沒有使用多少敘述,如同梁遇春大部分的議論性美文,本文作為非議論文,內在的脈路依然是埋藏著一個莊嚴的理念,即人應當如何生活,對人生應當抱何態度,表明作者對人的很高的期望。不過,題旨儘管嚴肅,寫起來,梁遇春仍然是真正的小品文好手,可以瀟灑自如,能夠想像飛騰。特別是本篇又做到了乾淨、簡練,逗人遐想,所謂笑談真理,是他的文字的絕大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