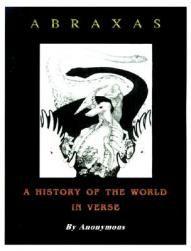心理學家榮格(C.G.Jung)經常在他的作品中提到靈知主義者,他託名巴西里德(Basilides)13)寫過一個冥想短文《向死者的七篇布道文》(The 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
夜晚,死者站在牆邊哭泣:
我們本應認識神。但神在哪裡?
神死了嗎?
神沒有死。現在,永遠,他活著。
這是一位你們不認識的神,因為人類已經忘記了他。
我們稱呼他的名字ABRAXAS。
Abraxas站在太陽之上,站在魔鬼之上。
這是不可能的可能,不真實的實在。
如果普累羅麻是一個存在,那么Abraxas就是它的顯現。
死者於是大聲喧譁,因為他們是基督徒。
Abraxas生出了真理和謊言、善與惡、光明與黑暗,
用同一話話、同一個動作。
為什麼說Abraxas是可怕的?
他是愛,也是愛的謀殺者。
他是聖人,也是聖人的背叛者。
他是白天最亮的光,也是瘋子的最黑的夜。
這首小詩中的這位自相矛盾的Abraxas就成了後來的“自我”(the self),在隨後的四十年中,榮格把它當作“a complexio opposotorum”(對立面的結合) 加以反覆討論。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是通過意識對無意識(包括黑暗的“陰影”的一面)的吸收而達到並趨向於“完整”的境地的。因此,榮格對靈知主義者堅持“惡是一種積極的本能”這一點深感興趣。他讚許地寫道:“靈知主義者詳盡地討論了惡的問題。”“惡從哪裡來?”——惡來自於以“不完美的、虛榮、無知、無能的德穆革與善的、完美的、靈性的神”相對立。在《唉翁》(Aion)一書中,榮格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對這個神話加以闡述:“這位無知的德穆革把自己想像為最高的神,這表明了自我(ego)的困惑情緒,即,當自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無視於它已經被更上一層的權威所罷免的事實時所感受到的困惑情緒...這種無法描述的‘完整’存在於意識與無意識過程的相加,在於內在的自我-心靈(ego-psyche)的對立,即我所謂的自我(self)。”榮格的心理學象許多靈知派的文獻那樣描寫了分裂成碎片的自我的圖景,並且與他們一樣在這些碎片中找到了神的形象。
二十世紀的許多作家都構畫了這種心理學式的靈知主義。黑塞於一九二五年發表的《德米安》(Demian),就是在接受了榮格的心理分析之後寫成的。這篇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構造了一個榮格的原形(Jungian Achetypes)的寓言。強有力的人物德米安的出現是要模糊一切年齡、性別、倫理的界線。他是“出奇地與眾不同”。他告訴那位對靈知派修正聖經感到不安的英雄,指出“有骨氣的人願意接受聖經故事中的不公平待遇。”德米安還象榮格式的靈知派那樣,推動他的英雄去超越他對於現實的有限視野。“一個將要出生的人必須先摧毀一個世界”,然後飛往神,這個神“的名字是Abraxas,把神性的要素與惡魔的要素結合起來。”德米安其實是代表了這位英雄的自我的一個方面,因為小說的結尾部分模糊了“他者”與“內在者”之間的區分。在神秘的、同性戀式的幻象中,這兩個角色融為一體。黑塞的隨後的一篇小說《荒原狼》(Steppenwolf)描寫了一個人物,居住在“這個陌生的世界...無家可歸的荒原狼,一個狐獨的人。”荒原狼暗示了古代靈知主義者的一個最令人驚異的意象,看到“整個人類生活乃是最初的母親的一場痛苦而不幸的流產,是自然界的劇烈而悽慘的災難。”與“自然”(黑塞把它等同於“粗俗的習俗”)相對抗的乃是“趨向於上帝的...精神。”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荒原狼發現這種對抗更為複雜,不僅僅是兩個,而是有上千個靈魂在與他一起喧鬧,“一片潛能與衝動的混亂。”回應他的努力,荒原狼得到了一個心理學式的、很現代的信息:“你嚮往拋棄這個世界、進入到另一個逾時間的世界中去。當然,你知道這個世界隱藏在什麼地方。唯有在你自身當中存在著這個另外的實在。”
黑塞的這些小說是二十世紀極為重要的一種文學類型的早期形式:即在通往心靈王國的旅程中所發現的外部世界與內心實在之間的衝突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以當作“靈知派”的作品來閱讀,這是不足為奇的。其中有一些,比如萊辛的《下降到地獄簡述》(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辛辣地抨擊了平庸的生活。她的小說不提倡走向完全人格的整合,相反,它限制英雄的分裂了的心靈的幻想,以免犧牲他的精神“健康”。他的內在旅程帶領這位英雄進入到外空的神話的土地,然後又作為諸神的信使回到地面。主人公奮力抓住這個現實,抵抗他的精神病醫生的藥物和休克療法,這個過程是用典型的靈知派的隱喻——醒和睡、遺忘和回憶——來加以描寫的。
這也是一個巫術用語,相當於希臘字的“365”,也就是一年當中日子的數目。神秘學家及巫師、祭師等等,都將這個字雕刻在寶石上面,以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護身符。
Abraxas也是一個同時兼有善與惡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