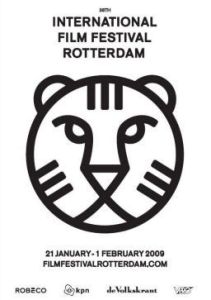電影節介紹
 第38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第38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第六代導演張元憑藉影片《北京雜種》於1993年獲22屆荷蘭鹿特丹電影節“最有希望導演獎”,他的另一部作品《兒子》(1995年)獲25界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另一位第六代導演婁燁的影片《蘇州河》(1999年)獲“金虎獎”。2006年,中國電影《賴小子》再次獲得“金虎獎”。
2019年1月9日,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公布競賽單元入圍名單,中國年輕導演朱聲仄的《現在完成時》成為8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唯一華語作品。
電影節
 電影節圖示
電影節圖示鹿特丹電影節(IFFR)是對中國電影,確切說是對中國獨立電影最重要的一個西方電影節,卻很少被這個行業之外的人所了解。當年王小帥、張元、何建軍等人剛起步的時候,他們那幾部等於是開啟了中國獨立電影時代的作品都曾在這裡展示過;1994年,電影局下文封殺田壯壯,王小帥,張元,吳文光等七個導演的“七君子事件”就是他們“私自”參加這個電影節的直接後果。電影節有一個HBF基金,專門資助開發中國家的電影製作,中國那些為人所知的獨立電影導演們,幾乎每一個都得到過它的資助,從張元,何建軍,王小帥,丁建成到賈樟柯,幾乎是一個可以貫穿起中國獨立電影發展史的名單。鹿特丹在荷蘭西部,一個在二戰的廢墟上重建起來的港口城市。它以現代建築設計聞名,大概因為整個城市提供了這樣一個巨大的實驗場。但街上所見更多還是高層玻璃幕牆和公寓式住宅,這樣的景觀,若不是電影節,平時很難聚集如此多的人到這裡來。但這些每年一月末二月初聚到一起來的人,其實也只需在一個小的區域裡活動。
電影節發展
前身
 鹿特丹
鹿特丹1972年夏,資深影迷和影展策劃休伯·巴爾斯(HUBERTBALS)在自己的家鄉鹿特丹城組織了一場被媒體評論為“相當先鋒”的電影展映活動,選映的作品多是歐美獨立製作和先鋒作品,觀眾不過寥寥十數人——這就是鹿特丹國際電影節(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ROTTERDAM,簡稱IFFR)的前身。
改革
 Gerwin Tamsma
Gerwin Tamsma發展
38年以來,IFFR依舊能夠走在全球視覺工業的風口浪尖,憑藉的正是對世界各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新晉青年導演的關注和扶持。而鹿特丹毫不妥協的選片標準和對全球獨立影業視覺語彙變化的關注非但未令電影節成為曲高和寡的小眾事件,反而成就了每年伊始鹿特丹城乃至荷蘭全國引以為傲的電影盛事;IFFR也與坎城、柏林、威尼斯、洛加諾(瑞士)一起被譽為歐洲五大電影節之一,在主要來自於鹿特丹市政府與贊助商的資金支持下,每屆的鹿特丹影展都不斷做出自我革新,對以青年人為創作主體的獨立電影和視覺實驗始終不離不棄。影展本身因為它選片的視野、展映影片質素和先鋒精神培養了一批自己的忠實影迷,而各國青年導演也把鹿特丹視作他們與世界尤其是歐洲對話的前沿陣地。
現狀
到現在,鹿特丹的發展壯大是近十幾年的事情,除了本國政府和基金會的支持,也和HBF在開發中國家發揮的持續的影響力有關。它到現在已經資助了600多個項目,每年提供兩次申請,按不同的製作階段給作品提供1到3萬歐元不等的輔助金。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年度預算達到了480萬歐元,分別來自政府基金、企業贊助和票房;參展作品一度達到300部,近兩年都限制在250左右,他們聲稱質量永遠比數量更重要。包括媒體和產業場,每天最多可以有27個影院(廳)同時展開放映,每個廳4-5場,這樣每個作品都可以放映2-4輪。
在歐洲,關於IFFR,有一種說法是它是坎城唯一有所忌憚的電影節。的確,鹿特丹有一種鮮明的左派立場,而坎城,包括努力步坎城後塵的柏林和威尼斯顯然都太主流了。主流有主流的標準和趣味,這正是鹿特丹反對的。它總是把自己和“獨立”“反叛”“實驗”這樣的詞聯繫在一起,儘量容納各種風格,把每種嘗試都當作電影的一種可能性;它在總體傾向上顯示出來的,絕不是一種優雅的趣味,相反這裡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直接和生硬的,正如這個電影節本身品性的不易消化。這種立場當然不是說,而是做出來的。
獎項設定
 韓傑《賴小子》勇奪鹿特丹電影節金虎獎
韓傑《賴小子》勇奪鹿特丹電影節金虎獎荷蘭鹿特丹電影節(IFFR)宣揚的是個人主義,是年輕人的能量。它的核心部分老虎獎競賽單元,就是針對年輕作者的,十五部作品只接受處女作或第二部作品,老虎獎一共三個,也不分高下。這在全世界電影節都少見,除了充分說明他們反對標準,以鼓勵為先以外,至少還有效避免了評審們意見的折衷和折衷導致的平庸。鹿特丹的左派立場,更明確地表現在對開發中國家電影的支持。
到現在為止,中國差不多有三十個項目獲得過這筆錢的資助。難得得是,HBF還是與時俱進的,從去年開始,他們專門為DV電影立項,每個入選項目可以獲得兩萬歐元的製作費,眾所周知,用這筆錢在中國完成一部DV作品,象現在最經常看到的那種,現實題材,沒多少人,也沒大場面,還是綽綽有餘的。鹿特丹的HBF和歐洲其它面向開發中國家的電影基金相比,如法國的南方基金(FondsSudCinéma)和德國的世界電影基金(WorldCinemaFund),是條件最少,門檻最低,因此最具慈善性質的一個,它資助的電影,很多都是沒有市場能力的,不可能進入本地院線發行,令投資者得到回報,而對後兩者,一部成本太低,缺乏市場能力的電影,從開始就是不可能被選擇的。這種狀況可能和當地藝術電影市場的能力相關,但無論如何是一個事實。
電影節選片人
 電影節的logo,一個可愛的小老虎頭在歐洲,威尼斯是金獅,柏林是金熊,鹿特丹是金虎
電影節的logo,一個可愛的小老虎頭在歐洲,威尼斯是金獅,柏林是金熊,鹿特丹是金虎 鹿特丹電影節的選片人之一厄文(GerwinTamsma)總是帶著一臉謙遜的笑容而不失風度地出現在不少亞洲影片的首映禮上……在影片開始介紹年輕導演,在放映結束主持問題環節(Q&A),言談中不失荷蘭人特有的堅毅,還總能感覺到他的坦誠和幽默。
選片人的職責遠非表面上看來這般簡單,鹿特丹如此緊密而充滿驚喜的排片計畫可以看做是各位選片人和選片顧問(ADVISOR)在更為廣闊的區域選片網路中互相配合的工作成果,雖則這些選片人的低調在場與影院與普通工作人員、志願者無異,可他們可說是影展真正的幕後推動力。交談中,厄文和我分享了更多對於自己工作、中國獨立電影和鹿特丹電影節的意見。
“選片人和選片顧問還有片探會和電影節主席一道為電影節選擇影片。鹿特丹的6位選片人每個人都會負責特定的區域,但是當然絕不會僅僅局限於自己的單元,比如這次我也同時會負責短片單元”。厄文說,對於類似於多倫多電影節和鹿特丹電影節這樣的影展來說,選片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且這種趨勢會保持下去。對於電影節來說,慣例一般是主席負責選片(儘管其實通常他們並不會真的負責全部單元),但眾所周知,鹿特丹的規矩是幾位選片人與主席密切合作選片。
電影節特點
 電影節圖片
電影節圖片1972年6月第一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開幕的時候,只有17位觀眾參加了這個簇新影展的首場放映,儘管開幕儀式因為現場冷清而被迫取消,這卻絲毫沒有影響到當時的影展策劃人休伯·伯斯(HUUBBALS)的鬥志,他認為如果假以時日,誕生之初就被貼上“非常具有實驗精神”標籤的鹿特丹電影節不但會成為鹿特丹這個歐洲首位海港重鎮的文化坐標,也會以絕世獨立的姿態為世界電影文化揚起一面旗幟……時至今日,後來移期在陰鬱冬日舉辦的鹿特丹電影節已經成為世界上觀眾人數第2位的頂級影展,07年(1月24日到2月4日之間舉辦)的觀眾人數就已經達到36.7萬——鹿特丹電影節也成長為形式多元的高素質獨立製作、藝術電影和實驗電影面向世界最重要的展映和交易平台之一,它尤其偏愛來自“南方”即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亞洲的獨立新人新作(同時也有若干單元專門展映歐美藝術影片)——這種固執不從眾的口味堅持37年來似乎未曾動搖過,甚至逐年膨脹的觀眾數會令前任主席不無擔心,認為過分的大眾化會影響電影節本身自我標榜的另類口味。
歷屆獲獎
何建軍:《懸戀》1994年獲鹿特丹電影節影評人獎。
 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張元:《北京雜種》1993年獲鹿特丹電影節“最有希望導演獎”。
《兒子》1996年獲得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
婁燁:《蘇州河》2000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新銳導演獎
李康生:《不見》2004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金虎獎。
韓傑:《賴小子》2006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金虎獎。
禾家:《大地》2009年獲得鹿特丹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蔡成傑:《北方一片蒼茫》2018年獲得第47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