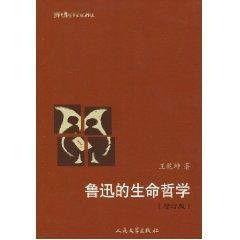作者簡介
王乾坤,祖籍山東曲阜,1952年生於湖北天門,從小在鄉下長大。1982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省直機關,一年後,即調至武漢市社會積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現任該院哲學所研究員、所長。能標誌十多年來研究路跡的著述有:《論詭辯論與辯證法的同一性》(1982)、《論人道主義之爭的方法論分歧》(1983)、《人在工業化過程中理性與情感的分裂》(1987)、《離開了個性自由無以界定“五四”傳統》(1989)、《思想家的魯迅》(1992與人合著)、《由中間尋找無限》(1996)等。
作品簡介
對於“民族魂”魯迅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門顯學。歷來的魯迅研究者基本為文學研究者,而本書則是一部哲學研究者撰寫的魯迅研究專著。作者多角度、多層次地切入對魯迅的“生命哲學”的探究,透闢而深刻地體認、闡釋了魯迅這位思想文化巨人的生命哲學所獨有的文化內涵,精神意蘊和價值取向。
致讀者
有一種猛禽,古時名“梟”,俗稱“貓頭鷹”。它習性古怪:黑夜活動,白晝棲息;即使睡去,也睜著一隻眼睛。這獨異的生活方式,使它擁有了與眾不同的目光和視野。貓頭鷹飛翔時悄無聲息,偶爾發出一兩聲慘叫,難免令人驚悚。
在希臘神話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爾的詞典里,它是哲思的別名;而在魯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徵。魯迅一生都在尋找中國的貓頭鷹。他雖不擅丹青,卻描畫過貓頭鷹的圖案。我們選取其中的一幅,作為叢書的標誌。
我們渴慕智慧,我們企求新聲。這便是“貓頭鷹學術文叢”的由來。
編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書本目錄
自序
美籍華裔學者王浩先生在《中國和西方哲學》中稱:“魯迅和王國維都在文學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內容上,魯迅更能創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的生活。應該說魯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個廣義的哲學家。”這是我所讀的著名哲學家中,唯一這樣稱為魯迅者,所以印象很深。一位以數理邏輯、數學哲學為業的學者有如許的人文眼光,讓人佩服。
不過,本書以哲學為題,卻絲毫沒有將魯迅作為哲學家研究的意思。以其殊異的生命性情,將其歸於任何體制性的“家”都是不盡妥帖的。在不算長的生涯中,他當然也做“家”們所做的事,比如說,也研究學術,也當教師,也寫小說,也編雜誌,也弄翻譯,並且做得很認真,富有成就。然而有如盧梭、尼采,他不願意以任何一種“家”(甚至包括“文學家”)的角色定位自己。任何一種實體性目標對他都構不成生命衝動,任何一種“家”的成功對他都沒有根本性的慰藉效力。他無疑屬於那種來到世間就沒有準備成“家”的天才。
然而,他又決不是中國歷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遙者。他討厭於此,而終生“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守護著所謂人之“自性”的東西。這東西不僅不是任何可以由“家”、“門”、“功業”、“目標”之類所能代替的對象,也不是靠菩提樹下求道、面壁千仞地悟道所能濟事。他的法子是用“無所有”消解一切實體性希望,孤魂野鬼一般地在一種似路非路的人生之路上,無休止地踉蹌前行,以不斷的“走”顯證其信守。同時,他決不獨善其身,而冷靜地觀察著、洞悟著這個世界,並天真地、不識時務地向世人報告他所獨識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訊息,從而把他的“私有財產”或“奢侈品”撒向人間。領受這份財富並不容易,他因此而成為異類。
不管是以蘇格拉底、西塞羅等之“學習死亡”,還是以康德追問“人是什麼”,以及薩特、海德格爾們之尋回個人“存在”,抑或以中國古代的“致良知”來界說哲學,都可以如是說:在中國本世紀不多的思想人物中,魯迅當屬最具哲學精神氣質的人物之列。然而,他不是“哲學家”。
他的精神天馬行空,兩腳卻立於苦難的大地。他稟著高傲的精神情懷,憎惡流俗,詛咒庸眾,乃“平均人”或“一般人”之死敵,卻同時深深地摯愛著被欺侮和被蹂躪的奴隸,並且自覺地從士大夫中叛逃出來而成為奴隸的朋友。這使他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無法歸類的一個人、一個思想者。
反觀中國幾千年的精神資源,無論如何,魯迅是一篇獨異的故事,一個不曾有過的結構。然而,生活中偏偏就常有這樣的事:一個人們自以為最熟悉的人往往可能正是自己最不熟悉者。在相當的程度上可以說,魯迅對於我們就是這樣一種人。雖然他已經死了六十年,雖然對他的研究被稱為“顯學”。
我常常驚訝於這種自明,然而我把自明當起點。
一個人不可能完全地進入另一個人。所以我對本書的設計,主要是個人性的讀解,以便在這個過程中,使自己對這樣一個人物變得熟悉一些。當然,我同時也贊同“人同此心”的說法,否則大家就不可以合稱為“人類”。因此在寫書之中,也含有另一重期許。
正如書名所示,這裡所讀解的是魯迅的生命哲學。因它所提交給讀者的,是一種生命類型的個案考察。從學術上說,當然也不妨看作生命哲學、思想史的一例個案研究。不過,這一取向,並非通常所謂技術“角度”的選擇,而純然是與魯迅的相遇所決定的。一個世紀之前,在德、法等歐洲國家出現了“生命哲學”流派。德國的狄爾泰作為創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學”一詞。這種哲學對本世紀的中國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中的柏格森在“五四”前後就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名字,很多派別的學者與之有關。然而本書的取名與此無關,也不準備重拾這些歷史的話題,雖然二者在實際上不無聯繫。這裡所謂“生命哲學”主要是一種範圍上的限定。無非是說,它所求解的,是魯迅對生命的一種哲學態度。就事論事,別無深意。
生命哲學最好的相遇方式是無言,尤其是不宜作理論邏輯的鋪張。這也許是此類性質的對話不同於其它學術研究的一個地方。筆者本來願意像很多讀書人那樣,與書本神交,如是足矣。無奈一個以職業謀食者,不管願意不願意,必須“完成工作量”,必須有“學術”、“理論”的闡述,而且必須形成“著作”。更無奈何的還在於,自己無法徹底切斷對“概念木乃伊”的偏好;我對它的恨與愛同在,並在總量上相等。
一旦有了這許多矛盾、雜念和人性上的弱點,在體式上就注定免不了“妥協”、變通和後現代主義者反感的結構性製作。我已經盡了努力,以便與述說對象大體保持一個相諧的風格。但我知道沒能做到這一點。比如說,中國既有的話語模式顯然不夠支持對於魯迅的闡釋,為了幫助理解,不得不涉及到一些西方人物,不得不借用他們的一些學術概念。我相信,這樣做在精神總體上未失大端,但有時難免損卻原旨。從學術言,這種相異是應該辨析的,然而,倘若過多過細地說明或註疏,又會節外生枝,拖泥帶水,把題旨沖淡,讓人不知所云。因此,只好兩弊之中取其輕。
如上都是我的不徹底處。開脫著說吧,也是“學術”或語言本身的短處,甚至是生而為人的麻煩。我無法徹底克服其弊與煩,徹底克服很可能就會同歸於盡。我顯然做不到這樣灑脫,至少現在。何況同歸於盡根本就不是一種選擇,而是整個取消問題本身。我只希望讀者不要過分拘泥於本書的言述方式或結構,一如後文要提到的:將其當作過河即拆的橋。
第一章終極的消解與眷注
一、一個前導性話題
二、“中間物”辯
三、生命——時間觀
四、“消解”,而非“勾銷”
第二章古今中西之間
一、中庸之道
二、邏各斯主義與道
三、新神思宗
四、佛緣
第三章自由與他由
一、“朕歸於我”
二、“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三、“眾數”與“物質”
第四章自律與他律
一、不能含糊的“聲音”
二、“偉大的審問者”和“偉大的犯人”
三、沉淪與“忽然驚醒”
四、聲發自心
五、良知:存在論的和價值論的
第五章勇氣:出死入生
一、價值與勇氣
二、“無所希望”
三、拒絕逍遙
四、創作的慰藉
第六章苦難與愛
一、第二視力
二、摩羅:為愛而反叛
三、偉大的俄羅斯
四、以流血的心去愛
五、“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卻”
第七章毀滅中的大歡喜
一、雙重的被告
二、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
三、意志為死亡立法
四、人生的路
五、關於崇高的判斷
第八章盛滿黑暗的光明——讀《野草》
一、夢與人生
二、深淵的夢魘
三、例解
四、叫出無愛和無所可愛的悲哀
後記
本書的思想當然醞釀已久,然而它的寫作來於一個很偶然的推動。
1996年在上海開會,朋友孫郁和我聊天,說他一直注意著我魯迅研究,但覺得不好捉摸,至今沒有從中理出一個思路。這個說法使我很有些慚愧不安。
人都有天性,我的天性是很多事能不乾就不乾或能拖則拖。文章有沒有讀者、銷路怎樣之類的事我一向不怎么掛心。一個作者沒有權利也不應該要讀者注意你。你說你以為然的話,別人聽他以為然的道理;倘若互不搭界,於己於人,都沒有必要認真。但是,倘若真心關愛著你的讀者朋友為你失望,卻心安理得,無動於衷,這恐怕多少也有點問題,說不過去的。正好此後沒事,於是下決心寫一組論文,儘可能通暢地把自己的思路檢討、梳理一下。幾個月下來,竟一氣寫了六萬餘字的《魯迅世界的哲。學讀解》,連載於北京的《魯迅研究月刊》。發表到“之五”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培元先生來電話,希望在此基礎上,充實一下結集出版,尤其囑我最好對《野草》作一些解說。這樣,我只得有頭無尾,中斷連載,按照著作結構來重新布局謀篇、遣詞造句……這就是本書的來由。
所以這本書得首先獻給孫郁、王培元二位先生。沒有他們,這項工作顯然至今還歸在“能不乾就不乾或能拖則拖”之列。文字遠播四方,對己對人並非一定就是幸事,然而得到友情卻肯定是幸事。
據說,寫書一般都應有假想讀者,然而一直到此刻,我也不知自己講話的對象應該定於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生命哲學有關。這是我寫作中常想到的。所以我的對象很渺茫。就像一個望著天花板或者牆壁發言的演說者,我只有儘可能平實地說著自己的話,平靜地求解著我的對象(當然也在無意中塑造著我自身的經驗)。不過眼前也不時閃現十幾雙(為師的和為友的,活著的與死去的,相識的與不曾謀面的)殷殷相勸的眼睛,這倒是真的。這些眼睛流瀉出來的關愛之情和期待之光,在慵怠之中曾給我以鞭策,甚至在某些章節還影響到了我的敘述方式。所以我不能不獻給他們。也許,他們中有人讀後會搖頭。這不打緊,為什麼一定要點頭呢?為什麼一定要別人同意你呢?
這些眼睛有多大的讀者代表性,很難懸揣,我想多少總還會有一些的吧。這十幾雙眼睛以前不就是陌生的么?那么好,就連同我的感激,一起奉獻給他們——我的新朋友,我的新讀者。
弄這樣一種跨時空、跨學科而且是生命哲學性的著述,超過了我的境界和能力。僅僅是想到這工作得有人做,於是也就做了。其問題不難想像,對此我不想多說什麼逃脫責任的廢話。自製的果子只能由自己吞食。無論它苦還是甜,澀還是酸。然而由於天生的粗心(我相信是天生,因此我常懷疑是否適合於學術研究),加上結稿期電腦屢屢搗亂,對技術上的錯誤雖然下了比行文痛苦十倍的功夫,仍然事倍功半。到了最後,夫人看不過去,不得不援手鼎力而救正之,舉家合圍,但恐怕也難免有不少漏網者。為此造成的差錯,敢請讀者鑑諒。雖然它同樣由我負責。
著者
199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