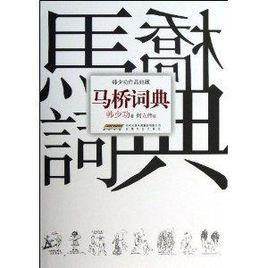內容簡介
《韓少功作品典藏:馬橋詞典》是中國作家韓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按照詞典的形式,收錄了一個虛構的湖南村莊馬橋弓人的115個詞條,這些辭彙部分也是作者所虛構(如暈街)。《韓少功作品典藏:馬橋詞典》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曾榮獲“上海市第四屆中、長篇小說優秀大獎”中的長篇小說一等獎。
作者簡介
韓少功,當代著名作家。1953年出生,湖南長沙人,現居海南。1977年正式開始文學創作,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海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省作協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月蘭》《飛過藍天》《誘惑》《空城》《謀殺》《爸爸爸》等,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暗示》等,散文隨筆集《夜行者夢語》《聖戰與遊戲》《靈魂的聲音》等,翻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另有傳記文學、詩歌、翻譯、評論等作品多種。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上海中長篇小說大獎、台灣最佳圖書獎等獎勵。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意、荷等文字。《馬橋詞典》入選《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作家曾獲“法蘭西文藝騎士獎章”
圖書目錄
一畫
一九四八年(續)
二畫
九袋
三畫
三毛
三月三
三秒
虧元
馬同意
馬橋弓
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馬疤子(續)
小哥(以及其他)
鄉氣
下(以及穿山鏡)
四畫
天安門
不和氣
不和氣(續)
開眼
月口
公地(以及母田)
公家
雙獅滾繡球
火焰
五畫
龍
龍(續)
打車子
打玄講
打起發
打醮
民主倉(囚犯的用法)
白話
台灣
漢奸
歸元(歸完)
發歌
六畫
老表
夷邊
壓字
同鍋
紅花爹爹
紅娘子
朱牙土
企屍
江
軍頭蚊
問書
七畫
走鬼親
呀哇嘴巴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八畫
現
楓鬼
肯
羅江
官路
話份
憐相
怪器
放轉生
放藤
放鍋
寶氣
寶氣(續)
泡皮(以及其他)
九畫
科學
茹飯(春天的用法)
梔子花,茉莉花
掛欄
背釘
貴生
賤
荊界瓜
結草箍
狠
神
神仙府(以及爛桿子)
覺
覺覺佬
洪老闆
津巴佬
十畫
萵瑋
根
格
破腦(以及其他)
哩咯啷
暈街
豺猛子
流逝
漿
冤頭
罷園
十一畫
夢婆
黃皮
黃茅瘴
甜
清明雨
十二畫
散發
黑相公
黑相公(續)
隔鍋兄弟
蠻子(以及羅家蠻)
渠
道學
十三畫
碘酊
嗯
煞
十四畫以上
模範(晴天的用法)
滿天紅
撞紅
顏茶
嬲
飄魂
嘴煞(以及翻腳板的)
磨咒
懈
懶(男人的用法)
醒
後記
附錄一文學有副多疑的面孔——2011年2月國際紐曼華語文學獎授獎晚宴致辭
附錄二語言的表情與命運——2004年3月在香港國際英語文學節上的主題演講
附錄三《馬橋詞典》評價摘要
後記
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後,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麼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么。”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么、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么?”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歷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辭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自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冬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緻、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人國語。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裡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御製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裡的人說起國語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只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瞅嘔啞鞏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國語無法照亮的暗夜裡。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國語。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我進人現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只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國語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國語化了,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它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正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乾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國語談論,也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隻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剷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0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0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面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三結合”、“豆效票”、“老話”、“成分”……一批辭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澱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裡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裡流通一樣。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還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里說。即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栓釋。當然,他們一旦進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不會在意識的暗層里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呢?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國語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營、歧很、歧義、歧視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下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也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裡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覆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這只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里各種各樣的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 1995年12月
序言
應安徽文藝出版社邀約,我的兩部長篇作品在這裡成套再版。餘下的《山南水北》《日夜書》等,也擬在今後適當時機納入。
這些作品的體裁定位多少有些模糊。有的更靠近小說。但小說里有散文;有的更靠近散文,但散文里有小說。多年來,我對俄國文學中只區分“散文”與“韻文”的傳統饒有興趣,也相信以四大古典名著為代表的中國小說傳統來自散文,與歐洲小說傳統來自戲劇形成了觸目的差異。既如此,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寫作人,接續本土文學的審美源流,在全球化多元競放的格局之下,尋求某些異類的體裁特點和表現形式,哪怕寫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哪怕碰個頭破血流,是否也值得一試?
這就是上述作品的緣起,也是我有時候更願意用“寫作”“敘事”一類概念來取代“小說”的緣由。另一番考慮是,長篇與短篇不僅有長度區別,還有效能的不同側重。作為一種大容量,長篇作品理應承擔一種體系性的感知和立言,不能只是短篇的拉長;理應是對世道人心的多角度和多層次剖示,相當於一次對記憶和想像的“大體檢”。在這一過程中,尿檢、血檢、胸透、B超、cT、MR等手段全方位地啟動,並非黑心醫院宰客的虛招濫套,一般情況下是因為醫生遇到了疑難,遇到了大問題。
長篇就是處理大問題的常用工具。優秀的長篇作品一般都具有內在的大結構,以回應時代和社會中重大而艱難的挑戰。所謂“重大”,是指作品必涉及大多數人充滿痛感的境遇和感受,不能止於太太的減肥之憂或書生的悶騷之苦,不宜遊戲於一地雞毛——哪怕這些東西在短篇作品裡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所謂“艱難”,是指作者通常糾纏於兩難的糾結,甚至是自我對抗的苦鬥,承擔著精神前沿的巨大風險,大多時候很難用對或錯、黑或白、yes或no的舉牌表態來及時裁決——哪怕這種裁決的簡單明快,在不少短篇作品裡在所難免不必苛責。中外文學史上的托爾斯泰、曹雪芹等前輩,就是這種為難自己的行家、敢於在深水區遠航的高手,使長篇的體裁能量得到了一次次最好的釋放。我對這種偉大的文學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感謝好友何立偉先生為我的作品配圖。
感謝讀者們的閱讀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