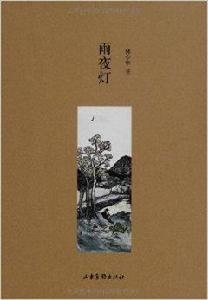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雨夜燈(精)》由林少華著,主要內容:我的故鄉遠在千里之外。可我仍然看見了故鄉的雲,故鄉的雨,故鄉的燈。看見了那座小山村的夜雨孤燈,看見祖父正在燈下哼著什麼謠曲編筐編蓆子,看見燈下母親映在泥巴牆上納鞋底的身影,甚至看見了當年的自己……
此刻,故鄉也在下雨嗎?那盞煤油燈還在嗎?童年的夢?是夢又不是夢,不是夢又是夢。那是存放著的童年的夢,存放在夜晚,存放在下雨的夜晚,存放在彌散著雨夜昏黃燈光的書房中。我覺得,自己最終還是要返回那個小山村,返回故鄉。因此,這裡存放的不僅僅是童年的夢,也是自己現在的夢。
作者簡介
林少華,著名文學翻譯家,學者。祖籍山東蓬萊,生於吉林九台,畢業於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曾在暨南大學、日本長崎縣立大學任教,現為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外國文藝》編委等職。譯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餘種,廣為流布,影響深遠。
圖書目錄
寫在前面
不想回城
無法回遊的“鮭魚”
往日故鄉的臘月
拜年:難忘磕頭
春節的喜鵲
夜半聽雨
倪萍的姥姥和我的姥姥
青州的柿子
永恆的風景
“初戀”:我的第一份工作
醉臥錢塘
鄉間使生活更美好
不想回城
城鄉差別和牙醫
保守也是優勢
一貧如洗和“一富如洗”
“香車美女”和三輪摩托
並非另類的婚禮
換了人間
中國何必在舌尖
“高牆”與“雞蛋”之間的困惑
城管的眼睛和我們的眼睛
領導說“蒲公英是雜草”
貪官其實很可憐
警車開道與“迴避·肅靜”
我為什麼要改洗腳館為圖書館
中國何必在舌尖
有錢人“比較研究”
數量關乎尊嚴
農村:拒絕兒子
車:買還是不買,這是個問題
“少不入川
“甄娠體”和“杜甫很忙”
候機大廳里的講演
美女有樹好看嗎?
三個杯:四個人
足球與高俅
公路收費站的微笑
教育就是留著燈
致人大校長公開信
夢醒時分:“教師節能不能取消?”
朱校長和“牛”校長
清華教授何以絕食
讀“道”:大學之道、為師之道
屈原缺席端午節
文化與《圍城》
指標:一切浪漫情調的死敵
“211”與血統論
教育就是“留著燈”
放飛季節:拒絕庸俗
驚心動魄的七個字
復旦的心靈
秋天,未名湖畔
冰雪“哈軍工”
詩意正在失去
八十年代:貧窮與奢侈
文化回眸:《獨唱團》與“羊羔體”
詩意正在失去
“處長”和我:誰錯了?
我的另兩隻眼睛
傳播源於愛
春天:偉大的母親
麻將PK書:誰輸?
來生的選擇
鐵生永生
史鐵生的母親
中日空姐“比較研究”
空姐和“語言學教授”
嗚呼《關雲長》
村上春樹何以中意陳英雄
“蟹料理”席間的錯位
“班花”與日本人的婚禮
《青島晚報》:永遠的槐花
中年是一部小說
村上的“小確幸”和我的“中確幸”
歪打正著:我的文學翻譯之路
序言
寫在前面
也許你喜歡華燈初上的黃昏街頭,喜歡萬家燈火的入夜城區。我也並非不喜歡,但我更喜歡夜深人靜時分書房那盞孤燈。若窗外響起淅淅瀝瀝的雨聲,我往往擲筆於案,走去兩排書櫥的夾角,蜷縮在小沙發上,捧一杯清茶,在雨聲中任憑自己的思緒跑得很遠很遠。倏爾由遠而近,倏爾由近而遠。
記得南宋詩人蔣捷有一首詞《虞美人·聽雨》:“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雨或許是同樣的雨,但聽雨的場所變了,由歌樓而客舟而僧廬。年齡亦由少年而壯年而老年,最後定格在老年聽雨僧廬。我則聽雨書房。沒有紅燭昏羅帳的孟浪,沒有斷雁西風的悲涼。不過,想必因為同樣鬢已星星,“悲歡離合總無情”,庶幾近之。
夜雨關情之作,李商隱的詩更加廣為人知:“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寫得真好,世界第一。拿兩個諾貝爾文學獎都不過分。
如今,李商隱不在了,蔣捷不在了。所幸雨還在,夜還在,燭也還在。雨、夜、燭(燈)、書房,四者構成一個充分自足的世界、一個完整無缺的情境。不是嗎?白天的雨是不屬於自己的,甚至是妨礙自己的他者。不僅白天的雨,而且白天本身也好像很難屬於自己。屬於政治,屬於經濟,屬於公眾,屬於征戰與拼搏,唯獨不屬於自己。但雨夜不同,夜的細雨不同。夜雨具有極重的私人性質,是專門為自己、為每一個獨處男女下的雨。雨絲、雨滴從高高的天空雲層穿過沉沉的夜幕,輕輕划過書房的檐前,或者微微叩擊燈光隱約的玻璃窗扇,仿佛向你我傳遞種種樣樣的信息,講述種種樣樣的故事,天外的,遠方的,近鄰的,地表地下的……至少,雨沒有忽略宇宙間這顆小小的行星上蜷縮在書房角落的微乎其微的自己——我不由得湧起一股莫可言喻的感動。
驀然,我想起了已經去世兩年多的史鐵生。鐵生說夜晚是心的故鄉,存放著童年的夢。是啊,故鄉!“那故鄉的風和故鄉的雲,為我撫去創痕。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我的故鄉呢?我的故鄉遠在千里之外。可我仍然看見了故鄉的雲,故鄉的雨,故鄉的燈。看見了那座小山村的夜雨孤燈,看見祖父正在燈下哼著什麼謠曲編筐編蓆子,看見燈下母親映在泥巴牆上納鞋底的身影。甚至看見了我自己。看見自己算怎么回事呢?但那個人分明是自己——一盞煤油燈下,自己正趴在炕角矮桌上抄錄書上的漂亮句子。油越來越少,燈越來越暗,頭越來越低。忽然,“刺啦”一聲,燈火苗燒著額前的頭髮,燒出一股好像燒麻雀的特殊焦糊味兒。俄爾,屋角搪瓷臉盆“咚”一聲響起滴水聲。我知道,外面的雨肯定下大了,屋頂漏雨了。草房,多年沒苫了,苫不起。生活不是抄在本本上的漂亮句子。可我歸終必須感謝那些漂亮句子,是那些漂亮句子使我對山間輕盈的晨霧和天邊亮麗的晚霞始終保持不息的感動和審美激情。是她們拉我走出那座小山村,把我推向華燈初上的都市街衢。
此刻,故鄉也在下雨嗎?那盞煤油燈還在嗎?童年的夢?是夢又不是夢,不是夢又是夢。鐵生說得不錯,那是存放著的童年的夢,存放在夜晚,存放在下雨的夜晚,存放在彌散著雨夜昏黃燈光的書房中。我覺得,自己最終還是要返回那個小山村,返回故鄉。因此,這裡存放的不僅僅是童年的夢,也是自己現在的夢。
鐵生上面的話沒有說完,他接著說道:“夜晚是人獨對蒼天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來?我能不能不來,以及能不能再來?”三個追問,大體說了三生:前生、今生、來生。夜雨孤燈,坐擁書城,恐怕任何人都會不期然想到這個神秘而重大的命題。作為宗教命題是有解的,而作為哲學和人生命題則是無解的。特別是來生:能不能再來?鐵生沒有明確回答,但他說了這樣一句:“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種形態。”鐵生的今生已經結束了。那么他的“生”之形態究竟是怎樣一種形態?鐵生夫人陳希米日前出了一本書《讓“死”活下去》,以其特殊身份和特殊情感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回答。但我所關心的,更是鐵生實際上能不能再來,逝者能不能再來。
想到這裡,我走去窗前,拉開窗,面對無邊的夜空和無盡的雨絲沉思良久。不管怎樣,我還是相信靈魂,相信靈魂的不死和永恆。
當然,我在雨夜燈下想此外還想了許許多多,其中一部分物化成了你手中的這本小書。
2013年4月10日於窺海齋
時青島垂柳初綠玉蘭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