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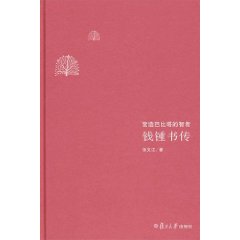 錢鍾書傳:營造巴比塔的智者
錢鍾書傳:營造巴比塔的智者目錄
自序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學時代
(1910—1938)
一、“我家江水初發源”
二、從清華到牛津(上)
三、從清華到牛津(下)
第二章 意園神樓
(1939—1949)
一、在創作和評論兩路精進
二、《圍城》意象
三、“咳唾隨風生珠玉”——《談藝錄》
第三章 滄浪之水
(1950—1965)
一、“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二、碧海掣鯨——《宋詩選注》
第四章 槎通碧漢
(1966—1978)
一、“衣帶漸寬終不悔”
二、天 琳琅(上)——《管錐編》四種文獻結構
三、天 琳琅(下)——《管錐編》十部書簡義
第五章 群峰之巔
(1979—1989)
一、躍上成就的高峰
二、“吾猶昔人,非昔人也”(上)——《談藝錄》補訂本
三、“吾猶昔人,非昔人也”(下)——《七綴集》
結語 中國現代文化和錢鍾書
一、中國現代文化和錢鍾書
二、若干可能存在的局限
附錄一 錢鍾書著作的分期和系統
一、寫作分期
二、著作系統
附錄二 錢鍾書簡易年表
後記
又記
文摘
第三章 滄浪之水(1950—1965)
一、“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總的形勢是向上的。但是在政治和文藝界,已經發生了若干次大的鬥爭。僅以文藝界而論,在1949—1956年間,比較大的運動已經有了三次: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對《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如果分析這三次批判的性質,就會發現它們的矛頭所指各有不同,而且一次比一次嚴峻:批判《武訓傳》“行乞興學”的“至勇至仁”,批判的根子是封建主義,其時間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觀點,雖然從《紅樓夢研究》作者俞平伯入手,而總根則是“五四”以後居於“右翼”的代表人物胡適;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其根子已涉及“五四”以後同居於“左翼”文化陣營內部的不同派別。這裡歷史和邏輯似乎有著一致:三次批判對象由封建階級、“五四”啟蒙主義到三十年代左翼,呈現由外而內的狀態;而且從批評、幫助到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後在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由內向外翻出,終於達到高峰,衍成1957年涉及全民的反右派運動,並成為後來更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驅,前十七年的形勢也就此轉折。在三次批判之間,還有過一些其他小運動,比如在1951—1952年間,和全國規模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結合,有過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的方式還是相當和風細雨的,但對思想也有深刻的觸動。這種做法後來被稱為“洗腦筋”,楊絳後來用長篇小說描寫了這次運動,把它稱作“洗澡”。“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新環境的考驗。
錢鍾書1949年舉家北上,定居北京。清華是他的母校,他來到的是一個熟悉的舊環境;但他所身處的已是一個新時代,這裡對他來說又是一個新環境。新環境不得不影響著他,他也作著調節和適應,智慧增長了。在新時代的清華園裡,錢鍾書教過書,帶過研究生,他非凡的才華和驚人的記憶力,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接近傳奇。當時在清華讀書的人回憶道:
四十年代,筆者在京就學時,錢先生任教於清華大學。他的驚人記憶力,在學生中廣為流傳。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學從圖書館回寢室大叫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驚問怎么回事,原來這位同學是研究唐詩的,他為了考證一個典故,從圖書館遍尋未獲,正巧碰到錢鍾書先生,便上前請教。錢先生笑著對他說,你到那一個架子的那一層,那一本書中便可查到這個典故。這位同學按圖索驥,果然找到了這個典故,因此他大為驚訝。
錢鍾書先生筆鋒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雖然他待人寬厚,常開玩笑,但他學識之淵博,卻使學生產生敬畏之感。還記得有位同學在學期末交了一份讀書報告,他沒有好好思考,只是從幾十本書中東抄西湊成一篇,草草交賬。錢先生看後,不加一句評語,卻把他所引的話的出處一一注出。當時大家表面都笑話這位同學,但從心裡不得不佩服錢先生的學識和記憶力。
錢鍾書其時已經不發表作品了,只是靜靜地讀書,既用人類文化知識豐富著自己,也適應著時代。在清華園裡,錢鍾書也接待過客人,例如傅雷夫婦、黃裳等。傅雷來訪時,錢鍾書夫婦曾受吳晗之託請他留在清華,但傅雷沒有聽從,還是回到了上海。。黃裳來訪時,見到的是一個典型的夜讀情景。黃裳回憶道:
住在清華園裡的名教授,算來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錢鍾書。第二天吳晗要趕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訪問安排在第三天的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我找到他的住處,他和楊絳兩位住著一所教授住宅,他倆也坐在客廳里,好像沒有生火,也許是火爐不旺,只覺得冷得很,整個客廳沒有任何家具,越發顯得空落落的。中間放了一隻挺講究的西餐長台,另外就是兩把椅子。此外,沒有了。長台上,堆著兩疊外文書和用藍布硬套裝著的線裝書,都是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他們夫婦就靜靜地對坐在長台兩端讀書。是我這個不速之客打破了這個典型的夜讀環境。
這裡提到的吳晗當時已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並且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來又擔任北京市副市長。黃裳回憶中的“第二天吳晗要趕回城去”云云,指吳晗參與政務工作的繁忙,這和錢鍾書的靜靜讀書,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黃裳回憶中提到西餐長台旁的“兩把椅子”,實際上是記憶失誤。錢鍾書後來糾正說,那間大房間確有一隻講究的西餐長台,但椅子是沒有的,那只不過兩隻豎擺著的木箱。。“椅子”原來是“木箱”,可見當時條件的確簡陋。而“冷板凳”竟然也有“椅子”和“木箱”的區別,這裡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更正,錢氏夫婦事事求真的細膩風格,也可見一斑。錢鍾書北上後,繼續廣收博覽地讀書,當時清華所藏的西文圖書,幾乎每一本的書卡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似乎不用藏書,因為都藏在腦子裡了。錢鍾書在1950年還生過一場病,滬上的友人如冒效魯等對此也極為關心,冒氏有《訊默存疾》一詩寄京,詩中用了維摩詰、孔夫子等典故,那是尊重這位大學問家的身份了。
P6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