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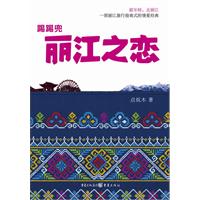 簡單而又繁華的圖案道不盡那愛情中的絕望
簡單而又繁華的圖案道不盡那愛情中的絕望趁年輕,去麗江。
現在,你就可以開始這場刻骨銘心的麗江情愛之旅。去觸摸四方街的古樸、拉市海的澄澈、瀘沽湖的柔軟和玉龍雪山的純淨;去感受幽靜的束河小鎮、迷離的櫻花塢、古老的東巴象形文字和納西族對生死的執著信仰;透過一對戀人的眼睛,麗江的風情在且行且止中,流溢出她令人著迷的神秘與神聖。
兩個在麗江相遇的年輕人,踢踢兜和點炕木,背負著各自的秘密,絕望地愛上了對方,渴望在短短的十天裡,耗盡一生的愛。
相愛不逢時,刻骨亦枉然。此去與君別,生死兩不知。
當他們的旅行結束,各自離開麗江,這座古城的角角落落,因為留下了他們相愛過的痕跡,而變得更加令人神往。
你說情色,她說憂傷。
趁年輕,去麗江。
作者簡介
炕木,原名華楠,創意人,出版人,寫作者,古怪的服裝設計師。
1974年,出生在一座山下的一條河邊。
17歲,進入北方某工科大學,在火車上第一次看見平原。
18歲,退學回高中,改習文科。
19歲,考入中山大學,睡上鋪,中午下床吃飯,下午踢球,晚上看夜場錄像,夜半寫詩。
23歲,大學畢業,當過一年老師,因喜歡上課打瞌睡,誤人子弟,遂引咎辭職。
26歲,因喜歡大眾傳播,創辦上海華與華行銷諮詢公司,並將其發展為國內收費最貴、最成功的諮詢公司之一。
31歲,因喜歡讀書,創辦北京讀客圖書公司,連續推出《藏地密碼》等超級暢銷書,使讀客成為國內單行本平均銷量最大、最成功的圖書公司。
35歲,突然領悟了人與服裝的關係,相信服裝可以直抵我們的內心,創辦古怪服裝品牌ttdou。
書摘插圖
1
我是一個熱愛痕跡的人,熱愛所有的痕跡。我覺得痕跡是這個世界上最美最迷人的東西。
我侄兒4歲的時候在我新房的白牆上留下的髒手印,幾年了我都沒有擦掉。我讓它留在那裡。孩子一點點長高。等有一天他已經長成一個小伙子的時候,我再把牆角的那個手印指給他看。剛高過他膝蓋的手印,他要蹲下來才會看到。那個痕跡還在那裡,是他小時候留下的,清晰得就像剛剛留下。那么,他的童年就會穿越時間
來到他自己面前。
但我現在心裡想著的這個人,她什麼痕跡也沒有給我留下。
現在是凌晨兩點,我從床上醒來,打開一瓶紅酒,決定開始寫這個故事:
先寫那天晚上我和文雯在辦公室做愛。
兩年來,我們在我辦公室做愛的次數肯定比在床上的次數多,多很多。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我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見過面了。
我永遠都在加班。
“我們都很久沒有在白天見面了。”有時候文雯會這樣抱怨一句。
那天晚上,又是凌晨兩點,我們在辦公室做完愛,躺在牆角的沙發上,看著窗戶外面的夜上海,車水馬龍,霓虹閃爍。
文雯說:“你還要加班多久啊?”
“最多一個小時。”我說。
“我是問你還要這樣加班多少年啊?”
“三年。”我看著窗外說。
“六年前你就是這樣說的。”
“那最多還有六年吧。”
我轉過頭來,開始撫摸她的頭髮。按我的經驗,不管文雯有多生氣或者低落,或者發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脾氣,只要我看著她的眼睛,輕輕地在她頭髮上摸一把,她就會安靜下來,嘴角就會往上翹,甜甜地笑起來。
我把這個絕活稱為“摸一把頭髮秘訣”。
但這次居然不靈。她把頭輕輕轉向一邊,躲開我的手,一縷髮絲像鰻魚一樣從我指縫間滑走。她站起來,赤裸著身體,走到玻璃幕牆邊上。
“我不會等你多久的。”她說。
那一瞬間我沉默了兩秒。
我站起來走到她身後,緊緊地貼著她,把她壓在玻璃幕牆上,將她的乳房壓平在玻璃上。
“玻璃好冰啊!”文雯說。說完推著玻璃直起身來。
我雙手繞到她胸前,在那兩個小傢伙掉下來之前一把把它們接住,手指輕輕挑逗。文雯很快就進入了狀態,喘息起來——辦公室里瀰漫起文雯低低的呻吟之聲。
我的人生沒有理想,只有計畫。
我的計畫只有兩個:一個是掙足夠多的錢;另一個是和文雯結婚,生兩個小孩。
但這兩個計畫現在看來有些衝突:要掙錢就顧不了文雯,要顧文雯就掙不了足夠的錢。關鍵是,我還沒想好多少錢才算足夠。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目標是一個無限不循環小數的最後一個數字,我以為我在飛速地接近它,其實它在無限遙遠的地方。其實它根本不存在。
做完愛之後,文雯開始彎腰收拾剛才她被我脫下來,散亂在地上的衣服。
丁字褲,是她專為今天晚上見我而買的。一個多小時以前在我替她脫下這條褲子以前,她還站在我的辦公桌上跳艷舞。現在她把它穿上了。
胸罩,是我買給她的。春節的時候我去歐洲出差,為了彌補不能跟她一起過新年的歉疚,我買了一套香奈兒的內衣送給她。她現在把它穿上了。她先把罩杯托在乳房下面,然後雙手捋著吊帶,伸到後背,開始系帶扣;扣好之後又伸手進去將那對可愛的小兔子樣活潑潑的乳房往中間託了一托。
那對小可愛被她收起來了,過會兒她還會把它們帶走。
牛仔褲,是我們一年多以前一起在恒隆廣場買的。那天她抱怨說已經很久沒有跟我一起逛街了,當時她正在辦公室里陪我一起吃便當。我說:“現在就去逛吧。二十分鐘,我們去逛二十分鐘。”然後我們就匆匆買了這條范思哲的牛仔褲。二十分鐘後我就回來了,一大堆事情還等著我。
T恤,我從來沒見過,是一件新的白色T恤。很別致的一件T恤,衣服兜里冒出一條叼著骨頭的小狗。為了能夠馬上開始處理明天一早要發到歐洲和南非的幾個傳真,我開始謹小慎微地調整氣氛,
以便她穿好衣服親吻一下就走人。
“T恤不錯。”
“喔。”
她穿好衣服後,情緒不是太好,看我的眼神有點傷感。
“我該走了嗎?”她問。
我沒說話,湊上去親了她一下,其實是默認她該走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接著處理。
文雯低下頭,嗚嗚地說:“我不想這樣了。你給電話我就送上門來,深更半夜還要一個人回去。我算什麼?”
2
一個小時以後,QQ閃了起來。
“還在公司Ⅱ馬?”文雯問。
“你怎么還沒睡?”我說。
“你都沒有問我到家沒有。”
“喔,那你到家沒有?”
“現在還用你問嗎?”
“喔,你已經到家了。”
“唉。”
“早點睡吧。我還有一個明早發的傳真要寫。”
“我們結婚吧。”文雯突然說。
“明天?”
“明天。”
“後天吧,我明天安排一下。”
“那說定了後天。”
“等我查一下。”
“查什麼?”
“查一下後天的安排。”
然後我就趕緊去查日程安排,五雷轟頂。明早8點要開項目籌備會:10點要向董事會匯報工作:11點是一個投標計畫討論;下午1點要跟開普敦的客戶通電話,跟他討論40多個樣品的問題;下午兩點要去工廠,有一批馬上生產的大貨要封樣;後天早上要見法蘭克福來的採購商,接著要開公司業務碰頭會;後天下午要見汕頭來的生產商:後天晚上要見北京來的行業協會會長。
“接下來兩天沒空。”我在QQ上說。
“沒空什麼?”
“沒空結婚啊。”
我打下這幾個字,一摁回車就後悔了。
果然,對話框裡一出現這幾個字後,文雯的QQ頭像就變成了黑白色——她下線了。
我立刻打她電話,被摁斷了。再打,關機。
我開始處理明天一早要發給開普敦的傳真。
寫了很多次開頭,都覺得不對,只好刪掉重來。
突然,外面的門鈴響了。
文雯哭得淚人似的站在玻璃門外。
今晚真是個奇怪到傷心的夜晚。
“我們明天出去旅遊吧。”文雯說。
“你不要生氣。”我說。
“我不是生氣,我是絕望你明白嗎?我在變老你看見了嗎?”
“你怎么會變老呢?你還年輕得很啊。”我趕緊拍馬屁。
“我不是要你說這個。我是要你明白,我不會一直這樣等下去,不會每天一個人在房間裡等一個永遠加班加班加班的人!”
我準備過去實施“摸一把頭髮秘訣”,但手剛一抬起來,就反應過來今晚這招不會管用。手在半空停住,拐了一個彎,摸到自己頭髮上。
那小狗在她T恤的兜里笑嘻嘻地看著我。
“我過來是想告訴你,”文雯嗚鳴地說,“我明天要出去旅遊。”
“去哪裡?”我問。
“我不會告訴你。”
“喔。”我有點無奈。
“我想你明天也出去走走。”文雯說。
“好啊,你去哪裡我都陪你。”我說。
“不要你陪我,我們分別出去。”
“喔?”
“給我們自己十天時間吧。我還不知道是不是要跟你結婚。”文雯說。
“不要賭氣。”我說。
“我不是賭氣啊。”她輕輕地說,“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還愛不愛你。”
“你是愛我的,傻瓜。”我說,“你只是現在自己犯糊塗。”
“各自出去想想,我們還要不要在一起。給我們自己十天時間,如果還想在一起,我們就結婚;如果有一不想了,我們就分手。”
“好吧,”藏說,“出去散散心也好,回來我們就結婚。”
“哎,你也自己想想吧。說不定我明天就會愛上別人。”文雯說。
那晚真是個奇怪的夜晚。
3
兩個小時後,我寫完了所有的傳真和工作安排,把手機壓在一張紙條上。紙條上寫著一行字,給我的秘書的:小聶,這段時間幫我接電話。
收拾完東西,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出自己的辦公室,來到外面的大廳。
大廳里一片昏暗,一個一個的小格子間,每一個都空著。有一台忘記關的電腦,發出淡藍色的螢光,映在不鏽鋼的格子間隔段上。
我一陣恍惚,想起那個格子間就是我到這間公司以後的第一個座位。那是個專供實習生坐的位子,臨近前台和印表機。六年前我就坐在那個座位上,負責資料錄入和給其他同事放列印紙。
“小華,放紙。”不管辦公室的哪一個角落傳來這個聲音,我就會從座位上彈起來,跑到印表機前,放一張A4紙在紙架上,然後才轉過頭來開始搜尋剛才是誰在叫我。等列印的東西從印表機下方吐出來,我就恭恭敬敬地給那位大人送去。
有時候他們嫌麻煩,省掉了“小華”兩個字,只說“放紙”兩個字。
“放紙!”一聽到這兩個字,我就從座位上彈起來,向印表機衝去。
再後來,指令進一步進化,他們只需要大聲說一個“紙”字,我就明白是叫我去放紙,我就從座位上彈起來,向印表機衝去。
他們單說這個“紙”字的時候會稍微拖長一點音。是“紙——”。或者“紙呃!"或者“紙呢?”再或者“紙!紙!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