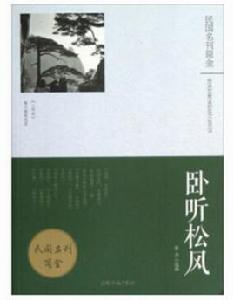內容簡介
《臥聽松風:人間世散文隨筆選萃》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前言
人
林琴南先生
王靜安先生
章太炎先生
記辜鴻銘先生
李叔同
胡適之
知堂先生
劉復
郁達夫豐子愷合論
梁漱溟先生
老舍
記魯彥
黃廬隱
記齊白石
徐悲鴻先生
論
說自我
論真率
說浪漫
談忍
論中國人鄙視歐洲人
論風度與人情
談死
談“本色的美”
談美麗病
談服裝
談迷信
談旅行
論高下
警句
談金錢
書
論讀書與談話
談讀舊書
自序《屐痕處處》
《不驚人集》前記
有不為齋叢書序
《浮生六記》英譯自序
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
書店
北平舊書肆
巴黎的舊書攤
東京的舊書鋪和舊書攤
藝
文言畫
論山水畫
談指頭畫
說牌子曲
灘簧
談桂戲
川戲
靠山調——天津特有的一種歌曲
琵琶小記
刻印小記
草書學說
地
說揚州
芙蓉城
閒話襄陽
湖南雜憶
太湖
浣花溪
塞外點滴——宣化特寫
牛津憶錄
暹羅灣與湄南河
游
登泰山
出昱嶺關記
揚州舊夢寄語堂
焦山望月
秦淮
游牛首山記
贛濱之行
馬達山遊蹤
華茨華斯故鄉遊記
閒
閒
等閒
談閒話
睡的哲學
小病
論玩物不能喪志
弄蟋蟀
試獵記
論煙
談麻將
蜘蛛
蝌蚪
河豚
談“吃田雞”
蘿蔔
相思子
“民國名刊簡金”叢書例言
後記
“民國名刊簡金”叢書例言
晨鐘暮鼓——自古以來,鐘聲總是伴著東升的旭日,宣告黑夜的消逝和新的一天的開始。鐘聲的渾厚、雄壯,帶給人們的感受是:新的希望、新的生機。當新文化運動的鐘聲報導了舊文化舊思想的一統地位的終結後,人們發現,透著新思潮新觀念的氣息、一展新文體新文風的格調的散文園地,也迎來了它的滿園春色。如果說,“五四”運動前後現代散文尚處草創期,尚有那樣多的舊的思想文化桎梏需要進一步衝破,那么,從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前期的十年間,現代散文則步入了一個多彩多姿花團錦簇的時代,正如朱自清先生《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中所說——散文“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屈、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在那眾芳爭妍的散文苑囿中,尤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文體和以周作人、林語堂為代表的“小品文”文體最具影響力。對前者來說,“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十分注重文章的戰鬥性,強調散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而不是“小擺設”。它反映出在當時中國那樣的黑暗時代,“敏感性最強影響力最大的進步的作家們一定有一番新的奮起、新的努力”,決不會像“歸去來兮”的陶淵明那樣“自謂是羲皇上人”而超然物外。
對於大張“性靈文學”旗號的自由主義作家而言,因為“立志做‘秀才’”,不願持久地用肩膀承受“國事”那樣的重負,所以總是希望把散文帶入一種“閒適淡雅”、“和平靜穆”的境界,“百忙中帶入輕筆,嚴重中出以空靈”,追求散文純粹的藝術美、意境美,並不理會那山河破碎時節的“十萬軍聲半夜潮”的氣氛。從理念上說,這般超脫世務牽累、心儀平和沖淡,對散文意境的深入開掘,對散文文風的進一步發展,不是沒有意義。只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猶如此心平氣靜,自成一統,坐看浮雲,閒庭信步,那顯然是一種理論與現實的錯位,理所當然地要遭到學界的激烈反對。尤其抗戰爆發後,這種文學主張也就陷入了明日黃花的境地。
當抗戰的烽火也燃遍整個文學界時,傳統的“儒生無力荷干戈”、只作“艱聲長嘆”的狀態,被現代身兼救亡與啟蒙雙重角色的知識分子所改變。他們手頭的筆,既是喚醒民眾的號角,也是刺向敵人的投槍。這樣,戰鬥性的散文成為這時期散文領域的主流。就其奮勇進擊、鼓舞民心方面看,這種文風具有積極向上的意義,而且其時確也形成了抗戰文藝中暴風驟雨式散文的新氣象。然而,挾帶著激憤、焦躁情緒,在一個相同的主題下,用一種近似的文風,所創作出來的散文勢必缺乏個性,從而顯出了格調單一的弊端。儘管曾有人發出沒有硝煙味的、“與抗戰無關”的文章也應做做的呼籲,但在群起鳴鼓而攻之的氛圍中,那種試圖有所更新、有所恢復戰前已達到一定高度的散文文體、文風的聲調,終究是微弱的。抗戰勝利後,劈頭而來的又是關係到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內戰,使政治關係左右散文創作方向的狀況沒有大的改變,散文除了在嚴肅的主題下體現時代精神外,似乎很難由單一性向多元化嬗變。
有感於現代散文曾取得那般輝煌的成就,也有感於現代散文曾歷經那樣曲折的道路,我們把目光投向了發表散文的重要陣地——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學期刊,試圖從中一覽現代散文發展變遷的概貌,並欣賞到其中最精彩的散文篇章,同時也讓人大致領略不同期刊的思想志趣、文章風格的區別。於是,我們有了分刊分類整理出版舊刊中的散文名作的願望。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中,早已說過選文章之難:選者“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如果選者“眼光如豆”、那可就是一個“文人浩劫”了。儘管我們也深知此中之難,但歲月的塵封湮沒了多少曾經流光溢彩的“金聲玉振”之作,舊刊的面貌今人也已難以知曉,為了使讀者在欣賞舊作的過程中獲得關的享受、品性的陶冶、思想境界的升華和知識面的增廣,也為著免去專業研究者查找舊刊上的某些散文的麻煩,我們還是儘自己所能去遴選,並且也自信基本能選出諸刊中短小散文的精華、反映各刊在散文創作方面的基本風貌。《世說新語·文學》中謂:“潘(岳)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機)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本乎此義,故題叢書名日“民國名刊簡金”。
既是叢書,自有“凡例”之類說明文字:
時間——以散文領域流派紛呈、千帆競發的30年代的文學期刊為主,亦兼顧20年代和40年代。
刊物——首批所選之刊物有:《小說月報》(1921~1931)、《語絲》(1924~1930)、《現代》(1932~1935)、《文飯小品》(1935)、《太白》(1934~1935)、《雜文(質文)》(1935~1936)、《論語》(1932~1937,1946~1949)、《人間世》(1934~1935)、《逸經》(1936~1937)、《魯迅風》(1939)、《萬象》(1941~1945)、《野草》(1940~1943,1946~1949)。
文風——既注重閒適清新、詼諧美妙之作,亦不忽略傷時感事、憂國憂民之文及憤世嫉俗、勇猛奮進之章。對各家各派兼容並包,反映特定時代、特定流派的思想志趣和藝術特點。當然,派別不同,立場有別,某些文章就難免帶有門戶之見,甚而有彼此相互攻訐的文字;並且也不排除個別文章在思想傾向上有偏差的情況,這就需要讀者將文章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去閱讀、去理解了。
作者——名家固不可少,無名作者而有精妙之文亦廣為容納。個別作者後來在思想立場上或許是消極甚至反動的,但他們當時的有些作品卻有進步意義或有較高審美價值,故也適當選錄。
形式——以2000字以內的短小精悍之文為主,亦適當選入(或節選)某些長文。當然有的長篇名作只得忍痛割愛了。一刊(或性質相同的兩刊)之作編為一書,並根據刊物特點,將所選文章分為幾類,如民風世象、雅人深致、百味人生、書里書外……之類。
此外,為便於讀者理解,個別疑難問題作有簡注。但原文文句有不合乎語法者,不加改動;一般的異體字也保持原樣。唯以下幾種情況有所修改:
原刊不規範的標點符號,徑改之;不規範的版式,適當作調整;明顯錯字或不規範字,徑改;疑為錯字或當時通行而現在視為錯字者,酌情用[]標出正字;衍字,直接刪除;漏字,用 >補上。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一切都在變化,都在更新。當新世紀的鐘聲行將敲響,回首那半個世紀前散文園地曾有過的爛漫與輝煌,重溫那個性鮮明、異彩紛呈的美妙篇章,我們感受到了時代風雲撞擊下的心靈震撼、藝術享受中的品性淨化。我們不禁要期待“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新時代的散文華章對以往的超越,我們也堅信,隨著五四運動“‘個人’的發現”的傳統的發揚光大,散文創作更美好的春天必將到來。
(陳益民)
序言
文學期刊的出現,是文學傳播上的大事,也是整個文學史上的大事。先前,詩文寫成,達到讀者,只靠口耳傳誦,筆墨傳抄,既慢又貴且零散;從而,作家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作者與作者、作品與作品的關係,文學與其社會人生背景的關係,文學與其社會人生效果的關係,等等,都是鬆散的,遲緩的,遼遠的,朦朧不明的,難以預計的。即使在名山勝景、郵亭驛館的壁上題寫,在盛會雅集沙龍中吟誦,影響可以擴大一點,經久一點,究竟也很有限。印刷術雖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其用於文學作品,長時期只是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於隨時寫成的單篇文字,除了進學中舉點翰林時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學期刊、民國20年代始有新文學期刊以來,情形大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則以周計,長亦不過以年計,可以剋期印成千萬份,與千萬讀者相見。而且,還有別的作者,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以同一體裁品種或不同體裁品種的作品,同時在一本期刊上與讀者相見。並且這不是“一次性行為”,而是一段時期內總有某個期刊雜誌在那裡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與讀者相見,讀者也可以期待著常在那上面見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這樣,作者就會相當明確地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寫給哪一類讀者看,大致有多少讀者,知道讀者大致會怎樣接受,歡迎不歡迎,考慮要不要適應讀者,或是引導讀者,或是改造讀者,或是有意與讀者為敵;也大致知道自己在這上面將與哪些作者哪些作品為伍,考慮要不要適應他們,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異,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學期刊,所謂“文壇”的“壇”才有了實物,“壇”就是主要由期刊組成的。新文學對舊文學的迅速勝利,就表現在新文學期刊在全國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占領了期刊就是占領了文壇。新文學運動以來,認真努力作舊體詩文的人一直未絕,仍自有其師承流派,也有成就頗高的;然而,他們沒有什麼期刊,偶有幾個也勢孤力薄,不成氣候,所以他們沒有一個“壇”,就顯得潰不成軍了。有了文學期刊所組成的文壇,而後才可能有職業半職業作家。每種文學期刊有一個主編或編輯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進、促退,安排、協調,組織、引導等等方面起著很大作用,在作者與讀者的聯繫中起著很大作用,在作者與文學市場的聯繫中起著很大作用,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學史上所沒有的,他給文學史帶來許多全新的東西。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晨報副刊》,沒有“開心話”這一欄的設立,沒有孫伏園,沒有孫伏園與魯迅的關係,沒有孫伏園善於笑嘻嘻地催稿,就不會有《阿Q正傳》,或者不會在那個時間寫出來,或者不會是現在這個題目這個樣子。《阿Q正傳》如果是在沒有文學期刊之前寫出來的,即使能達到“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也不會在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危懼不安,恐怕以後要罵到自己頭上,從而對作者為誰作種種猜測,多方打聽,先是到處說《阿Q正傳》處處在罵他、後來又逢人便聲明不是罵他這些戲劇效果。甚至,孫伏園如果不是離開北京一段時間,《阿Q正傳》就會比現在長些,阿Q被槍決就會遲些。
研究晚清以來的文學史,特別是研究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史,當然要研究各種別集、總集、長篇專著,但單是這樣還不夠,還必須研究各種文學期刊(以及有文學作品的綜合性期刊)。一個文學期刊,往往大致上體現一個流派、一種主張、一種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業性刊物,也仍然有一個大致共同的傾向。從期刊上,才較易於看清作品的“語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間的關係,作家作品在當時的地位、作用、影響的比較和受讀者重視歡迎的程度的比較。從期刊上,才較易於看清文學流派傾向的全貌,看清一個個文學流派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從期刊上,才較易於看清一個一個文學論爭(也有些不純是文學範圍上論爭)的全貌,看清論爭的起因、發展、結局,看清論爭各方的是非得失。魯迅斥梁實秋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來,時常被舉為魯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寬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當時的有關期刊,才看到其實是梁實秋首先把“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么一個文藝理論上的問題,引到“在電燈桿子上寫‘武裝保衛蘇聯’”的問題,引到“到××黨去領盧布”的問題,給論敵扣上一頂當時千真萬確會招來殺身之禍的紅帽子,這才看得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稱實在還是很寬厚的,這是近來逐漸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學運動以來,可以肯定地說,散文的成就在小說詩歌之上;魯迅、周作人兩個高峰的創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證據。要研究新文學的散文方面的歷史,尤其要研究文學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別還因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無論是再現現實,還是表現自我;是針砭時弊,還是抒寫性靈,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葉,所以更需要從文學期刊上來研究,才能夠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體“語境”中,同一流派傾向中,不同流派傾向的競爭中來理解。
新文學中的新散文,濫觴於《新青年》的“隨感錄”。《新青年》不是文學期刊,後來它一分為三:後期《新青年》繼承了前期的政論而外,《小說月報》繼承了它的文學方面;《語絲》繼承了它的社會文化批判方面。《小說月報》原是鴛鴦蝴蝶派的陣地,是商業性的文學期刊,商務印書館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來接任該刊主編,是鴛鴦蝴蝶派失去了讀者失去了市場的反映;沈雁冰接編後把它徹底改造為文學研究會的陣地,則是新文學的一大勝利。《小說月報》以小說和文學理論為主,其所載的散文隨筆,常常帶著小說的印跡,是後來的社會速寫報告文學的先聲,代表散文的一個重要方面。《語絲》則是第一個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魯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點是充分發揚主體性,任意而談,批判舊的,催促新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後來周氏兄弟分道揚鑣,周作人從“我思故我在”的立場,堅持思想自由、個性自主,在其領導或影響下,出現了《論語》、《人間世》、《逸經》、《文飯小品》等散文隨筆刊物,被論者稱為“閒適派”。魯迅則從“我在故我思”的立場,堅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領導或影響下,出現了《太白》、《雜文》、《魯迅風》、《野草》等雜文小品刊物,被論者稱為“戰鬥派”。這兩個稱呼未必十分貼切準確,但大致可以說,二者正好分別代表《語絲》的一面,是《語絲》的一分為二。二者曾經尖銳對立,今天從文學史的巨觀上看,又未嘗不可以說是合二而一,共同發揚了《語絲》所開創的光輝傳統。此外還有比較中間比較兼容並蓄的《現代》和《萬象》,二者不純是散文刊物,而所載散文亦有相當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說的《新青年》之後的十種新文學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學史上民國時期的主要散文。現在按期刊分別選集,較常見的名家名作,也與同一期刊上較不常見的作家的優秀之作選在一起,這樣就接近於以期刊為載體的散文發展史的“原生形態”,帶露沾泥,生香活色,讀起來自與讀作家專集或他種選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對於愛好散文的讀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來說,這是我們敢於說這套選本有他種選本所不能代替的價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蕪序於碧空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