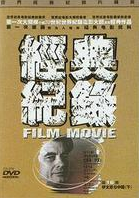簡介
導演 |張同道主演 |尤里斯.伊文思
年份 |2000
地區 |荷蘭
語言 |國語
片長 |30分鐘
色彩 |彩色
影片評價
“文革”時期,由外國人來華拍攝並產生廣泛國際影響的兩部紀錄片,一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二是伊文思和羅麗丹的《愚公移山》。後者歷時5年完成的長達12小時的12集系列片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僅從每集的片名即可略見一斑:《大慶油田》(84分鐘),《上海第三醫藥商店》(75分鐘),《上海電機廠》(131分鐘),《一位婦女,一個家庭》(110分鐘),《漁村》(104分鐘),《一座軍營》(56分鐘),《球的故事》(19分鐘),《秦教授》(12分鐘),《京劇排練》(30分鐘),《北京雜技團練功》(18分鐘),《手工藝藝人》(15分鐘),《對上海的印象》(60分鐘)。即便這些影片在我國上映之初也沒有多少人看過,更不用說今天的年輕人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央電視台近期播出的6集電視系列紀錄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國》(邵振堂導演),將使新老國人有機會看到《愚公移山》(以及伊文思和羅麗丹在中國拍攝的所有影片)的某些片斷。關於《愚公移山》及其兩位導演的話題,本文也只能擷取其中的某些片斷。悠悠故鄉情
在世界電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可以用這樣幾句話進行簡單概括。首先,他是一位紀錄電影先驅,與美國的羅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和蘇聯的吉加·維爾托夫被並稱為四大紀錄電影之父,與其他三位先驅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創作生涯最長,在長達6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拍攝了60餘部影片。其次,他是一位國際主義戰士和詩人,這位“飛翔的荷蘭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其他國家度過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以攝影機為武器聲援它們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在這些國家獲得獨立之後,又熱情謳歌它們的建設成就。第三,他是一位電影教育家,為五大洲的數十個國家培養了大批電影工作者,而且他與弟子的關係超越師生之誼而升華到朋友之情。最後,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38年拍攝《四萬萬人民》到1988年完成《風的故事》,他與中國的交往長達半世紀之久,親切地把中國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伊文思1960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都是與瑪斯琳·羅麗丹合作完成的,此後他的每一次中國之行都與羅麗丹形影相隨。羅麗丹曾經在開創現代紀錄電影先河的法國導演讓·魯什拍攝《夏日紀事》(1960)時擔當過重要角色,親自拍攝過反映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的紀錄片《阿爾及利亞零年》(1962),正是在製作此片的過程中她與伊文思相遇,並且從此成為伊文思的合作夥伴和生活伴侶,她與伊文思的結合也為傳統紀錄電影融入了現代風格。1971年6月,伊文思和羅麗丹應中國政府之邀來到北京,帶著幾部關於法國68年5月事件的影片。周恩來一見到伊文思就問:“你怎么沒帶攝影機來啊?應該在這兒拍幾部影片。”伊文思頓時感到不知所措,雖然他與周恩來已有幾十年的交情,但沒想到周恩來會向他提出一個如此直截了當的提議。周恩來補充說:“反正你還要回來的,你和瑪斯琳利用這段時間參觀參觀中國,把你們帶的片子留下,我們來看看。”
那時,封閉已久的中國正在向世界發出某些開放的信號。當伊文思和羅麗丹在中國參觀的時候,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正在秘密進行美中之間的穿梭外交。伊文思和羅麗丹一直在中國呆到9月份,他們一邊參觀一邊思考在中國拍片的事情。儘管他們還不清楚到底想拍一部什麼樣的影片,但是伊文思認為:“不管怎么說,中國顯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這部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時,中國在國外的聲譽降至最低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續不斷的混亂,除了使人困惑不解之外,還給穩重和有責任感的中國形象抹了黑,西方新聞界更是亂上添亂。向來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的伊文思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重整旗鼓,也深切領會了周恩來的建議,於是準備拍攝一部有關中國的影片以《正視聽》。
將影片拍成什麼樣子,這對伊文思和羅麗丹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探索。當時,他們沒有明確目標。當然,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但在地域遼闊、歷史悠久的國度里發生的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千姿百態,許多問題他們都很不了解。伊文思憂慮的是如何確保影片的獨立性,他的想法與周恩來不謀而合,周恩來想要的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影片,只須以中國做主題。正是出於保證獨立性的考慮,當伊文思提出與中國合拍這部影片時,遭到周恩來的拒絕。伊文思與羅麗丹回到法國後開始了一系列準備工作,除了尋找經費、籌劃製片等活動之外,還在法國多次舉辦有關中國的報告會,收集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聽眾提出的200多個問題,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歸納整理,他們逐步了解到了人們對中國的疑問所在,以及他們對政治、哲學、社會、文化及至古老的黃禍論等諸方面的知識與無知,定見與偏見”。
茫茫心頭怨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羅麗丹再度來到北京,準備開始影片的攝製工作。雖然擁有共和國總理的官方批示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有效協助,拍攝過程仍舊困難重重。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創作觀念的差異,二是有關領導的干預。創作觀念的問題似乎不難解決,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中方創作人員的工作得到了伊文思和羅麗丹的高度讚賞,而來自有關領導的生硬幹預卻讓伊文思和羅麗丹大傷腦筋。這裡所說的有關領導,既包括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也包括攝製組所到之處的地方負責人。江青在伊文思和羅麗丹1971年訪華期間曾經三次接見他們,多次陪同他們觀看樣板戲,向他們傾訴自己的經歷,並且暗示他們為她拍攝一部名為《紅都女皇》的影片。伊文思和羅麗丹無聲地拒絕了為她樹碑立傳的請求,結果是他們在拍攝《愚公移山》過程中遇到了來自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其爪牙的百般阻撓,而且江青在對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國》發動批判運動期間,甚至要求伊文思和羅麗丹明確表態,兩位世界級的電影導演對此一拖了之。伊文思在一本回憶錄中記述了拍攝《愚公移山》時的心頭之怨(本文中的引語,除特別標明外均出自羅伯特·戴斯唐克與伊文思著《尤里斯·伊文思:一種目光的記憶》,法國BFB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已由胡瀕先生譯成中文)。比如,攝製組首先被帶到大寨村,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裡大寨是完美的典型,但在伊文思眼裡:“這裡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無缺,太呆板生硬,讓人感到很不舒服。”這樣的地方恰恰是伊文思試圖極力避免拍攝的。然而,作為早在1938年就來中國拍片、對中國有著相當了解的伊文思還是在那裡作了短暫逗留,拍了一些素材之後隨即轉道北京。可是,在清華大學的拍片經歷同樣使他不滿,比如當伊文思問大學生們上大學之前做什麼工作時,所有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這怎么可能?”伊文思感到失望。當他問這些學生對知識分子從事農業生產的態度時,所有人都稱頌體力勞動,對插秧、養豬之類的農活齊聲稱道,伊文思明白:“這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號,它同我們想拍的東西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經歷更是讓伊文思和羅麗丹啼笑皆非。地方負責人總是把攝製組置於既成事實之中,告訴他們哪兒能拍,哪兒不能拍,哪些場面絕對要拍。伊文思很清楚,這些都是為攝製組安排的陳規俗套,同他所期望表現的中國南轅北轍。在喀什的經歷簡直是登峰造極,伊文思將之稱作“喀什的噩夢”。那裡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以至於曾經在好萊塢工作過的伊文思都不相信華納或者環球公司能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場面:“早晨七點,十字路口與整條街上都擁入了成百名的男女,他們服裝鮮艷,笑容可掬,小學生們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舊如此……在一個商店裡的排演可謂達到了頂點,安居樂業的居民們圍著琳琅滿目的櫃檯來回走動,自由自在地挑選商品。”攝製組所到之處,至少有五六部官方汽車開道,而且地方領導人還為攝製組選定拍攝角度。這些素材沒有編入《愚公移山》,而在大寨和清華大學拍攝的素材被扔進了垃圾堆。
對於拍攝過程中遇到的這類困難,伊文思早就有思想準備。周恩來對他說過:“用不著遮遮掩掩,中國是個窮國,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地域遼闊也改變不了這一事實。我們不能打腫臉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頭來倒霉的還是自己。”他又補充道:“用不著去拍一部粉飾太平的影片,中國是什麼樣兒,你就按什麼樣兒拍。”周恩來是針對伊文思將要遇到的那些念念不忘美化現實的地方領導人說這番話的,他還提醒伊文思和羅麗丹要當心美化現實這個頭號敵人:“只有打好這一仗,你們才能拍出一部好影片來。”伊文思心裡非常明白,美化現實的事本來不足為怪:“人,不管他是原始人還是文明人,社會主義者還是資本主義者,黑人、白人或者黃種人,總是要在客人來時把大門前打掃一番。美化現實也是1971年的中國的情況。”然而凡事總有限度,超出限度就令人難以接受了。另一方面,將真實視為紀錄電影的生命的伊文思恐怕也不會有醜化現實的想法:“要我背著中國,拍攝一部反華、反社會主義、反我自己信仰的影片,我是不會幹的。”
依依愚公幫
伊文思和羅麗丹的拍片活動陷入僵局,他們甚至感到非常絕望。另一方面,深諳中國文化的伊文思明白,此時只有真誠而耐心地等待事情出現轉機,就象中國的古老寓言《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那樣。也許是他的真誠和耐心感動了上蒼,後來事情果然出現了轉機。從新疆回到北京之後,攝製組進行了人員調整,伊文思和羅麗丹已經基本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片了。此後,攝製組在廣闊的中國大地安營紮寨,長期而深入地觀察不同地區與不同社團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覺得要拍攝全面反映中國的影片還應該去西藏,並且多次提出去西藏拍片的請求,考慮到伊文思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哮喘病,中央沒有批准他的請求,伊文思非常不安地對他的翻譯說:“陸,去問問你們的中央,黨中央他是要一個活著的不革命的伊文思,還是要一個死了的革命的伊文思?”(見紀錄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國》第5集陸頌和的回憶)向來將生死置於度外的伊文思所說的這番話應該是肺腑之言。1974年中期,伊文思和羅麗丹一回到法國就開始剪輯120小時的素材。1975年初,他們帶著剪輯完成的7集影片來到北京,一是想為其他幾集補拍一些鏡頭,二是打算將完成的影片放給與他們一起工作過的朋友和拍攝對象觀看,這些影片在北京組織了幾場放映,可是他們拍攝過的人沒有看到。在北京的放映中有一場是帶有生死定奪性質的,那位芭蕾舞演員出身的文化部負責人對這些影片提出了多達61條的修改意見。比如,不應該把頌揚毛澤東的樂曲《東方紅》與下雨的畫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園裡推兒童車的小腳女人的鏡頭剪掉,或者用解說詞說明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有兩個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讓人覺得他們像是做小買賣的,建議剪掉;表現黃浦江的清晨的鏡頭髮灰,會讓人聯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見恐怕要多達上百條。伊文思辯護說:“如果影片中的解說詞有歷史陳述方面的錯誤,或是統計方面的錯誤,我們可以糾正。”
伊文思在事後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當我們為自己辯護時,朋友們,同事們前來為我們打氣,他們要求我們不必理睬那些要求,建議我們帶著影片儘快離開。他們說:‘時局還在變。’而當時我們對中國的內幕毫無所知。此次中國之行,經歷不愉快的三個星期逗留之後,我們最終收拾行裝動身回國。出發那天,四十多位朋友來到機場為我們送行。全體攝製組成員都來了。他們在北京成了‘愚公幫’,我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動人的告別場面,怎能想到它竟發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四十多個送行的人一直走到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們聚集在舷梯下,用雙臂緊緊地擁抱我們,和我們告別,大多數人落下眼淚,我們也無法控制自己。大家都清楚,他們將再度面臨大獄,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這就是中國之行給我留下的最後一個印象:四十雙目光,四十雙高舉的雙臂,一片搖動飛舞的手絹,機艙門就這么關上了。我們帶回了《愚公移山》——這部當權者不願看到的記錄中國的影片。”當然,這裡所說的“當權者”主要應該是指“四人幫”。無論如何,《愚公移山》可謂生逢其時,如果是在1973年或1974年完成和放映的話,恐怕也要像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那樣遭到全國人民的批判。幸運的是,這部影片直到1976年春天才開始在國外上映,那時的“四人幫”已經快要遭到全國人民的批判了,也就顧不上批判這部影片了。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
戀戀中國緣
自1976年3月初開始,《愚公移山》被編排成放映時間大致相當的若干影片組合,在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四家藝術影院同時上映,此片僅在法國的映期就長達6個月。由於滿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閉已久的中國的渴望,義大利、西德、荷蘭、芬蘭、美國、加拿大、巴西以及許多其他國家也爭相購買拷貝和電視播映權,播映後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和評論家的廣泛好評。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愚公移山》在西方博得的喝彩是短暫的。隨著1976年10月中國政局發生巨變,這部影片突然被撤出西方的電影院和電視台。有人開始懷疑這部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實性,有人開始指責它是一部中國製造的官方影片,善良的人認為伊文思和羅麗丹被中國人欺騙了,不友好的人則認為他們幫助中國人欺騙西方。這種情況使伊文思和羅麗丹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甚至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在歐洲找不到工作。可是,伊文思生前絲毫沒有向他的中國朋友們提過這件事,直到1998年羅麗丹來北京參加“紀念伊文思誕辰100周年研討會”時才有所披露:“當時我與伊文思向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影片發行的同時,要不要向觀眾講述我們在中國所經歷的事情?最終我們決定不說自己在中國所遭受的待遇,因為如果說了,我們就好像和那些偏激地批評中國的人站在一起了。現在想來,如果當時說出‘四人幫’當權時我們所受到的部分當權者的某種待遇,這樣也許對中國會更好,可能我們的一些中國朋友正需要國外有一些揭露‘四人幫’的聲音。如果在《愚公移山》發行的時候,我們採取的是這樣的態度,我們就不會在十年之中得不到工作了,也不會有那么多記者對伊文思說那么多難聽的話。”
縱然茫茫心頭怨,依舊戀戀中國緣。《愚公移山》之後,伊文思和羅麗丹在80年代中後期來華拍攝了《風的故事》,講述了一位歐洲老藝術家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這位老藝術家不是別人,正是伊文思。影片的序幕部分,少年伊文思那句“媽媽,我要去中國!”的呼喊,道出了這位藝術家自幼嚮往中國的心聲。這部影片成了世界上最後一位紀錄電影之父的最後傑作。伊文思的“中國緣”可以說是他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的體現,是他在20世紀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不斷抉擇的必然結果。伊文思一生中面臨無數次抉擇:“1917年前後他認識了蘇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選擇了共產主義;1938年他在燃遍抗日戰爭烽火的中國,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了共產黨,並把它介紹給世界;1946年他在作為殖民一方的祖國荷蘭和作為被殖民一方的印度尼西亞之間選擇了印度尼西亞,為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奔走吶喊;60年代,他又在中蘇大論戰中毅然站在中國一邊……”(引自胡瀕《一所流動的“‘直接電影’學校”》,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伊文思抉擇的標準是,始終站在被壓迫的人民的一邊,始終堅信人類的美好理想一定會實現。
11月18日,是伊文思104誕辰周年紀念日。筆者為在法國舉辦中國電影展事宜飛赴巴黎,伊文思的墓前獻上一束鮮花,看望羅麗丹,雖然趕不上帶去登載此文的刊物,但至少可以告訴她,中國的電影人仍在懷念伊文思,中國的電視台仍在播放伊文思與她合作拍攝的《愚公移山》。今天,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就像到鄰家串門一樣,然而誰又能忘記在封閉鎖國的艱難日子裡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愚公移山》呢?2003年法國將舉辦“中國文化年”,2004年中國將舉辦“法國文化年”,屆時當有更多的人重新認識這部非凡影片的非凡意義。
代表作品:
《雨》The Rain,1928《橋》The Bridge,1929
《英雄之歌》Song of Heros,1932
《塞納河》The seine Meets Paris,1957
《西班牙土地》The Spanish Earth,1936
《印度尼西亞在呼喚》Indonesia is Calling,1946
《四萬萬人民》The 400 Million,1938
《早春》Before Spring,1958
《愚公移山》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1976
《風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