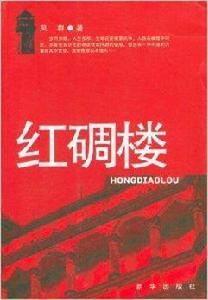內容簡介
《紅碉樓》編輯推薦:歲月如煙,人生多艱。生命在逆境裡抗爭,人性在幽暗中對決。儘管芸芸眾生的命運猶如浮游的迷船,但總有一種不屈的力量在其中貫穿,遂使傳奇永不熄滅……
書評
《紅碉樓》收錄了鳳群11篇小說,是其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這些作品或伸向弔詭的歷史深處,或徜徉在現實底層,或往返於記憶與現實之間,呈現了作家頗為寬闊的敘事視野。從敘事格調上看,它們依然延續了作家一以貫之的審美特質,輕逸而又溫婉,粘稠而又神秘;人物關係若即若離,人物的內心世界卻異常豐饒;故事情節大多曲折迷濛,宛如江南煙雨中的田間小徑。這是“鳳群式”的敘述風格。它決定了鳳群的小說洋溢著陰柔之美,溫潤之美,兼及某種感傷主義的內在韻致。
作者簡介
鳳群,安徽涇縣人。現為廣東五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上個世紀80年代就學於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首屆文學班,在國內刊物發表過大量中短篇小說、散文、電影文學劇本,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文學作品多次獲獎,有的選人作品集。
圖書目錄
序
紅碉樓
立園
小鳥天堂
包裝時代
都市民謠
1986年的愛情
徽州紀事
柴窯瓷瓶
雪崖
謎船
天使的飛行
後記
後記
這本《紅碉樓》是本人第二本小說集,也是我的一個作品自選集。收入其中的十一個中、短篇小說中,只有少數幾篇寫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其餘均為2000年後在國內文學雜誌上陸續發表的一些近作。
1992年,我從內地江南一所師範大學調到廣東五邑大學工作。五邑大學在珠江三角洲西部江門市,這裡毗鄰南中國海,荔風蕉雨,山環水繞,自然環境非常優美。江門又稱五邑,因為地級市江門下轄新會、開平、台山、恩平和鶴山五個縣級區市,故得此名。江門地靈人傑,歷史上不僅出過陳白沙、梁啓超這樣有名的教育家與思想家,司徒美堂這樣的僑領,還出了許多藝術家。僅著名電影人就出了一百多位,如民國年間的黎民偉、胡蝶、陳雲裳,當前走紅影壇的劉德華、梁朝偉、甄子丹等。江門又是著名的中國第一僑鄉,至今開平、台山等地仍然保留了一千多座各個時期海外華僑歸來建造的碉樓,這些碉樓在那個時代的作用主要是防匪患與水患。其外部形態各異集萬國建築之長,蔚為大地奇觀,其中開平碉樓與村落已經列入聯合國文化遺產。另外,江門還是南宋滅亡之地,七百多年前宰相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趙咼跳海自殺的地方,金戈鐵馬折戟沉沙,一個風雨飄搖的王朝在此灰飛煙滅。故五邑大地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地方風物人情濃郁,是個特別有故事的地方。我在此已經生活了二十年,所以很自然地將創作的目光從原來的江南轉移到嶺南這片土地上。在工作之餘,陸續寫了一些取材於五邑地區的文學作品,其中部分小說已收入到這個集子中,作為我對第二故鄉的一種回報。
由於長期在高校工作,教學與科研工作繁重,我的小說創作曾經一度中斷,所以在創作思路及取材立意上難免滯後。但有一點仍然是我所堅持的,我始終認為小說是一種關於敘述的文體,寫小說不只是給讀者講述一個故事,而是作者需要掌握的一種敘述藝術。故事是屬於大眾的,而敘述則是屬於自己的,這也是作者的個性與才華顯露之處。所以寫小說時常令我苦惱的是這個故事用什麼獨特方式去敘述?在這十一篇小說中,本人試圖根據題材的要求在小說敘述上進行多種嘗試,有民間傳統白描敘述、現代多角度重疊敘述以及借鑑電影蒙太奇的敘述等,當然我並沒有忽視故事。文壇長期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故事是屬於通俗文學的,而純文學則可以忽視故事或淡化故事。但我認為故事與敘述並不對立,把好故事讓給通俗文學,似乎不是一種明智的寫作行為。通俗文學與純文學最大的分野之處,應該是通俗文學只注重故事內容,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性,而忽視敘述。純文學則注重敘述,重視用各種敘述方式與技巧去建構這個故事。但純文學如果只有敘述技巧而沒有一個好故事支撐,同樣得不到讀者歡迎的,中外文學史上的許多小說大家,在這兩方面結合得都非常成功。選入這個集子裡的小說,我有意在故事曲折性與敘述多樣性兩者結合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希望能適合各個層次的讀者閱讀。
我的校友、國內著名文學評論家洪治綱教授的序為本書增色不少,在此表示感謝。同時,對本書寫作及出版給予大力支持與幫助的我的親人、編輯、校友、朋友、同事們,表示內心最誠摯的謝意!
希望這個集子能給眾多讀者帶來閱讀的愉悅。這年頭能坐下來耐心讀小說的人已經不是很多了,我也非常感謝你們。
作者
2012年4月
序言
鳳群先生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1984年秋天,當我邁進大學校園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恰巧遇上了一個文學極盛的好時光。後來,我漸漸發現,在那個年代,校園詩人就像王子一樣到處受寵,很多人都對詩歌抱著宗教般的虔誠和痴迷。不寫詩是不可思議的,在中文系,寫詩不只是最為流行的時尚生活,還是對自我才能的一種終極認證。發表一首詩歌,遠比某門功課考了一百分要榮耀得多。
因此,我們對待詩人就像對待天才一樣,從來都是持以最為崇高的文學敬禮。幾乎每一個人都沉迷於詩歌,每一個人都陶醉在詩人的夢鄉里。我也不能例外。於是,我悄悄地將自己的第一首詩投到了校報。感謝鳳群老師,他是校報唯一的副刊編輯。記得當時他將我叫到編輯部,給我面授了許多寫詩的要領,然後幫我修改了那首處女作,並發表在校報上。
這讓我激動了數日,我將之視為命運的酬謝。特殊的年代,讓我遇上了特殊的啟蒙老師,也讓我們從此結下了數十年的師生情誼。事實上,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鳳群先生已經是一位相當活躍的青年作家。記得當時的《中國作家》、《青年文學》等雜誌都發表了他的小說,其中的《謎船》曾轟動一時,許多中文系的師生爭相傳閱,我當然也一一拜讀過。這些小說留給我的印象至今未忘,現代,神秘,充滿了某種輕逸而又靈動的審美氣息。
歲月如梭。二十多年過去之後,我們又先後來到了嶺南,在不同的高校里都從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所不同的是,為了文學評論和研究,我早已拋卻了寫詩的夢想,也喪失了寫詩的激情。而鳳群先生依然堅持做著小說家的夢,並在教學科研之餘,陸續發表了不少小說。這本小說集《紅碉樓》便是見證。
《紅碉樓》收錄了鳳群先生十一篇小說,是其創作中最為精華的部分。這些作品或伸向弔詭的歷史深處,或徜徉在現實的底層,或往返於記憶與現實之間,呈現了作家頗為寬闊的敘事視野。從敘事格調上看,它們依然延續了作家一以貫之的審美特質,輕逸而又溫婉,粘稠而又神秘;人物關係若即若離,人物的內心世界卻異常豐饒;故事情節大多曲折迷濛,宛如江南煙雨中的田間小徑。這是“鳳群式”的敘述風格,它決定了鳳群先生的小說洋溢著陰柔之美,溫潤之美,兼及某種感傷主義的內在韻致。
因此,讀鳳群先生的小說,我們也許不會體驗到燕趙悲歌式的雄渾和蒼涼,也難以感受到血性和彪悍的陽剛之氣,但是,我們卻始終浸潤在一種典雅舒緩的意境中,穿行在各種迷離不清的人物命運里.體會一次又一次繁雜而無序的人生碰撞,感受一種又一種命運的無常和無奈。在《立園》中,鳳群先生曾敘述到:“西揚在本質上是個詩人,他崇尚古典,時常將自己沉浸在那些雜亂無章且又十分清晰的優美境界裡,自己獨自一人去品評其中的況味。那些優雅浪漫而具有古典性質的情境,也時常模糊了歷史與現實在他心中的距離,使他的意識經常重疊於兩個不同的時空而陷於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我以為,這句話其實也是鳳群先生自我氣質的一種寫照。
這種貼近古典而又不乏現代意識的審美追求,使得鳳群先生的小說既顯得細膩、典雅、感傷,擁有宋詞般婉約的氣質,又充滿了某些神秘、奇譎和悖謬的特徵,折射了創作主體的現代哲思。譬如在《紅碉樓》中,作家以嶺南文化中特有的碉樓作為空間載體,將情仇、匪劫、家怨、粵劇、僑眷、自梳女等等,匯聚於一個複雜的故事之中,通過司徒長風、慧儀、十一郎之間的情感糾葛與衝突,展示了民族劫難的大背景下,人性的瘋狂與乖張,命運的無奈與無常。《立園》以一位青年畫家西揚在立園寫生為視點,緩緩地打開了立園裡的隱秘歷史。它與其說是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的情感衝突史,還不如說是中國傳統女性曲折的命運史,其中所隱含的傷與痛、悲與怨,纏繞在竹青與梅雲的內心,成為她們一生也難以掙脫的宿命,同時也構成了後人解讀不盡的人生謎團。《小鳥天堂》則敘述了一段悽美的網戀。它著眼於信任,視心靈的敞開為愛情的基石,從日趨功利和虛偽的現實倫理中,展示了兩性情感真誠交流的困境。在這篇小說中,小鳥天堂與純潔的愛情形成了一種互為隱喻的關係,天堂的樹林裡只剩下白鷺和灰鷺,就像現實的愛情中只留下欲望和功利。
無論是碉樓、立園,還是小鳥天堂,它們都是廣東江門的文化標誌,也是嶺南僑鄉的一些重要符號。鳳群先生以此作為敘事對象,無疑體現了他對這片土地的摯愛。他試圖從這些具有深厚文化意蘊的載體中,尋找千年嶺南的精神血脈,展示一個外來移民作家對本土文化的感悟和思考。
與此同時,在這本小說集中,作家還刻意收錄了一些有關故鄉徽州的敘事。鳳群先生出生於皖南,自幼便飽受徽州文化的薰陶。在很多小說中,他曾經執迷於探討有關徽州的文化精神。像《徽州紀事》、《柴窯瓷瓶》等,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在這些作品中,作家並不是刻意去表現某種地域性的文化鏡像,而是將之融入人物的內心深處,以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來詮釋這種文化特有的精神氣質。
文學是入學,它永遠離不開對人性的探索。鳳群先生對人性的探討充滿了熱情,尤其是對那些非理性的生命情狀,對那些像頭髮一樣紛亂的情感意緒,他更是顯得極為痴迷。像《都市民謠》、《雪崖》、《謎船》、《包裝時代》、《天使的飛行》等,都體現了創作主體的這種審美意願。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殘酷環境中,還是在欲望橫流的市場環境中,各種非理性的人性狀態,都在作家的筆下呈現出異常妖嬈的景觀,鮮活靈動,又耐人尋味。它是原始生命的自然流露,也是人生之所以曼妙而詭異的內在緣由。鳳群先生在表達這些生命的存在狀態時,從不亮出自己的主觀價值判斷,這也體現了一個作家對生命的尊重。
就我個人的審美趣味而言,我最喜歡的,還是鳳群筆下的女性形象。她們仿佛是一群善良而柔韌的精靈,洋溢著東方傳統文化中的某種神韻。她們天生麗質,卻又多愁善感;渴望專注之愛,卻又屢受傷害;直面尖銳的現實,卻又不乏浪漫的懷想。像《天使的飛行》中的安琪、《雪崖》中的芬、《都市民謠》中的阿香、《1986年的愛情》中的劉卉、《紅碉樓》里的慧儀、《立園》中的竹青等等,都是如此。可以說,她們不僅彰顯了小說內在的陰柔之美,也成功地展示了小說敘事的詩性氣質。
我常常想,一個優秀的小說家不應該在現實面前忍氣吞聲,而應該對一切人類可能性的生活飽含激情和幻想。他的敘事,不是對現實邏輯的簡單複製,而必須穿透所謂“客觀真實”的經驗壓制,展示生命應有的複雜和豐饒,典雅和詩意。從某種意義上說,鳳群先生的小說一直體現了這種審美追求。
2012年4月2日於廣州
(本文作者為著名文學評論家、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