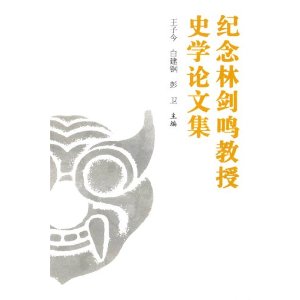內容提要
林劍鳴教授在史學界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其史學思想在學術界具有很高的地位。這本《紀念林劍鳴教授史學論文集》是林教授的學生和晚輩們為紀念他而自發把各自的學術論文貢獻出來集結成冊的一本史學論文集,其中不乏思想獨特、觀點鮮明之作,相信會對喜歡歷史的您有所幫助。後記
嚴格說來,我們是1981年底開始師從林劍鳴教授學習秦漢史的。那正是林劍鳴教授的《秦史稿》問世後不久。然而,作為1977年恢復高考後第一屆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的學生,實際上入學之後就對林劍鳴教授以《試論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為主題的講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回想,那已經是23年前的事情了。1978年,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學術,包括中國史學實現顯著進步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林劍鳴教授的《秦史稿》,就是在這一年完成初稿的。我們在這時走上學術道路,開始蹣跚前行,正是在西北大學的諸位老師包括林劍鳴教授指導下邁出初步的。
此後一二十年來,我們治學的點滴進步,都是在林劍鳴教授指導下奠定的學術基礎上取得的。有些工作,還得到林劍鳴教授的具體指教。林劍鳴教授從事學術研究的勤奮精神和開拓意識,仍將長期給予他的學生們以有益的影響。
為了紀念林劍鳴教授,由白建鋼倡議並提供出版資助,我們編輯了這部《紀念林劍鳴教授歷史學術論文集》。謹此感謝李學勤先生、熊鐵基先生、瞿林東先生、謝桂華先生在百忙之中撥冗惠賜大作,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精心編校。
白建鋼彭衛王子今
2001年6月22日
目錄
論郭店簡《老子》非《老子》本貌李學勤漢魏六朝佚史芻議周天游
關於范嘩史學思想的兩個問題瞿林東
戰國後期秦的職官與選官制度黃留珠
秦漢選官制度雜議劉文瑞
試論秦始皇的法外擅權譚前學
秦始皇與漢武帝的人才觀和用人政策異同論賀潤坤略論漢代“酷吏”的政治心理余華青
論西漢步、騎兵的兵種、編制和戰術白建鋼
秦漢時期雲南的大開發熊鐵基
論秦漢時期河北地區的歷史地位呂蘇生
甘、寧地區秦長城考察記史黨杜田靜
海南漢代珠崖郡治城址考李琳
秦簡《日書》之“建除法”試析張銘洽
從秦簡看戰國秦漢時代“順天”思想特徵吳小強
漢簡所見律令拾遺謝桂華
江蘇連雲港市出土的漢代法律版牘考述張廷皓
秦漢“夜行”考議王子今
漢代旅舍蠡說彭衛
蛭子考劉福德
林劍鳴教授學術傳略
林劍鳴教授主要論述目錄
後記
書摘
一、秦的軍功制問題秦國厲行軍功制,致成統一大業,已成定論,不再贅述。然而,以秦始皇統一為界,戰國時期的軍功制,到統一以後的秦代是否仍在具體實施,似乎未見明確論證。頗有學者不分秦國與秦代,認為統一後的秦代,依然實行軍功人仕,甚至有稱秦代仍以軍功為主要仕途者。據筆者之見,秦代是否沿用戰國時期的軍功制,頗有疑問。即使秦代仍有軍功人仕之途,較之戰國時期也有所變化。
戰國人仕之途,一為軍功,一為養士,七國皆然,以秦為甚。且秦國以軍功與養士合二而一,形成客卿以軍功升擢的定例,卓有成效,黃留珠先生在《秦漢仕進制度》一書中論之頗詳。該書列秦仕進之途為六,即保舉、軍功、客、吏道、通法、徵士。關於秦統一後的仕途,該書指出有些仕途已明顯不復存在,如以客出仕;而有些仕途又有較明顯發展,如徵士;始皇三十四年之後仕進大多出自“法”、“吏”二途①。獨未論保舉、軍功二途在秦統一後的變化,本文試對軍功一途在秦統一後的情形略加補充。
秦的統一,奠定了國家的和平環境,儘管有北御匈奴、南戍五嶺之舉,但相對於七國爭雄的戰爭環境而言,秦代從建立皇帝制度起直至二世爆發大規模的起義反抗為止,戰爭不是國家的主要任務。因此,可以說在統一後的年代裡,軍功人仕已經失去其存在的現實基礎。且秦國的軍功人仕,在惠文王十年以後,已與以客人仕密切結合。既然統一後以客人仕已明顯不復存在,那么,在基本和平的環境下,又失去了與其配套的客卿途徑,軍功制亦當不再盛行,起碼不再是秦代的主要仕途。
當然,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沒有廢除軍功入仕的明確記載,但同樣也沒有廢除以客人仕的明確記載。我們既然可以根據統一後失去了以客人仕的客觀條件而稱其不復存在,何不可對軍功人仕同理對待呢?現有史料中,有關軍功人仕的記載,均為統一前的材料,統一後無一例,足以說明問題。
還有,縱觀歷史,任何一個朝代,並不是伴隨著開國的炮聲就能建立起自己的選官制度的,西漢的察舉,隋唐的科舉,無不如此。西漢之察舉,經高、惠到文、景,方才創立,武帝時才逐漸昌盛。隋唐之科舉,真正成為重要仕途,是在高宗武后乃至玄宗時才實現的。或者有人可舉出曹魏九品中正制為反證,孰不知曹丕開國之前有曹操多年執政為鋪墊,且有東漢的察舉和清議、月旦評為基礎。即使同為科舉制,宋代沿襲唐制,也是在太宗、真宗時才逐漸完善的。明代儘管有朱元璋煞費苦心地為後代立祖制,然官制的實際定型,是在成祖永樂以後。清代制度,則多建立於康雍期間。立於康雍期間。甚至新中國創立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也在80年代。大體上,每個朝代的選官制度,真正實施往往距開國少則三四十年,多則七八十年:其原因據筆者推測,當有兩點:一是任何制度的施行,均需一定的社會基礎,須建國者努力積累一定時間;二是開國之初有大量功臣勛吏,不存在立即進行人事大換班問題。秦王朝國祚短促,統一前的大量功臣元勛和選用六國降官,足以滿足其統治的需要,而且直至秦亡也不存在官吏隊伍的換代問題。所以,秦王朝不可能,也無必要在選官制度方面有重大建樹。不管是秦始皇還是秦二世,在軍功人仕已經失去作用的情況下,並沒有能夠創造出全新的替代制度。論者往往忽視這一點,苦於秦統一後沒有選官制度重大變化的史料。故以戰國之秦制推論統一後之秦制,誤將軍功制推到了統一後的秦代。
軍功制在秦統一後失去其社會基礎,但又沒有明確廢除,那它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從史料可知,秦國在戰國時期。軍功就與勞考相結合。人仕靠軍功,而升遷則靠勞績,由於秦漢時期選考合一,故人們多把含有考課勞績內容的軍功制以“軍功”一詞總而括之。實際上,雲夢秦簡有關於考勞的不少記載,<秦律十八種>和《秦律雜抄》不乏其內容,甚至專門有<中勞律),《秦律雜抄》的《中勞律》條稱:“敢深益其勞歲數者,貲一甲.棄勞。”顯然,“中勞”是關於勞績的考課制度,而且和年資緊密相關。據《秦律十八種》,考課殿最者,可罰勞或賜勞,均以時間計算,按年考課,最者可賜“三旬”,殿者可罰“二月”。既然賜勞和罰勞都有時間,則可以肯定,官吏的升遷和俸酬有一定的年資要求。隨著統一,戰爭的減少和治理國家的需要,考定勞績肯定會越來越重要。因此,隨著秦的統一,在不急於補充大量官員的前提下,過去將入仕與考課合二而一併以人仕為主的軍功制,肯定會出現向以升遷為主而考察勞績的中勞制轉化,即由“功”向“勞”的轉化。而《中勞律》不僅有秦簡資料為證,還有居延漢簡資料為證①。從“漢承秦制”的角度說,“中勞”應當是秦代的主要人事制度之一,而且極有可能已將統一前的軍功製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