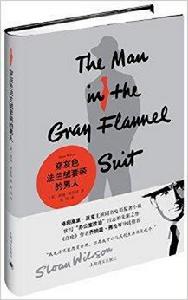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奧斯卡影帝格利高里·派克主演同名電影(1956)。描摹發達資本主義年代大公司內部壓抑競爭,呈現“辦公室政治百態”。揭示二戰遺留的創痛。超級暢銷經典《自由》作家喬納森·弗倫岑導讀推薦 。
作者簡介
斯隆·威爾遜(1920—2003),美國作家。1942年哈佛畢業,隨即被招入海軍服役。戰後擔任記者與大學老師。《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是其最著名的小說,已成為反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社會的經典之作。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精準描摹了‘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這一社會群體,剖析了他們的壓力、難題與習慣……威爾遜是旁觀者,卻並不冷眼相對……他寫下了一出精彩的社會喜劇。”——《紐約時報》
“極有洞見的故事……刻畫了在二戰中成年的一代人。”
——《邁阿密先驅報》
名人推薦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有影響的美國小說之一。”
——大衛·哈伯斯塔姆(美國著名記者兼作家,普利茲獎得主)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是一本關於五十年代的小說。前半部分可以作為消遣來讀,後半部分卻可以讓讀者一窺即將到來的六十年代。畢竟是五十年代給予了六十年代那種理想主義——還有憤怒。
——喬納森·弗倫岑
後記
後記
從我完成了對《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的創作至今,已經過去二十八年了,可以算作是整個一代人過去了。我還記得最後一次改稿時的興奮,那是在半夜的時候,因為我在布法羅大學 擔任對外宣傳員一職,白天都在忙學校的事。我當時正在努力趕工,因為熱情洋溢的出版商理察·L·西蒙先生給我規定了截稿日期,我剛要開始列印最後一章的備份,我唯一的那台打字機上的”e”鍵就飛了出來,彈到桌子上,像一隻將死的蟲子一般。把它按回鍵盤上倒不難,但一碰到那鍵子,它就又掉出來。無奈之下,我將就著先列印了一頁,將所有”e”的地方都空出來,然後手寫填上去,但它是字母表中最常用到的字母,寫完之後看起來根本不行。
我從書房的窗戶向外望去,看到鄰居艾倫·陶博家裡的燈還亮著,還能聽見深夜聚會的聲音。我知道艾倫家地下工作室里有很多工具,他修理東西很在行。我便匆忙來到他家門口,唐突地打斷了聚會。他放下酒杯,從工作檯上拿起烙鐵,他漂亮的妻子珍妮拿著手電筒照著打字機,就這樣艾倫將”e”鍵牢牢地焊在了打字機上。
艾倫和他漂亮的妻子,還有許多老朋友現在都已經去世了,讓人驚訝的是,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自己卻還在繼續,不老的還有這本書第一版的封皮上我的照片,或是由此書改編的電影中的格里高利·派克的形象,經久不衰。我的那位主人公湯姆·拉斯似乎找到了永葆青春的不老泉。
小說本身也有一段奇特的歷程。創作期間,像許多新秀一樣,我也曾幻想著自己的作品可以與《戰爭與和平》 相匹敵。最初的幾篇評論稱這部作品是粗俗的感傷,一下子打醒了我,後來諾曼·卡曾斯 在《周六評論》和奧威爾·普萊斯考特 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評論讓局勢有了轉機,他們沒有將我比作列夫·托爾斯泰,但都說我寫了一個很好的故事,講述了我們這一代人自二戰歸來後所面臨的問題。令我吃驚的是,這部小說,雖然我自認為絕大程度上是自傳題材,卻被一些嚴肅的思想家認為是對郊區生活的世俗和刻板的一種反叛。這本書後來躋身於最暢銷小說排行榜,並被翻譯成二十六種不同的語言。歐洲人似乎把這部小說當成了美國人生活的精確寫照;而俄羅斯卻查禁這部小說。
後來,突然之間,這本小說,或者至少是它的題目,在美國變成了一種國民笑話。我還記得那是在一個電視幽默劇中,阿特·卡爾尼 穿著髒兮兮的工裝褲從下水道里爬出來,對傑基·格里森 說,“你以為是什麼?還能是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 優秀小說《金臂人》的作者納爾遜·艾格林 曾說過:如果《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娶了《馬喬里·莫寧斯塔》 ,他不會去參加婚禮。《瘋狂雜誌》也拿灰色法蘭絨出氣。書的標題成了時髦用語,不論哪個喜劇演員都會脫口而出,如此時髦反而讓人大倒胃口,而且,人們問我,“就是你寫的《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嗎?”時,總會縱聲大笑。
裁縫們主動提出為我免費定做灰色法蘭絨西裝。當年上預科班就開始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主管們現在開始穿運動裝上班,以示他們的自由精神。藍領工人們則開始購買灰色法蘭絨西裝。我的主人公湯姆·拉斯在一家大廣播公司的董事長所建的心理健康慈善基金會工作,但不知怎么就被當成了廣告界人士。知識分子、嬉皮士和花童開始覺得他並非是世俗的反叛者,而是世俗的最高代表,是最守規矩的人。人們攻擊他是物質主義的代表,不善思考或是根本沒有思想,一個永遠也不會和傑克·凱魯亞克 同路的人,也不會整日與某人逍遙快活;這個觀察很準確,他和我認識的大多數人一樣,即使有時深受誘惑,他們也不會那么做的。
十多年後,那陣狂熱退卻下來,而這本書卻滲透出懷舊情懷。甚至在現如今,只要我做演講,談我十二本書的創作的時候,都還會有人在提問環節問到《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這本書,好像在詢問一位多年的老友一般。社會學家以及各界的思想家一直在他們的寫作中引用這一題目,來指代那些一眼便被認出來的人,比巴比特 更和善聰明的典型的美國人,但思維仍然受局限的那類傢伙。《巴特利特語錄》 將這一標題列為通用術語之內。
一些高中和大學將《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列在必讀書目當中。我收到一些年輕人的來信,他們比我自己的孩子都小,也在讀這本書。令人欣慰的是,與那些在書剛一出版時或讚頌、或嘲笑、或憎恨這本書的大多數讀者相比,他們似乎更能理解我寫這本書的創作意圖。對於湯姆·拉斯,這個經常被忘記名字的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來說,他的主要問題就是他感到自己為了取得事業上的成功,養活家人,正在被這個世界逼成一個工作狂,而這一窘境在1983年,對於正值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女來說還仍然存在。湯姆所面臨的另一大難題就是,他是否應該給在海外打仗時生下的私生子以經濟上的援助。一些從朝鮮和越南歸來的老兵對他的困境是再熟悉不過了。湯姆·拉斯感到現實充滿了諷刺,他因在戰場上殺死十七個人而被高度讚揚,卻因為有了私生子而面臨聲名掃地的危險,他的感受得到了更多現代讀者的同情,比1955年剛出版時要好一些。在商界所要求的溫文爾雅的外表下,湯姆·拉斯的內心充滿了憤怒。當我叫他“拉斯 ”時,我原以為有人會批判我取名這樣粗俗,用意太過明顯,但在書中由於湯姆舉止溫婉,並沒幾個讀者覺察到這一點。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都將他們的內心情感隱藏得很好,但青年一代的讀者卻看穿了這一偽裝。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結尾部分,我刻意地讓湯姆·拉斯對自己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與過去的28年相比也應該這樣,回想起來,我很高興至少我曾讓他有過短暫的歡欣。他之前一直生活艱難,理應得到這份幸福感,而1955年大多數人都會有這樣的幸福感。修好了打字機上的“e”鍵,也買了新機器,我再也不必半夜求朋友幫忙修理了,那之後我一直在琢磨,當湯姆·拉斯認為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了之後,又發生了些什麼呢。這些年來,一直有出版商請我再續寫一部,最後我決定試試,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時候,湯姆·拉斯將成長為一個不同的人物。最初那位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就是位年輕人的形象,不是其他年齡段的人物形象。1955年是我最擅長創作年輕人形象的時候。從本質上來說,《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基本上是一本關於年輕人的書,為年輕人而寫的書,因此對於出版社為年輕人再版這本書我萬分感激。
——斯隆·威爾遜
這篇後記是1983年版的前言部分。
序言
引言
一個經典的小說場景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康涅狄克州郊區,一個像沙皇時期的聖彼得堡或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一樣舒服的小世界。閉上眼睛,你就能看到秋天的落葉飄落在安靜的街道上,可以看到戴著軟呢帽的上班族從紐哈芬火車站台湧出,能聽到夜晚第一瓶馬提尼酒的叮噹聲;還有午夜過後難聽的爭吵聲;聞到令人絕望的性愛的味道。
這個小世界中的所有慰藉和挫折都可以在《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中找到。這部小說是斯隆·威爾遜的處女作,於1955年出版。該書出版後極為暢銷,很快被拍成電影,由格里高利·派克 主演,但是之後的幾十年該書沒有再版。如今人們大多只能記得它的名字,該書和《孤獨人群》 、《組織人》 共同成為50年代順應時代的口號。
你可能樂於譴責那種順應,你也可能悄悄地在其中寄託了一份懷舊之情;不管怎樣,《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這部小說都會給你帶來純粹的50年代的景象。主人公湯姆·拉斯和貝琪·拉斯是很討人喜歡的一對白人新教徒 夫婦,兩人保持著傳統的分工:貝琪在家照顧三個孩子,湯姆通勤到曼哈頓做一項極其乏味的工作。拉斯一家順應時代,但並不快樂。貝琪抱怨著乏味的社區;她夢想著逃離周圍奮鬥中的鄰居(鄰居們本身也是不滿足的);她算不上一個超級媽媽。一個女兒用一瓶墨水把牆給抹得一團糟時,貝琪先是打了她一巴掌,然後和她一起睡著了;晚上湯姆看到她們“緊緊地抱在一起,”兩人的臉上全是墨水。
和貝琪一樣,湯姆的失敗也越來越讓人同情。“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本是他恐懼和不屑的那種人;可是,他在二戰中當傘兵的那段生活與他現在養家餬口的郊區家庭生活感覺完全脫節,這使得他有意識地將自己隱藏在灰色法蘭絨西裝下。他想在聯合廣播公司爭取到一份更掙錢的公關工作,期間他了解到公司的董事長霍普金先生計畫要成立一個關注心理健康的全國委員會。湯姆對心理健康感興趣嗎?
“我當然感興趣!”湯姆熱誠地說道,“我一直都對心理健康感興趣!”這話聽起來有點傻,但是他想不到別的話來改正了。
順應潮流是湯姆給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開的一副藥。儘管本性真誠,他卻百般嘲弄一切。“我畢生的興趣就是為心理健康工作,”一天晚上他對貝琪開玩笑道。“我自己怎么都行。我可以奉獻到底。”貝琪批評他總是憤世嫉俗,還說如果他不喜歡霍普金就別為他工作,而湯姆回應道:“我喜歡他。我愛慕他。我的心都是他的。”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中的道德和情感核心就在於湯姆四年的軍旅生涯。無論是殺敵的時候,還是愛上了一個孤苦伶仃的義大利年輕女孩的時候,作為軍人的湯姆·拉斯都是強烈地感覺自己是活在當下的。他對戰爭的記憶與和平時代“緊張而狂亂的”生活形成了痛苦的對比,和平時代的生活就像貝琪哀嘆的那樣,“對什麼都感覺提不起興趣來。”可能戰爭讓湯姆的心靈不幸受到了傷害,也可能正相反,他想念戰爭中才有的那份刺激和英勇衝鋒的感覺。不論是哪一種,貝琪的指責都沒有冤枉他:“自從你回來後,”她說道,“你真是無欲無求。你工作努力,但是內心中你從沒有真正盡力過。”
湯姆·拉斯事實上陷入了消費時代的困境中。有三個孩子要撫養,他不敢冒險去走一條反常、嬉戲和混亂的道路,一條凱魯亞克 開闢、平欽 跟隨的垮掉一代的道路。但是消費主義單調乏味的工作,以及物質欲求的舒適的生活方式,也讓他同樣感到危險。湯姆可以預想到,如果他步入了享樂主義下的單調工作,他真的會變成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麻木地不斷追求更高的薪水,以便能負擔起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杜松子酒。於是,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他在兩個都不怎么吸引人的選擇面前掙扎著,他的心情和語氣從疲憊不堪急劇轉為憤怒,到色厲內荏,從憤世嫉俗到膽小懦弱,到有原則的堅決;而貝琪,令人心酸的是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為什麼不開心,和他一樣在掙扎、在轉變。
小說的前半部分寫得更好。拉斯一家討人喜歡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很多情緒都很尋常。該書最開始跑龍套的那些角色通常都滑稽而有趣,他們的存在仿佛是要反射出拉斯一家後來的變化一樣:總是在桌子後邊斜倚著的人事經理,討厭小孩的上門醫生,雇來的保姆,她把拉斯家不守規矩的孩子們收拾得服服帖帖。小說的前半部分是很有意思的。沉浸在威爾遜老式的社會小說的講述中,就像是乘坐老爺車游車河的感覺;你會訝異於它的舒適、速度和性能;通過小窗戶看到熟悉的場景還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書的後半部主要寫貝琪——湯姆的妻子。儘管他們倆先後經歷了三年的初戀、四年半的戰爭分離、九年“沒有激情”的做愛、“只剩焦慮”的負擔家庭的生活,貝琪仍然一直站在丈夫身邊。她制定了一個家庭自我改善計畫。她使湯姆參與了當地的政治。她賣掉了討厭的房子,帶領家庭走出陰暗的“流放生活”,搬到更加獨立的環境。她自願過高風險的全職企業家生活。最重要的是,貝琪一直勸誡湯姆要真誠。結果,故事的主線由“一對感人的問題夫婦對抗50年代的世俗” 逐漸轉為了“充滿內疚的男人被動地接受賢良妻子的幫助。”儘管世界上存在像貝琪·拉斯這么優秀的人,但從人物塑造上講他們並不成功。在小說的序言中,斯隆·威爾遜對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莉斯寫下了一句充滿感情的致謝詞,(“這部書的很多想法都是來自於她”),簡直讓人懷疑這部小說是不是威爾遜寫給伊莉斯的情書,一部他們婚姻的頌歌,說不定他是想要藉此書消除自己對婚姻的疑慮,讓自己重新相信愛。在小說充滿女性的後半卷里明顯出現了一些有爭議的地方。當然,儘管拉斯身上矛盾不斷,威爾遜卻從來沒讓他的角色接觸到任何真正的不幸。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中一個明確的含義就是社會的和諧取決於每個家庭的和諧。戰爭使男人和女人之間產生隔閡,讓美國陷入病態;戰爭將幾百萬的男人派到海外去殺戮,去見證死亡,去和當地的姑娘做愛,而美國幾百萬的妻子和未婚妻在家裡高高興興地等待,期待著童話般完美的結局,承擔著一無所知的精神負擔;現在只有坦誠相見才能夠修補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紐帶,拯救失調的社會。就像湯姆總結的那樣:“我也許不能改變世界,但是我可以讓我的生活恢復秩序。”
假如你相信愛、忠誠、真實、公平,你就會像我一樣,眼含著淚水讀完這本《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可是,即便你的心正在融化時,你還會懊惱於自己對書的屈服。就像弗蘭克·卡普拉導演的傻乎乎的電影一樣,威爾遜讓你相信,一個人只要表現出真正的勇氣和誠實的品格,他就會得到一份離家只有幾步之遙的完美工作,本地的房地產開發商不會欺騙他,本地的法官會公正執法,討厭的壞人會被攆走,工業巨頭會表現出正派有禮和公民精神,本地的選民會投票為小學生上繳更多的稅,海外的前女友也會很識相地不給他惹麻煩,於是危機四伏的婚姻得到了拯救。
不管你信不信,這本小說確實成功地捕捉到了五十年代的精髓——這種不自在的順應行為、對衝突的逃避、政治上清心寡欲、推崇核心家庭 、尊奉階級特權等。拉斯一家要“灰法蘭絨”得多, 而他們似乎一直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與“沉悶的”鄰居們不同的地方,歸根結底並不是他們的不幸或是他們的怪癖,而是他們的美德。在書的開篇里,拉斯一家不經意間會說一些譏諷和抵抗的話,但是在最後的部分,他們家很開心地變成了有錢人。在第41章里,笑意盈盈的湯姆·拉斯可以說是志得意滿,正是第1章里那個困惑的湯姆·拉斯害怕而又蔑視的形象。與此同時,貝琪·拉斯完全不相信郊區的不安情緒可能有一系列系統的原因。(“最近人們過分地依賴於解釋了,”她想,“卻缺少勇氣和行動。”)湯姆之所以這么迷茫、不開心,並非因為戰爭導致了社會道德上的混亂,也不是因為他老闆經營的生意里滿是“肥皂劇、廣告以及喧囂的場內觀眾”。湯姆的問題純粹是個人問題,正如貝琪的行動主義僅限於本地和家庭內部一樣。這四年的戰爭(或者說在聯合廣播公司里的四星期,或是在韋斯特波特 一個陰暗的街道上當媽媽的四天時光)喚起了那些深層的存在主義問題,而這些問題被棄之不理:可能這就是五十年代本身不可避免的損失。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是一本關於五十年代的小說。前半部分可以作為消遣來讀,後半部分卻可以讓讀者一窺即將到來的六十年代。畢竟是五十年代給予了六十年代那種理想主義——還有憤怒。
喬納森·弗倫岑
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