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科利奧蘭納斯》是莎老晚年的一出可與四大悲劇相媲美的古羅馬歷史悲劇。故事情節如下:馬歇斯(後因攻下科利奧里城立功而被稱為科利奧蘭納斯),最初是羅馬共和國的英雄;而由於他性格上的弱點:脾氣暴躁,不肯低頭,而得罪了民眾,成了羅馬的敵人被放逐;他轉而投靠敵人:伏爾斯人,帶兵圍攻羅馬;後接受其母勸告,放棄攻打,而這行為又背叛了伏爾斯人,最後在戰亂中被伏爾斯人殺死。此劇的主題是英雄和民眾的關係。《科利奧蘭納斯》是反映人性弱點的悲劇,莎士比亞用生動的語言和豐富的修辭塑造了一個個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並描繪了一個個激動人心的場面。
故事情節
公元前5世紀羅馬共和國時期,將軍卡厄斯·馬歇斯戰功卓著,攻占伏爾斯人的科利奧利城之後榮膺“科利奧蘭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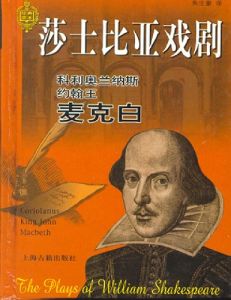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斯”之封號。科氏出身貴族,股肱元老,左右大猷,因被推舉競選執政官。科氏向來蔑視群氓,與世枘鑿,經護民官暗唆,平民群起反對,競選失敗,更遭驅逐,遂流亡至伏爾斯人的安息城投敵,鏇揮軍進逼羅馬復仇。正羅馬危卵之際,科母攜其妻孥前來求告息兵,羅馬因此得以保全,科氏則在敵營被殺。上述史實載於由托麥斯·諾思爵士(SirThom as North )於1579年譯出的古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之《希臘羅馬名人並置列傳》 。諾思這部獻給伊莉莎白(一世)女王的譯作,以古人古風為楷模,警喻現世,乃是多部莎劇故事之所本。也正是這部寫了46位名人的傳記,給了諸如蒙田、拿破崙以及打敗拿破崙的“鐵公爵”威靈頓等後人,以巨大的影響。莎士比亞多從古籍中引來故事原型,然後按時代精神,予以改造,寄託腹心。對比諾思的原型,《科利奧蘭納斯》劇中科母伏倫妮婭那種古希臘斯巴達式的信念(斯巴達系古希臘城邦名,其民風以簡樸、刻苦、苛嚴、黷武等特點傳諸後世)、科妻維吉利婭的緘默性格等皆為莎氏所添加;元老米尼涅斯和主要敵手奧菲狄烏斯的角色功能亦經改造;羅馬為因應反高利貸的起義而在元前494年建立護民官制度的史實只是一筆帶過;率少數士卒攻打科利奧利的史實則被改寫為科氏單槍匹馬陷城……儘管如此,有評家仍認為此劇乃莎氏竄改原型故事最少的一部。
劇中人物
| 卡厄斯·馬歇斯 | 後稱卡厄斯·馬歇斯·科利奧蘭納斯 |
| 泰特斯·拉歇斯 考 密 涅 斯 | 征伐伏爾斯人的將領 |
| 米尼涅斯·阿格立巴 | 科利奧蘭納斯之友 |
| 西西涅斯·維魯特斯 裘涅斯·勃魯托斯 | 護民官 |
| 小馬歇斯 | 科利奧蘭納斯之子 |
| 羅馬傳令官 | |
| 塔勒斯·奧菲狄烏斯 | 伏爾斯人的大將 |
| 奧菲狄烏斯的副將 | |
| 奧菲狄烏斯的黨羽們 | |
| 尼凱諾 | 羅馬人 |
| 安息市民 | |
| 阿德里安 | 伏爾斯人 |
| 二伏爾斯守卒 | |
| 伏倫妮婭 | 科利奧蘭納斯之母 |
| 維吉利婭 | 科利奧蘭納斯之妻 |
| 凡勒利婭 | 維吉利婭之友 |
| 維吉利婭的侍女 | |
| 羅馬及伏爾斯元老、貴族、警吏、侍衛、兵士、市民、使者、奧菲狄烏斯的僕人及其他侍從等 | |
地點羅馬及其附近;科利奧里及其附近;安息
創作背景
經專家們比照考證,《科利奧蘭納斯》當寫成在1608或1609年間,是莎士比亞的最後一部悲劇和最後一部羅馬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劇。此劇首見於文字是在“第一對摺本”(1623年)中,此前全無“四開本”的記錄。排字的顯然至少有兩人,格式乃至拼法都不統一,甚至連主人公的名字是Caius Martius還是Martius Caius都成舛雜;一個驚嘆詞數處拼作“O”,在別處又拼作“Oh”。爭議最大的是第1幕第9場第46行的一個詞:是overture (序曲)還是coverture(遮身物),還是ovator(領受歡呼的人)? 梁實秋先生顯然取coverture,因而譯作“戰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莎劇漢語全譯本乾脆跳過不譯;方平主編的《新莎士比亞全集》則譯作“清客”,實不知何據。由此也可見此劇文本的重大缺憾。此劇寫成時,英國先後發生過1597年的糧荒、牛津郡民起事和1607至1608年英格蘭中部各郡的騷亂。1607年6月28日英國王室曾發表公告稱:“國內最低微的民眾中近來多有人嘯聚作亂。”“暴民”問題當時正占去劇作家相當一部分注意力,是很有可能的此外,莎氏本人的母親死於1608或1609年,這或許也是導致劇作家戮力以藝術形式表達母子關係的因素之一。至於說劇中主人公科利奧蘭納斯即為時人埃塞克斯伯爵(也是“孤膽英雄”加“叛將”)的翻版,古羅馬處死叛徒的大帕岩暗指倫敦塔,科氏應受元老抑或平民節制則反映詹姆士一世與議會的對立等等附會,那是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機械地劃上太多等號,顯得牽強。
歷史評價
歷代評家對《科利奧蘭納斯》褒貶不一,粗線條地說,早期似乎是貶甚於褒。如果把這個劇本放在莎氏的所謂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成熟悲劇”的參照框架中考察,確有多處背離了已經確立的莎氏模式。首先是《科利奧蘭納斯》“缺乏超越時空的偉大悲劇所必有的活力和形而上教益”。詹森博士和柯勒律治也有類似的貶評,認為“成熟悲劇”多詩的暗喻,而《科利奧蘭納斯》劇中多用l ike或as的明喻,闕詩少文;哈姆雷特等“成熟悲劇”人物,甚至包括麥克白,多形而上的內省,僅漢姆雷特一角就有共291行的14則獨白,而在科氏悲劇中主人公僅有兩則涵義膚淺的獨白,多的是進軍、陷城、民眾喧譁起事等形而下的場面。蕭伯納更為刻薄,把科氏看作“掀蓋探頭”般的滑稽玩偶(Jack-in-the-box ),一觸即跳。另外,“成熟悲劇”和歷史劇的常例是每個英雄倒下後必有繼任者:亨利四世接替理查;安東尼接替愷撒,復被渥大維取代;福丁布拉斯接替哈姆雷特;卡西奧接替奧瑟羅;奧伯尼公爵接替李爾王……而科利奧蘭納斯始終只是“孤龍”(alonely dragon),最後只留下兒子小馬歇斯——所有莎劇中最年幼的角色——說出僅有的一句台
詞:“我不許他踩過(既應答祖母、母親‘要進軍羅馬唯有踩過我們的身體’之激,似也有不容仇敵踩踏的預言意味——蓋因下文其父被殺後奧菲狄烏斯踩其屍之上)/我要逃走,等我長大,我要打仗。”當然,也有藝術家為劇本的“放逐”主題和孤高英雄的命運所打動,18至19世紀經改編的演出記錄頗多;貝多芬還根據劇本“要么羅馬,要么我!”(Rom eorI!)的主題作曲,由華格納配上聲樂,流傳至今。《科利奧蘭納斯》這個劇本真正吸引評家和觀眾注意似乎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一位領悟到此劇對20世紀具有特殊意義的可能是T.S.艾略特,為此寫下了題為《科利奧蘭》 (C oriolan )的兩首敘事詩:“勝利進軍”和“政治家的難處”。在後一首的結尾處主人公喊出:
喔,母親
讓我呼喊什麼?
(眾市民)我們要求成立委員會,代議制調查委員會。
辭職!辭職!辭職!
劇本的現代意義於此呼之欲出!
政治涵義
心理學的崛起一度使科利奧蘭納斯成為繼哈姆雷特之後的又一個“戀母情結”主人公,其母借托子身,張揚“超我”(superego);更有醫學界中人以“陽具自戀”(phallic-narcissist)的躁進、支配慾、駕馭癖、拒不受制於人等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症狀來闡釋科氏的行為軌跡。同時,劇本的政治涵義被廣泛解讀,如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上演時曾激起敵對政治派別的紛爭,導致1934年2月6日的巴黎暴亂。總理達拉第只好下令撤換瑞士籍導演,代之以內政部保全局局長。德國更有早在莎劇寫成前演出科利奧蘭納斯故事的傳統,反對偽民主,呼喚強人,甚至還把故事編入課本(二戰後為占領當局所禁);布萊希特曾在20世紀50年代嘗試改編莎劇,後出於種種原因而中輟,但其素材鏇被他人廣泛利用。另一方面,在當時的蘇聯陣營,評論家們從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出發,確認莎士比亞的“人民性”——這正是筆者求學時代外國文學史課堂上反覆強調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等巨匠的偉大之處,即恩格斯所謂的“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在此劇中得到充分的表述,聲稱“莎士比亞的同情完全在平民這一邊”;莎士比亞已具有“英國民眾的階級意識”。布拉格某劇院在1960年演出此劇時則把那個戲說“肚子寓言”的元老代表米尼涅斯儘量作反面人物的誇張渲染,而把兩個暗中挑唆民眾起事的護民官演成“睿智並有階級覺悟”。現當代西方評家還多將《科利奧蘭納斯》當作政治辯論或預言劇來看待。美國喬治敦大學的B. R. Smith斷言:“如果說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哪一部是專為華盛頓官場所作,那就是《科利奧蘭納斯》了”;“對於2000年的華府官場同樣具有適時價值的是,劇本聚焦於一個公眾人物和他隱私生活的界面,這一切的背後總是一個女人(顯然是影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筆者按)”;並在引用劇中科氏的若干相關台詞後戲稱“沒有一位現任的國會議員能說得比這更透徹了”。
創作理念
誠然,莎士比亞在劇中描寫的是古代羅馬,但英國都鐸王朝的政治理念不可能不影響到他的思想並從其鵝毛筆尖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流瀉出來。這也是當代新歷史主義批評派的觀點。這些理念較為集中地體現在伊莉莎白(一世)女王的侍衛官Ludovic Lloyd的兩部書中:1590年的《時代的承諾》(The Consent of Time)和1602年的《耶路撒冷的策略》 (The Strategeys of Ierusalem)。到了詹姆士一世的斯圖亞特時代,雖則英王本人更醉心於王權權威,都鐸理念已深入人心,議會仍然強大,法制漸趨完善,英國社會在各種勢力相互制衡中求得和諧。質而言之,都鐸政治強調由所謂上帝意志確立的秩序體系,強調和諧穩定。此種理念,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可能正是英國社會除去一次弒君(指1649年詹姆士一世之子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的清教徒暴力革命,余則多為不流血的所謂“光榮革命”,社會相對有個超穩定結構的原因之一。此種理念亦即劇中元老米尼涅斯向民眾灌輸的“肚子寓言”:從前,身體所有器官/起來反抗肚子,還譴責說/肚子向來像個無底洞/占著身體的中央卻閒著不幹事/……/而其他器官/有的看,有的聽,有的出主意,有的獲教益,有的管行走,有的管感覺/相互協同,共去滿足/全身的需求和欲望/……嚴肅的肚子從容不迫/不像譴責者們那樣魯莽,於是答道/所有食物確是先入肚/你們大家全靠它維生,理所當然/肚子乃是全身的倉庫和工場/通過血管輸送食物/到達心的宮殿和腦的寶座/穿越人體曲折的管道/堅強的神經和次要的脈管/都從肚子得到滋養和活力/……/羅馬的元老們就是肚子/你們是作亂的器官。
包容在上述53行台詞中與“肚子寓言”一脈相承的意象還有:“頂著王冠的頭顱,注意視察的眼睛/運思策劃的心臟,作為士兵的胳膊/化作駿馬的大腿,作為號角手的舌頭”等等。雖說普魯塔克的原型中就有這個寓言,但是莎士比亞按照都鐸政治理念引申並發揮,把元老院稱作“肚臍”,把起事領頭的人物叫做“大腳趾”,把民眾稱為“忘恩負義的多頭妖魔”或“多頭蛇怪”(Hydra ),把護民官稱作“管住[人民]利齒的嘴巴”,把騷亂稱作“招引上身的麻疹”,把羅馬社會稱作“已無生望的病體”,強調政治機體官能失調而蠱壞的危險。有意思的是,古羅馬的科利奧蘭納斯還援用古希臘的先例來說明暴民民主的危害。不錯,莎士比亞筆下的市民部分說出了羅馬民眾的悲慘處境,有些人,如“市民甲”,對於科利奧蘭納斯或元老院的鬥爭,相對說來,比較講究有理、有利、有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節的策略。另就莎士比亞對民眾的總體態度而論,從《亨利六世》 (中篇)的凱德起義,經《裘力斯·愷撒》和據信由莎士比亞部分參與編寫的《托馬斯·莫爾爵士》 ,直到《科利奧蘭納斯》,應當說確有一個漸趨理性同情的發展過程,對於民眾“可以復舟”的力量也開始有所認識。但因此認定莎士比亞的“人民性”,說劇作家的同情“完全在平民這一邊”,顯然失之武斷,因為全劇壓倒一切的主旨首先在於:“大腳趾”挑戰“肚臍”畢竟只能擾亂秩序,破壞和諧,釀成禍端,最後導致肌體瓦裂。競選執政官的描寫也意味深長。科利奧蘭納斯稱自己像個“娼妓”、“閹人”,非得“披上長袍(候選人在拉丁語中作candidatus,意為clothed in white,故必須著袍),裸露身體,顯示傷痕”以取悅於選民,活脫脫一幅現代政客街頭競選的畫面!而蠱惑煽動(dem agogy)決不等於深得民心(popularity)。此外,劇中“若挨餓,毋寧死”的口號很容易使人聯想起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不自由,毋寧死”;至於劇中羅馬護民官之所作所為,只要民眾起而鼓譟(劇中眾口鼓譟聲voices多達30次,據1969年Cornmarket Press facsimile印載,此劇歷代演出中參與鼓譟人數最多時可達二百),便可裁決並即刻實施對科利奧蘭納斯的放逐,則也像後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時代的雅各賓專政。(試將法國政情與上述英國“超穩定”社會形態作一對比。)這類高調的古羅馬暴民民主與英國都鐸時代乃至後來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實有霄壤之別。如若讀者願意聽筆者稍稍偏離劇本說幾句題外話,倒是可以注意一下莎士比亞身後約400年,在東方的中國,有個名叫顧準的人是如何評價古羅馬民主的:“偉大的法國大革命不幸具有一個致命傷:‘國民公會集立法和行政於一身,它是古羅馬式的、由代表組成的直接民主機構。’這樣,羅伯斯比爾就是取勝,‘自己會變成拿破崙’。”莎士比亞筆下的“多頭蛇怪”作亂不正是古羅馬暴民民主原型的藝術闡發嗎?因此可以說,《科利奧蘭納斯》作為社會悲劇和政治悲劇,其真諦無非在於政治機體(body-politic)的官能失調。
鐵石行動
其次,試從分析劇中科利奧蘭納斯個人及其周圍的人物著手,來進一步挖掘悲劇的真諦。科利奧蘭納斯出身貴族名門,16歲從軍,曾手戮兩萬敵兵,留下27處傷痕,5次(一說12次——莎士比亞寫作時顧此失彼、前後不一的又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一例)戰敗主要敵手奧菲狄烏斯,多次頭戴橡葉冠奏凱歸來。這樣一個“肌肉和心腸硬如鐵石”武士的形象是需要鐵石來烘托的。於是,演出一開始就出現了兵器,直到劇終士兵為科氏“拖矛送葬”,全劇鐵石意象一以貫之;太陽的雹暴、擺動鉛鰭游水、堅硬的石塊作跪墊、神廟的水泥也燒成灰燼、走路似戰車隆隆,目光穿透甲冑,出聲猶如洪鐘,哼一聲就像大炮轟鳴等等。與此相應的是全劇暴力的渲染:第3幕第1場羅馬街道上的推搡追打,“抓住他”和“推下大帕岩”的叫囂、第5幕第6場敵營眾人接連五次的喊殺以及最後奧菲狄烏斯的踩屍。出現在以上背景中的科氏自然全無奧瑟羅式的浪漫夕照,或是與埃及豔后訣別的安東尼的騎士光環,甚至也沒有麥克白式的情感預警。這樣一部鐵石行動劇自然排斥溫情。母親伏倫妮婭更多的是羅馬的化身,早年驅遣兒子上戰場,嗜軍功如命,訓喻空房怨婦似的子媳,後來勸說科氏違心競選執政官,最後求告退兵赦免羅馬,意之所向,金石無阻。就連違反倫常的“母跪子”也是貞剛和功利的姿態多於溫情的賁發。綜觀全劇,惟有母親下跪之後,兒子亦跪並“執其手,默然”時,舞台表演如果凝化為造型,始有一點激盪感情的效果,被評家稱之為“全部莎劇中最具戲劇性的無言”,但就是這一點點動情之處,也是在普魯塔克原型紀事中就已載明的,莎士比亞不過是襲用而已。鐵石與柔情的失調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有反映。筆者未作科學統計,但是,誠如先師林同濟先生當年課上指出的那樣,《科利奧蘭納斯》中所使用的多音節拉丁理性大詞之多,在莎劇中顯然並不多見,除Coriolanus之名,其他諸如microcosm、conspetuities、empiricutic、cicatrices、carbonado、directitude、osprey等,讀起來無一不是amouthful(佶屈聱牙),每個詞都透出一種“力”,合成起來簡直就像米開朗琪羅的畫作!
歷史悲劇
嚴格說來,鐵石與柔情的失衡使《科利奧蘭納斯》劇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英雄。執行私刑似的暴民和擅長煽動的護民官不用說了;代表貴族的執政官大多軟弱,米尼涅斯算是個例外。在普魯塔克原型紀事中此人只不過是元
老院的代言人而已,但在莎士比亞筆下,他老謀深算,捭闔縱橫,像風中柔從的“蘆葦”對死硬的科氏這棵“橡樹”起著制衡作用,更被賦予科氏“父執”一輩的身份。然而,不論是他的“肚子寓言”還是後來為阻止科氏進軍羅馬一番舌敝唇焦的遊說,對民眾和科氏衝突雙方,終究罔效。科氏在全劇幕起伊始即已被定位成“人民公敵”的角色,雖說是“武士之花”,劇作家對他的剴切譏評可說是從頭到尾貫穿全劇。多數評家認定他的“瞎馬踢呀”(希臘語ham artia的嬉戲音譯,指悲劇人物性格的致命弱點,此系已故葛傳先生“發明”。另一希臘近義詞為h ubris,葛公戲譯作“修補利矢”)是驕傲——“驕傲……乃是他不由自主的天生癖性”。須知矜功得志,猖狂自彰確乃一位常勝將軍“不可自已”的弱點,科氏自然難免。但劇中同時也有數處——雖可能輕描淡寫了些——寫到這位將軍並非一味驕橫。如干戈甫停,科氏便想到曾收納自己借宿的敵方一窮漢已被己方俘虜,便求情釋放此人,足見他仁義忠恕未泯;又如奏凱後,科氏拒取駿馬等戰利品(史實卻是獨占戰利品),只願與士兵們同樂,得榮封之後,鼓號大作,民眾歡呼,科氏卻出乎意表地簡單回應:“我得去洗一洗了”。無怪乎考密涅斯將軍要慨嘆:“你太謙虛。”由此看來,所謂驕傲還不足以致命。其實,科利奧蘭納斯的“瞎馬踢呀”是多重的,恰恰由他的頭號對手奧菲狄烏斯說得最為中肯:我想他對於羅馬/就如鸕鶿對魚一樣,捕捉/全憑天性。原先他是他們忠義的僕人,可他不能/平和地維持榮譽。是否由於驕矜/因為事事順遂而有損好運;要不判斷失誤/致他機遇失盡/那可本該全是幸運,也許是本性/守真不二,只會/騎馬打仗不善坐而議政,和平之時/仍講究嚴厲過人/用上了治軍的一套,總不外乎上述某個原因——/……/……美德/在於審時盱衡。
思想基調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少年從軍,為戰而戰,任性易幟,由人詬罵“公敵”、“叛徒”,或恥笑作“愛哭的男孩”,不諳政治,不會審時度勢,不懂圓通,一步踏上不歸路,儼然像個“收割者死神”(a harvestman taskd tomow),最後卻落得個替罪羊的下場,既為羅馬元老和市民,又為對手奧菲狄烏斯和伏爾斯人,更為雙方的一再鏖戰獻了身,成為戰神的祭品。這種黷武主義的基調且瀰漫於全劇。讀者不妨聽一聽奧菲狄烏斯的下人是如何談論戰爭與和平的:仆乙:……這種和平只能讓鐵器生鏽,增加裁縫的人數,生養出唱民謠的閒人。仆甲:依我說,我寧要戰爭。戰爭領先和平,就像白晝領先黑夜:戰爭似獵犬歡奔,揚聲狂吠,緊追獵物而去。和平是麻木,無為,平淡,無聲無息,昏睡不醒,感覺遲鈍;和平生養的私生子比戰爭殺死的人更多。(本文各段劇本引文均由筆者譯出。)尤為發人深思的是,這種殺戮狂熱已由下一代傳承。科氏之子小馬歇斯捉了又放,放了又捉,撲殺蝴蝶,直至撕碎,是種跡近虐待狂的行為,似乎更為其父的殺戮狂熱作了一個註解:除了上述鐵石心腸導致柔情失重外,黷武激情使理性失調,也是科氏悲劇的一大因素。
悲劇人物
科利奧蘭納斯一直被稱為“孤龍”。據專家統計,在所有莎劇中使用“孤獨”(alone)一詞頻率最高的就是《科利奧蘭納斯》。全劇中,民眾,不管是羅馬人還是伏爾斯人,一概都是供政客驅遣的群氓;士兵(其實就是穿上軍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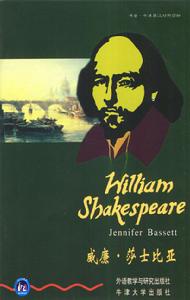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的平民)中不乏怯懦、貪婪之輩;政客,不管是元老一邊還是護民官一方,多工於心計的讒佞奸人,就連米尼涅斯的說辭也常顯圓滑,令人想起《哈姆雷特》里饒舌的波洛涅斯;伏倫妮婭一手培育並塑造了科利奧蘭納斯,但最後又親手毀滅了兒子,求和成功返回羅馬受到眾人歡呼之際,正是兒子遭伏爾斯人手刃之時,反諷之甚,莫過於此。科妻維吉利婭是個啞寂的存在,兒子僅一句台詞,至多只是丈夫或父親的陪襯而已。(注意科氏台詞:“我可不能像女人般柔弱/不能看這孩子和婦人的臉。我坐得太久了。”)泰特斯·拉歇斯和考密涅斯兩位將領是科利奧蘭納斯的袍澤,但懂得策略,譴責愚勇,特別是後者,提醒科氏“民亦可復舟”,羅馬派出的第一位說客便是他。奧菲狄烏斯一角較有意思。他雖屢敗於科利奧蘭納斯手下,當科氏前去投奔時卻忘其前愆,取其後效,欣然接納,更顯出誇張的熱情(擁抱時奧氏稱自己心臟劇跳,比娶新娘、進新房還要激動。這曾引得一些評家解讀出性愛的涵義);對科利奧蘭納斯說來,奧菲狄烏斯不僅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甚至可說是“另一個自我”(alter ego):“我要是變成任何別的人,但願就是他”。可是,奧菲狄烏斯並非科氏式的“絕對武士”一個,而是深諳通權達變之道。最初的“熱情”消散以後,部分由於難以忍受對方的習慣性張揚,奧菲狄烏斯開始對科氏心存芥蒂,謀劃利用後予以剷除之策。上文提到,奧菲狄烏斯對科氏弱點的分析最為精當,從這個意義上說,稱之為“另一個自我”倒也並不完全離譜,正因為知之越深,攻擊的殺傷力也才越大;正因為了解科利奧蘭納斯“一觸即跳”的弱點,這位工於政客心計的伏爾斯將軍先是用上“叛徒”的罪名,然後去了封號,直呼其名,最後在對方求告戰神之際,侮稱他是個“愛哭的男孩”,由此激他暴怒,使事態終至不可收拾。這環環相扣的計謀頗使人聯想到前文羅馬護民官勃魯托斯所說的:“直接激他暴怒;他慣於/征服別人,執拗成性。一受拂逆,便不能/溫和自製;這時便會信口說出/自己的真實思想,而這時/我們正好利用弱點扭斷他脖子。”這段話里的暴怒在英文裡用的是“choler”一詞,原意“黃色膽汁”,為中世紀生理學認定的人的四種體液之一(其餘三種為“血液”、“粘液”和“黑色膽汁”,分別導致欲望過盛、麻木遲鈍和鬱鬱寡歡的性格)。因黃色膽汁分泌過度(據筆者統計,choler一詞在全劇中至少出現4次)而導致體液官能失調者必是個“一觸即跳”的暴躁型人。
 《科利奧蘭納斯》
《科利奧蘭納斯》科利奧蘭納斯於是成了名副其實的“孤龍”,無法融入羅馬或伏爾斯人的社區,甚至無法融入自己的家庭。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不能融入社會生活者非神即獸。”科利奧蘭納斯的“非人”特點既是他的巨人特徵,恰恰又正是他的致命傷。羅馬放逐之初,他還有“天外有天”(There is a world elsewhere)的幻想,然而與任何一個社區或任何人都格格不入,或者說社區與個人關係的始終失調,注定了這是一個實際上永遠處於自我放逐狀態,最後終歸滅亡的悲劇人物。因此,作為個人悲劇的真諦,鐵石排斥柔情,黷武扼殺理性,孤高游離社群,“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荀子語),偏傷者,性格偏執失衡或官能失調之謂也。“這是我獨自做成的”(Alone I did it),“但是讓它來吧”(“它”當指下文厄運,此句自然使人聯想到漢姆雷特劇終台詞:Letbe),在各派力量制衡官能失調的亂世,一個性格“偏傷”之人倒下了,一出失調的悲劇上演了。但科利奧蘭納斯畢竟是接近“神格”的巨人或超人,所以莎士比亞還是讓他同哈姆雷特一樣,享受了軍人的葬禮,而這一待遇是奧瑟羅等其他悲劇主人公所未能享受的。
作品解讀
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有成就的詩人和劇作家之一。他生活的時代正值伊莉莎白女王一世及詹姆士一世的統治時期。莎士比亞出身於英國中部斯特拉福城一個富裕市民的家庭,少年時代曾在當地的文法學校讀過書,學過修辭、邏輯及拉丁文等科目。22歲時離開自己的故鄉,去到繁榮的首都倫敦謀生,尋找機會,廣泛接觸各階層的生活,加深了對社會的認識。1590年左右,他進了劇團,開始了舞台與創作生活。如在第110首十四行詩中他寫道:
“我曾經走遍各地,
作彩衣小丑在世人面前顯眼,
傷害自己的思想,廉價出售最貴重的東西。”
莎士比亞在劇團時,既要參加演出,又要進行創作,有時還要參加巡迴演出,如在第27首十四行詩中他說:
“勞動使我疲倦了,我急忙上床,
來好好安歇我旅途勞累的四肢;
但是腦子裡的旅行又鏇即開場,
勞力剛剛完畢,勞心卻又開始。”
莎士比亞的絕大部分戲劇都是通過對現成材料的改編與加工而完成的。在20多年中,他一共寫了39部戲劇,兩首長詩,154首十四行詩,以及另外一些雜詩。1613年才離開倫敦,回到久別的故鄉。1616年4月23日逝世。
莎士比亞於1608年寫成了《科利奧蘭納斯》,死後7年在1623年才正式出版。這部劇本以羅馬共和國時代的卡厄斯·馬歇斯的生涯為基礎。馬歇斯是古羅馬5世紀上半期的傳奇英雄。羅馬史家普魯塔克在他的《名人傳》中記述了他的事跡。莎士比亞就是根據普魯塔克的資料創作出此劇的。在有些人名的處理上出現了一點差錯。在莎士比亞劇本中,馬歇斯的母親是伏倫妮婭(Volumnia),妻子是維吉利婭(Virgilia),實際上他母親是維圖利婭(Veturia),而妻子才是伏倫妮婭。普魯塔克的《名人傳》是由托馬斯·諾斯(Sir Thomas North,1535—1601)譯成英語的,史料本身沒有錯,莎士比亞為什麼更換名字,難以確定。
這齣悲劇的情節如下:
馬歇斯,後來因攻下科利奧里城立功而稱為科利奧蘭納斯,是羅馬共和國的民族英雄,但是:“他所做的轟轟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個目的;雖然心腸仁厚的人願意承認那是為了祖國,其實他只是為了取悅他的母親,同時使他自己可以對人驕傲;驕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頂點。”(I.I.37—42) 科利奧蘭納斯居功自傲,對於有意見的市民總是破口大罵,如:
“發生什麼事,你們這些違法亂紀的惡棍,
你們盡提些惡毒骯髒的意見,
使你們自己變成社會的疥癬?”(I.I.163—165)
當時羅馬的敵人是伏爾斯人,伏爾斯的領袖是奧菲狄烏斯,他們正舉兵侵犯羅馬。奧菲狄烏斯相當怕科利奧蘭納斯,而科利奧蘭納斯也十分尊敬奧菲狄烏斯。他說他非常羨慕奧菲狄烏斯的高貴品格,他們曾交過手,能夠和這頭獅子般的人交手,是可以值得自傲的事。羅馬共和國派科利奧蘭納斯去迎戰,他英勇無比,打敗了對手,攻下了科利奧里城。
可是科利奧蘭納斯這個人頭腦簡單,脾氣暴躁,不肯低聲下氣,得罪了民眾和民眾的代言人護民官,結果從一個人民英雄變成了一個被放逐的敵人,他無路可走,便投奔伏爾斯人,為奧菲狄烏斯效勞。奧菲狄烏斯很樂意他投靠自己,便舉兵進攻羅馬。羅馬人害怕,派人來說和,科都不理,直到他母親前來求情,他才允和,這下又得罪了奧菲狄烏斯,便斥科利奧蘭納斯背叛,在亂軍中將他殺死。
科利奧蘭納斯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另一個悲劇人物,他和另外幾個悲劇人物不同,但給人們留下的意義是同樣深刻的。他的驕傲和導致他失敗的剛愎自用的性格是他母親一手培養起來的。如她對媳婦說:
“倘若我的兒子是我的丈夫,我寧願他出外去爭取光榮,不願他貪戀閨房中的兒女私情。……想到名譽對於這樣一個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讓他默默無聞地株守家園,豈不等於一幅懸掛在牆上的圖畫?”(I.Ⅲ.2—13)
她所希望的兒子是有不朽軍功的兒子,她寧願兒子為國家戰死沙場,而不希望他閒在家裡虛度年華。母親和兒子都有一顆高貴的心,希望為國家立下不朽功績,寧可以軀體獻給祖國。但這造成科利奧蘭納斯的驕傲自滿,剛愎自用,心中沒有別人,只知道自己。當國家把他驅逐出去時,他拒絕認錯,投奔敵人,成為羅馬的叛徒,最後又被敵人殺死,兩邊不討好。如果把這部劇本和《哈姆萊特》、《李爾王》、《奧瑟羅》及《麥克白》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這也是一部偉大的悲劇,也同樣反映出了人性的另一個弱點。因為人性的弱點都有可能造成悲劇。另一方面,此劇寫出民眾易受煽動利用,忽左忽右,而護民官政治家則假作謙虛,心懷私利,兩面三刀。科利奧蘭納斯實際上是吃了不懂政治的虧。
這部劇本也像其他劇本一樣,許多說白是用了五步抑揚格素體詩,而且是用莎士比亞式的特有的修辭來描述事物,使得氣氛明顯的加強。
所謂五步抑揚格素體詩有以下幾個特點:
1.每一行詩有十個音節。
2.每十個音節中分五個音步。
3.每一個音步有兩個音節,重音落在第二個音節上。
4.素體詩是無尾韻的。如十四行詩就不是素體詩,雖然也是五步抑揚格,卻是有嚴格的尾韻。
不妨舉例來看一下莎士比亞五步抑揚格素體詩在修辭上的特點:
All the contagion of the south light on you,
You shames of Rome!You herd of—Boils and plagues
Plaster you o’er; that you may be abhorr’d
Further than seen,and one infect another
Against the wind a mile!You souls of geese,
That bear the shapes of men,how have you run
From slaves that apes would beat!…(I.Ⅳ.31—37)
這一段的中文大意是:願南風吹來的一切瘟疫都降臨到你們身上,你們這些羅馬的恥辱!願你們渾身長滿毒瘡惡病,人們還沒有看到你們時就會厭惡你們,因為在逆風的一英里之外就開始傳染!你們這些穿著人形外殼的笨鵝靈魂,你們亂奔亂竄的奴才,連猴子也能把你們打退。
再看這段中的修辭,the south這裡不是“南方”,而是用方位代表具體事物“南風”,即吹來病菌的風。Boils是“膿腫”,plagues是“瘟疫”。而這裡boils and plagues指所有的毒瘡瘟病一類的東西。其他諸如be abhorr’d further than seen,one infect another against the wind a mile都是修辭完美的句子。
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不能望文生義,否則便理解得不確當,因為莎士比亞在運用詞時,有他時代的特點,也有他個人語義學上的特點,這是不能忽視的。如本劇中隨便可以看到下面一些詞或詞組在特殊情況下的含義:
on ’t:of it an ’t:if it
famously:for fame for that:because
to be:of being being:since you are
of:by still:always
like:likelycarry:win
voice:vote cause:dis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