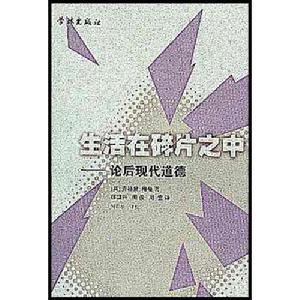基本信息
·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頁碼:348 頁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ISBN:7806682171
·條形碼:9787806682173
·版本: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
·正文語種:中文
·叢書名:歐洲思想系列
·外文書名:Life in Fragments
序言
本書是《後現代倫理》(Postmodern Ethics)一書的姊妹篇,是其主題的拓展。在《後現代倫理》中,我提出,後現代新圖景的變化,已經或正在喚醒我們對道德、道德生活的純正理解。我認為,現代企望及雄心的破碎,和社會化調整及個體行為一致化幻覺的消褪,使我們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洞悉道德的本相。首先,它使我們看清道德的“原始”狀況:遠在被教會社會地建構和提升的恰當行為的規則之前,也遠在被勸誡遵從一定行為模式和摒棄其他模式之前,我們就已經處於道德選擇的狀態之中。這就是說,我們注定是或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存在,即我們不得不面對他者的挑戰,面對著為他者承擔責任的挑戰,處於“相依”(be—ing—for)的狀態之中。“承擔責任”與其說是社會調整和個人教育的結果,不如說它構建了萌生社會調整和個人教育的原初場景,社會調整和個人教育以此為參照,試圖重新框定和管理它。
這一主張顯然不屬於經典作品。總體而言,它並非徒勞地討論人類的“善本質”和“惡本質”。“成為有道德的”並不意味著“成為善的”,它不過是人在善惡選擇時作為創作者與表演者的自由運用。我們說“人本質上是道德存在”,並不表明人在根本上是善的;我們說社會地構建和教導的規則是原始道德狀況下的第二因素,也並不是說,不健康的社會壓力或社會安排的缺陷,造成了最初善的扭曲和無能,導致了惡的產生。我們說人類生存狀況首先是道德存在物而非其他,指的是:遠在被權威地告知何為“善”、何為“惡”(有時兩者都不是)之前,我們在最初不可避免地與他者相遇時已經面對著善與惡的選擇。這也就是說,不論選擇與否,依照順序,我們面對的境況首先是一種道德的問題,面對的生活選擇首先是道德的兩難選擇。隨之而來的是對道德責任(即作為善惡選擇的責任)的承擔,而道德責任也遠先於任何基於契約、利益計算或支持某項事業而賦予或要求承擔的具體責任。與此相伴的是,這些具體責任不可能窮盡和完全替代原始道德責任,縱使後者被極力轉換成一套良好訓練的規則體系;也許,道德責任的真實面目只能是隱藏的,無法顯現。
最先面對道德選擇,作為我們“存在於世上”的原始事實,並不許諾一種樂天知命的無憂生活。相反,它製造困境,使我們痛感焦慮與不快。面對善惡選擇,意味著要在一種矛盾糾結的狀態中發現自身。如果善惡標準每一條都規定得明確無誤,只需直接從中選擇,那么選擇的模糊性所帶來的憂慮或許會相對較小。特別是在只需為他者負責而行動與克制自己不這樣做之間作出選擇,而且又非常清楚“按責任行動”所包含的內容時,更是如此。然而,道德責任的選擇並非如此。對他者的責任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模糊性。它沒有任何明確的界限,也不容易轉化為可操作的或克制著不去做的步驟。相反,它的每一步都包含著難以預見和更難事先評估的後果。這種與“相依’狀況相連的模糊狀態,是永恆的、無法改變的。只有取消了在道德境況下的一切“道德”的事物,它才會消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面對善恐選擇的永恆困惑(也即“擔當起自己的責任”)正是道德存在的意義(唯一意義)。
但是,這等於是說用“孤獨”這把鹽擦揉“困惑”這個傷口,兩難困境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選擇的必要性也並沒有為恰當的選擇帶來簡單的方法;努力行善的嘗試,既不能表明動機善,也不能擔保結果善。責任的王國處處充滿爭吵。低於和高於理想要求的行為同樣容易發生。道德生活永遠充滿了不確定性。道德大廈是用“懷疑”和“自我貶低”建造而成的。既然善惡界限事先沒有劃定,那么只能在行動中劃定。這種努力的結果,與其說是一張已標明道路的網路,不如說是一串足跡。因此,對於責任之所的居民來說,孤獨,正像困惑一樣,是永恆的、無法逃避的。
……
目錄
序 言 尋找後現代理性
第一章 無倫理的道德
社會:隱藏運作
面對不可面對的
編織紗幕
被刺
穿的紗幕
撕破的紗幕
顯性道德
倫理規則,道德標準
第二章 和睦的形式
相伴、相處、相依
習俗和承諾
相依的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性
善存在於未來
第三章 破碎的生活,破碎的策略
打破界限,進入監獄
加速和它的不滿:“生活質量”
加速和它的不滿:“身份”
朝聖般的現代生活
世界對朝聖者並不友好
朝聖者的接班人
道德際遇?政治際遇?
第四章 後現代憂慮的總目
第五章 對陌生人的再考察
第六章 暴力、後現代
第七章 種族道德
一、成為難辦事的身體
二、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及道德進步
三、一個世紀之久的集中營?
四、“排猶主義”再評價
第八章 道德與政治
一、後現代世界的知識分子
二、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由多個部落組成的歐洲
三、後記:威脅與機遇,舊與新
譯後記
人名譯名對照表
……
文摘
書摘
現在,我們終於“客觀如實地面對無序”了。我們從前從未這樣做過。僅僅面對無序就夠令人困窘和沮喪了。這種行為的新穎處——沒有先例可以被遵循,也沒有先例給出保證和指導——使情況變得令人不知所措。我們跳過去的水並不很深,但未經探測。我們甚至不是處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之所以是十字路口,是因為那裡已有道路。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在造路——這是唯一能夠存在的道路——我們只有通過行走才能做到這一點。
或者,換用哲學家和教育家的語言表述相同的道理(傳教士的語言,不管它的體系中留下的是什麼,我們仍未用它):沒有發現也不可能發現存在的基礎,並且,建立這種基礎的努力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成功。道德是沒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義,也是不能被描述和進行邏輯推理的。因此,道德像生命的其餘部分一樣,是不可預測的:它沒有倫理的基礎。我們再也不能為道德的自我提供倫理的指導,再也不能“創製”道德,我們也不再希望一種更加熱情或系統地投入這項工作即能獲得這樣的能力。既然我們自己和每個人都樂意接受這樣的觀點:道德只有在由一些比道德的自我本身更強的力量所構成的堅實基礎上,才是安全的——這種力量超越了道德本身的短暫/狹窄的時間/空間——我們發現,要理解為什麼自我是道德的,和我們如何去認識到它是道德的,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相信倫理基礎沒有建立或尚未建構成功是一碼事,而根本不承認倫理基礎的存在完全是另一碼事。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直率的話:“如果沒有上帝,一切都百無禁忌”,喊出了現代無上帝秩序構建者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沒有上帝”意味著:沒有比人類意志和抵抗力更加強大的力量來迫使人類成為有道德的,沒有比人類自己的渴望和預感更加崇高和值得信任的權威來使人類相信:他們覺得是體面、公正和正確的——道德的——行為的確是道德的,並且,他們能夠將人類帶離錯誤以防他們陷入非正義。如果沒有這樣的力量和權威,人類就被遺棄在自身的智慧和意願之中。當哲學家和傳教士不停地求索時,這種缺乏僅僅催生出犯罪和惡行;當神學家確信地向我們作出解釋時,這種缺乏不能成為產生正義行為或判斷的正義的依據。“無倫理根基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自我奠基”的道德缺少倫理基礎時,顯然應受譴責。
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確信:在一個承認道德無根源、缺乏效用,而且僅靠習俗這塊易碎的跳板來溝通深淵的社會中既存的或是可能存在的任何道德,都只可能是無倫理根基的道德。由此,一切都是或將是不可控制和不可預測的。以不同方式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摧毀和重建自己的時候,道德自己建造了自己:人們聚集在一起或者離開,加入一個聯盟或者解散它,取得一致意見或者彼此爭吵,修補或者撕毀使他們聯合起來的紐帶、忠誠和團結。我們知道的僅限於此,餘下的,即這一切的結果,卻是模糊的。
能夠作為對象處理的事物是:經仔細檢查過、解剖過、衡量過、分類過、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的事物。樹立一種對這類處理的阻礙,一種“目的化的障礙”,是一個與發展一種帶有感情的態度相一致的觀念。我們稱不受衡量和評估結果所限制的行為和思想是“有感情的”。感情不是推理,更無所謂邏輯推理。它們是不持久的而且幾乎沒有內聚力,無法避免內部矛盾。它們逃避或者摧毀任何由標準和規則建造的框架。既然,像列奧塔提醒我們的,我們已經用行為的預見性和規則性來表明人類的成熟—感情就不能不被輕蔑地看作幼稚的表現(即成熟化工程以現代賦予它的形式出現,希望我們遺忘的事物)。受感情支配,我們似乎回復到一種沒有防禦和被拋棄的幼稚狀態:沒有可以信守的規則;我們在又一個未經探索的世界中活動;我們重新勘察它,似乎是從頭開始,像我們從起點前進一樣。
這是“承擔責任”的含義。(這是作為向標準逐漸轉變的成熟化這一觀念所掩飾的事實;在此觀念中,“負責任!”的召喚就意味著“遵守規則!”)指著規則,將我與他者的聯繫重新描述為一組同樣的聯繫中的一個項目,某種類屬的一個樣本,某種普遍規則的一個案例—我逃避了除了程式上的責任之外的一切責任。另一方面,通過感情的方式與他者相聯合時,我是對他/她負責的,而且,首先是對可能與他/她有關的作為或不作為負責。我不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一組中可更換的項目,關係網中一個可再裝滿的狹縫;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價值的—而且,如果我停止不做,也是有影響的。現在,他者變成了我的擔保品;我轉而變成了我的責任的擔保品。
因此,將他者納入我的感情之網,建立一種彼此依賴的結合,這種重要的相互關係也是我一人的創造和我的唯一責任。我負責使這種相互依賴保持生機。這是我與他者的感情“接觸”所建立的唯一事實。剩下的是沉默;我不知道履行我的責任意味著什麼,責任既是空蕩的,等著被履行,也是無限的,不可能被完全履行。因此我還負責將現存的責任再鑄成一個可行的責任,負責填充它所缺乏的內容,負責盡一切可能實現它。這種責任使我變得強大而有力;它也臆斷了我的權力;它使他者以弱者的形象出現在我面前;它同樣也臆斷了他/她的弱點。一個人是向比自己強大的人負責;一個人為比自己弱小的人負責。
因此,相依和負責任實際上是權利關係。沒有什麼能改變這種情況,即使通過責任所產生的全部互動過程,以及在為目的而向他者屈服的行為中,被推向幕後或斷然地否定,它依然存
在。(甚至選擇屈服也是我的選擇權的一次實踐。)責任和權利之間的這種聯繫實際上是同義重複的,沒有權利,就無所謂責任。沒有權利,就無法想像履行實際的責任。(反之亦然,履行責任就是權利的一種體現。)
由於常常處於選擇性的親密關係中,因此,區分原因和結果只能是徒勞;對不充足的優慮是消費主義狂熱的原因嗎?或者,原因在於這一擴大的消費者市場的聰明策略或未預料到的後果—這一市場用對不充足的憂慮取代對偏離的優慮,變為大眾對不確定性的憂慮?討論也許很容易朝著任何一種可選的答案深入,但這已經失去了意義,因為—與韋伯闡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景非常相似—這種愚蠢的掩飾早已變成了一個鐵籠子,從中看不到任何逃走的方法。不充足憂慮和消費者狂熱相互促進,從對方汲取精力並且確保“他方”的存活和完好。
不管這將導致什麼,被取消了全景監獄同伴這樣一種商品供應者角色(一種不再能提供充足供應的角色)的現代個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商品消費者的地位,扮演著樂趣採集者,或者,更確切地,各種感受的採集者的角色。這兩種角色指向兩種不同的(集體的同私人的)處理不確定性憂慮的方式,這種憂慮是在被稱作現代性的重要的“擺脫責任”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兩種角色指向兩種不同的(集體的同私人的)負有運用這些方法的任務的機構。出現於防禦變化過程中唯一完好的、未受損的,是不確定性優慮本身—儘管現在喬裝為對不充足而非對偏離的憂慮。
對偏離的憂慮是一種經嚴密地凝聚的優慮形式。在形式多樣性背後卻比較容易發現一種共同的內容;霍克海默和阿多諾(Adorno)就能準確無誤地描述出“對空虛的優慮”,這是一種害怕與眾不同和由此導致的孤獨的體驗,是現代焦慮的核心。對後現代的不充足優慮的描述就做不到那么簡單明確了。部分地因為它在其中運作的這個世界本身—與“標準”的現代世界不
同—是破碎的,還因為後現代與線性的、連續的現代完全相反,它是“扁平的”和插曲式的。在這樣一個世界和這樣一個時代里,類別指的是“家族的相似之處”,而非“核心力量”,甚至不是“共同特徵”。在後現代焦慮這個豐富的池塘里幾乎找不到一個在每種類別中都會出現的特徵。“不充足”在這裡作為一個標籤將大量的憂慮進行歸檔—不同導向的、不同經歷的、不同處理的。這么多憂慮中沒有一種能被輕易地描述為焦慮這一鏈條上的“主要環節”,更談不上一切的“首要原因”。與其尋找一個後現代的“憂慮之源”,不如為後現代的焦慮設定一個總目。這,僅僅是這,正是本章餘下部分將做的。
限定、分離、放逐(驅逐出境或破壞),這一傳統的序列構成了一切因擔心健康而弓!起的政治戰略。圍繞著反對“頑固的健康危害”的鬥爭興起了極易激動、緊張不安而好戰的政治運動,這些人為他們基礎的脆弱而更緊張,更焦慮;他們只有自己集體性的由恐懼引起的熱忱可以依靠,只有以對別人的驚人的傷害使他們在現實上的印記看來似乎真實。因此使他們會吸引在整個社會中最易變化的、主要是處於邊緣的、獨立的激進主義分子,他們為“社會的”死亡所威脅,以及因極其渴望獲得別處拒絕給予的身份而不知所措的人。然而不論社會地位如何低微,他們都作為一個更大的部隊的先鋒派而行動;正是通過卸下所分擔的死亡恐懼的負擔,通過刺穿一個洞,使社會各部分中積聚的緊張情緒得以釋放,他們完成了對死亡載體中所蘊涵的種種恐懼進行貶低、破壞和羞辱的重大工作。
然後當代生物技術科學賦予個人以揉捏般形成他人身體的手段。我們很少會懷疑這種構想,即在母親腹中,孩子是母親身體的延伸,而且與他們的器官、附屬檔案一起的身體是私人財富(正如她可以自由地節食以消除“脂肪”或抽掉脂肪)。父母親同樣有權決定他們想要(或不要)把什麼樣的孩子帶到這個世上來—現在基因工程的技術使他們有一種全新的、未曾有過的機會去按他們的偏好行動。
至少在理論上,這種新形勢製造了兩種互為補充的可能性。其一是按少數人的要求“定製”他們的後代。他們很快能從冗長而變化的基因名單上選出他們自己所選擇的調製品,而醫生則保證完全按照囑咐—如果必要,在試管中—製造嬰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