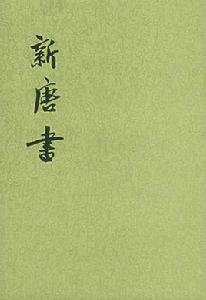譯文
唐朝時,汴州刺史王志愔在飲食上非常講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然而,給賓客卻吃剛剛脫去的糙米。一次,一位商人有一條驢出售。這條驢一天能行三百里路,曾經有人給他三萬文錢,他都沒有賣。這次,市場上的經濟人報價說十四千。王志愔聽了後說:"四千文錢少,我再加一千。"還有一次,王志愔手下人去給他買單絲羅,每匹三千文錢。王志愔問織一匹單絲羅得幾兩絲?代買的人回答說:"五兩。"於是,王志旻讓家童取來五兩絲交給代買人,又按每兩手工費用十文錢,取出五十文錢同時交給買人。
人物生平
王志愔(?—722) 唐博州聊城(今聊城市東昌府區)人。年少即以進士擢第,唐中宗神龍(705-707年)年間,累除左台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眾官都畏懼他,當時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皂雕”(黑老雕),意思是說他看待官吏就好像猛雕看待燕雀一樣。不久遷大理正,他曾上奏說:“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眾所謗。”時下大理寺官吏多不嚴格執法,認為放縱罪犯就是寬恕仁政,嚴格遵守法律條文就是苛刻,這實在是非常有害的現象。其實,嚴格執法本義即嚴格按法律條文行事,並非在條文之外濫施刑罰。唐中宗對其上奏很是讚賞,王志愔職遷駕部郎中。在正確理解與處理法與情的關係上,王志愔特彆強調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的作用。他認為理想的狀態是君上“居中履正”,垂拱而治;臣下恪守規制,任忠直為己任,為君主補遺缺。但“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即皇上臣下意見總是保持一致未必是好事,“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表現在執法上,這種可貴的“不同之和”應是為君者在法律之內行君道,為臣者嚴格執法,“不以忤懷見忌”,即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其《應正論》,文約數千言,廣徵博引,針砭時弊,以“和而不同”之理,深喻“齊眾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後於是成功”之道,表達了他嚴明法紀,以法治國的思想。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寺少卿。景雲二年(711年),朝廷下詔依漢制設定刺史,在全國大州衝要之地負監督檢查之責,大州置都督20人,挑選素有威重者授任。於是拜王志愔為齊州(治今濟南)都督,但因為其他的原因未能到任,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不久,徙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刺史,仍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712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100戶。不久加封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出為魏州(治今河北大名東)刺史,改揚州(今江蘇江都)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跡,境內肅然。後來召拜刑部尚書。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皇帝幸東都洛陽,令王志愔充京師留守。開元十年(722年),長安權梁山與其黨謀反,偽稱襄王男,自號光帝,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要擒殺王志愔,王志愔跳牆出避。不久屯營兵潰散,反殺權梁山等5人而歸營,並將權梁山等人首級傳示東都洛陽。而王志愔卻因慚悸病卒。史臣論其“位歷亞台,名德兼著”,贊其“稱職”、“聿修厥德”。《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收王志愔任汴州刺史軼事一則。
史料記載
舊唐書《王志愔傳》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台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皁雕”,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尋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眾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
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嘆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
有客聞而惑之,因謂仆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
仆斂襟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於袞職,用忠讜為己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理,刑期於無刑,人協於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嘆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己獨處正,應正而無咎。觀魚於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
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譎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方。維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
昔任延為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辯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
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眾以寬。”《傳》曰:“寬則得眾。”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
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深密。《內律》:“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寢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綱,立人極也。
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眾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後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實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逾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舍,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贓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駻,舍銜策於奔踶;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夫,何功之有?
又謂仆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為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子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舍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禮經不變之義。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圖,高視岩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眾工鹹理。聚以正也,仆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托,予何懼乎?
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謇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為深恥。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間仆也。
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
景雲元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為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戶。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出為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跡,境內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尚書。
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偽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逾牆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新唐書《王志愔傳》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台侍御史,以剛鷙為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為“皁雕”。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己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托,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舍銜策於奔⻊是,則王良不能御駻;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
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為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
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逾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慚悸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