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平
 烏斯曼·塞姆班
烏斯曼·塞姆班他十五歲離開學校,1942年加入自由法國軍隊,並於1944年隨部隊解放法國。二戰後,塞貝納在馬賽當碼頭工人,積累了烏斯曼·塞姆班
生於塞內加爾的OusmaneSembene是漁民的兒子,二戰時曾被法國徵召入伍參戰(塞內加爾當時為法國殖民地),戰後在法國的車廠工作,積極參與工人運動。在執起導筒之前,Sembene已是知名的作家,六十年代重返祖國後,希望透過電影接觸更多非洲人民,故遠赴莫斯科一年修讀電影,其後拍出改編自家小說的處女作“BlackGirl”(黑女孩)[1966],成為首部獲得國際影壇稱許的非洲電影。
“BlackGirl”講述一位當保姆的塞內加爾黑人少女,跟隨法籍夫婦僱主前往法國工作,卻在那裡過著儼如被禁錮的生活,被女主人呼呼喝喝,最終她選擇自殺結束生命。電影刻劃出白人對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黑人的偏見和歧視性的優越感,亦指出黑人對白人社會盲目的仰慕和崇拜。“Xala”(薩拉)[1975]普遍被視為導演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故事設在一個剛剛轉由黑人掌權的不知名非洲國家,當中一位部長挪用公款迎娶第三位年青的妻子,卻在床上赫然發現自己力不從心,更傳出他受到性無能的詛咒(Xala在Wolof語中為“詛咒”之意)。電影不但諷刺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的掌權者貪污腐敗,只求利己的政治歪風,亦批評非洲人在新時代中依然保留一夫多妻,男尊女卑,盲目迷信等不合時宜的舊觀念。
導演最後一部長片“Moolaadé”(割禮龍鳳斗)[2004],探討非洲國家中依然盛行的女性割禮習俗,指出人們應團結地以勇氣和開明的思想破除害人的迷信。電影結尾是一個非常有趣又有意思的蒙太奇:教堂上的駝鳥蛋忽然變成無線電天線,象徵著時代的變遷,亦強調讓知識廣傳的重要性。導演以這個無聲無息的劃時代大躍進作為其漫長電影生涯的句號,乍看似是簡單輕盈,但其實他多年來一直以電影勸諫、批評、勉勵不斷轉變的非洲社會中的人民。
主要作品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塞貝納在1963年回到塞內加爾,之後他製作了大量的長片和短片,從諷刺喜劇到嚴肅戲劇到紀錄片,都有所涉及。1966年他執導了《黑女孩》(La Noire de…/black girl),這是一部關於一個法國家庭虐待非洲姑娘的電影。他帶著他的電影到塞內加爾各地,以獲得更廣泛的觀眾。他後來的電影被認為有攻擊政府的傾向,所以經常遭到臨時查禁。90年代後,他的影片題材豐富。《Guelwaar》是一出發生在小村莊裡關於穆斯林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諷刺劇,.
LaNoirede…(1966)
Emitai(1971)
Xala(1975)
Ceddo(1977)
Moolaadé(2004)
作品資料
《割禮龍鳳斗》(2004)(Moolaade)
導演:烏斯曼·塞姆班
上映:2004年
地區:法國
語言:法語
顏色:彩色
類型:劇情片
劇情簡介
割禮龍鳳斗(2004)
Collé是一個溫和開明男人的三個妻妾中,最為聰穎、幽默且風趣並最得丈夫喜愛的二太太;她育有一女,已經到達適婚年齡,也訂了親,卻遲遲沒有受非洲社會傳統、象徵純潔的女性割禮,這點讓村子眾多長老、男人以及其它婦女所鄙夷,連她自己的女兒也不斷要求行割禮,否則不僅在社會中被排擠,也不能捧水款待客人。面對女兒底擋不住社會壓力,苦苦哀求行割禮,Collé就是不為所動。Collé不僅不願女兒冒著生命危險,接受割禮;連帶也當起四個跑來家裡躲藏的小女孩的守護神,在庭院前拉起象徵巫術的繩索Moolaadé,不準年長婦人進入家裡,搜尋那四個在割禮前脫逃的小女孩。割禮究竟是什麼?為什麼Collé誓死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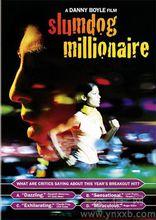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女性割禮,是割除女性部分或者全部的陰核以及小陰唇,傳統上用的是鐵片或者小刀割除,再用一般針線或者荊棘縫合,由於過程中沒有麻醉劑,刀片消毒不徹底,因此許多女孩還來不及長大便死於失血過多或者傷口感染。而即使她們的母親年輕時,在割禮中倖存,仍得終身忍受下體的疼痛,無論是行房還是小解,無論是生產還是勞動。
片中,Collé面對女兒的要求,她娓娓道出何以反對女兒也走上跟她同一條路。原因不只是割禮中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足以使人致命。還包括,這個女兒出生前,Collé也懷上孩子,但還來不及出生,即告夭折。當時Collé疼痛不堪,幾乎要死去,她實在不願意女兒遭受跟她一樣的苦痛。事實上,不僅如此,當Collé的丈夫外出旅行歸來,晚上與Collé溫存之後,男人翻個身便沉沉睡去,而她卻因行房後的疼痛,整夜不能眠;天蒙蒙亮,她即起身盥洗留在身上以及床單上的血跡。房事沒有高潮,沒有愉悅,沒有快感,只有難以忍受的痛!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如果說Collé代表的是非洲本地女性因為親身經驗的覺醒的話,她的女兒的未婚夫Mercenaire,這個自法國賺了錢開了眼界的優秀青年,便代表了「我們這些觀眾」詢問這種野蠻儀式的替身。他帶著榮耀、知識以及各種科技回到村中,受到廣大村民的歡迎,同時也目睹了一場葬禮,那是因為割禮而死去的小女孩的葬禮,雖然親屬覺得悲傷,但卻沒人對死因提出質疑與挑戰,Mercenaire震驚、疑懼,這場景也在他心裡發酵著。與此同時,Mercenaire的父親要他解除先前的婚約,改娶一個已經接受割禮,代表潔淨的11歲小女孩,他沒有接受。反而不顧村民的眼光,執意拜訪有智慧型、談話有內容且懂得生活的Collé,並欣然接受他的未婚妻,沒有受過割禮、被視為不潔的Collé的女兒的奉茶。烏斯曼·塞姆班的電影作品
非洲女性是不是只能被壓迫,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事實上,壓迫從來不是一種暴力與屈從二分的形式。在生活實踐中,我們仍能看到許多活潑且反壓迫的抵抗策略。這些非洲女性,日常最重要的娛樂,除了一同坐在樹蔭下乘涼談天之外,就是享受著收音機傳來的「外在的世界」的訊息與音樂。然而,隨著Mercenaire幾次與父親的嚴重爭執以及反抗父母指定的婚姻大事,外加Collé庇護連同親生女兒在內的五名小女孩,抗拒有生命危險的割禮,村中長老遂認為村子風氣太壞,Collé丈夫有失管教妻子責任,要他當眾以皮鞭毆打、「管教」Collé;另一方面,收音機是另一個敗德的來源,所以全村的收音機都得集中焚毀。男人集體上清真寺祈禱,女人呢,就利用公共洗衣井進行串連與反抗。儘管所有的收音機還是難逃被焚的命運,但總有漏網之魚,村子的女性也因為僅剩的收音機,而連結地更深了;至於割禮痛楚、喪女的共同經驗,則順帶地在這場串連中被喚醒:奪下刀片、驅逐割禮施行人、集體且大聲地說出「拒絕割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