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汪宗翰,號栗庵,湖北省通山縣汪家畈人,據《汪氏宗譜》記載:“宗翰,光緒己卯(1879)科舉人,揀選知縣大挑二等;庚寅(1900)科會試,中第九十二名進士,欽點主事簽分吏部。供職三年,改選甘肅鎮縣知縣,加同知銜。辛丑(1902)鄉試同考官,調補敦煌縣知縣。甲辰(1904)大計卓異,賞戴花翎。戊申(1908)調署華亭縣事,接補張掖縣知縣,誥封奉政大夫,晉封中憲大夫。”
1902年,汪宗翰任敦煌縣令時,對保護莫高窟藏經洞的文物和文獻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他學識淵博,對古代文獻有較深的認識,上任敦煌縣令後,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頗具興趣,曾在當地蒐集一些漢簡和文物來欣賞研究。當敦煌道士王圓籙送來敦煌經卷時,他十分讚賞,鏇即報於上級。
1900年,同為湖北(麻城)人敦煌道士王圓籙發現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王道士選了一些書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給當時的敦煌縣令嚴澤,希望能得到賞賜和嘉獎,可嚴澤不好此道,也就沒有引起他的重視。王道士認為藏經洞裡的經卷非常寶貴,就不辭勞苦跑到甘肅道台廷棟那裡報告,廷棟認為卷子上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的好,也沒給予重視。一年後,湖南人鄔緒棣接任縣令,對王道士的報告也不在意,1902年3月,汪宗翰調任敦煌縣令,王道士向汪宗翰報告了此事,得到了汪宗翰的高度重視,他鏇即向甘肅省教育長官學政葉昌熾寫了書面報告,但得到的回答是“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守。”汪宗翰奉命趕到莫高窟藏經洞,與王道士一起細心檢點封存文物和文獻,責成王道士看管,等候上級處理。他在送給葉昌熾的敦煌絹畫上題寫了“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等報告文書。遺憾的是,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調離敦煌縣,未能繼續保護敦煌文物,但之前對敦煌文物的保護做了大量的工作,離任後,還多次建議新任縣令要竭力保護好藏經洞。他在職期間,大力幫助改善百姓生活,深為百姓擁戴,在他前後5任縣令中,他建樹最高,名聲最好。
汪宗翰是一介清官,宣統辛亥年(1911),67歲在九江彭澤退休,在僚友資助下才順利回到故鄉。回到故鄉汪家畈後,他還是老驥伏櫪,不忘家鄉興衰,大力推廣教育,教化村民,深得當地官府稱讚。他於民國九年(1920)病逝,終年76歲,葬於通山縣闖王鎮汪家畈後山,墓碑上記載了汪宗翰生卒年月和仕途履歷。在考察中發現,汪宗翰的故居和墳墓與平民無異,可見他確實是一代清官。
主要成就
 汪宗翰
汪宗翰汪宗翰,是第一位真正發現、並懂得敦煌藏經洞中經卷、畫像重大文物價值的清朝官員,是第一位對敦煌藏經洞中經卷、畫像文物價值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也是最先對敦煌藏經洞中經卷、畫像作出了了保護、封存貢獻的人,更是首先真實向清朝政府匯報敦煌藏經洞文物古蹟、並申請清廷政府妥善保管的官員。就是汪宗翰調往京城後,也一直沒有忘記敦煌藏經洞中珍貴的經卷、畫像,努力說服朝廷撥資金將文物運往京城妥善保管,通過汪宗翰等人的不懈奔波與努力下,終天不負有心人,於1910年,僅剩的一萬卷經文、畫像得以運京。汪宗翰為敦煌藏經洞中經卷、畫像的封存、上報、最終說服朝廷運京,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試想一下,若是汪宗翰沒調往京城任官,不努力奔波說服主要的官員,那些經文、畫像又還能保留下多少在國內?)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在《發現藏經洞》一書中,有寫到時任敦煌縣令的汪宗翰。原文為: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是為敦煌帶來輝煌與劫難的日子。住敦煌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所僱傭的貧士楊某在磕煙鍋時,偶然發現了一個封閉800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紀的稀世珍寶重見天日。這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使敦煌成為世人矚目的焦事點。
 汪宗翰
汪宗翰我們又大量調閱了其他人寫的相關著作與文章。王道士本名圓籙,一作元錄,是湖北麻城人。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發現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書法、詩詞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這位有學問的知縣身上,企盼著他能解決好藏經洞的保護問題。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寶殿",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汪宗翰取其中幾件畫像、經卷,其他命令王道士暫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數日後,感覺這些文物古蹟的珍貴,便將這幾件畫像和經卷托人帶給了對很懂金石學的甘肅學政葉昌熾,一希望這位懂古蹟的好友認真研究其價值,一方面也希望葉昌熾能夠想到保護和處理藏經洞裡大量文物的辦法。葉氏研究後,自是知道其文物價值之重大,就建議藩台將此寶物運往省府蘭州妥藏。光緒三十年三月英甘肅布政司命敦煌縣令汪宗翰就地“檢點經卷畫像”再次封存,並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但王道士等清正清廉、頗有學問的汪宗翰於1906年初調往蘭州,黃萬春(雲南省保山人)、王家彥、張乃誠等新縣令上任之後,就一直私自將畫像、經卷盜賣給斯坦因等人。就這樣,王道士不斷地將這些珍貴文物賣往法國、英國、沙俄、日本等國的購買者,宣統二年(1910年),在敦煌文物運京保管之際,他又私藏若干。這批文物在運送途中,不斷遭受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洗劫!在這個過程中,汪宗翰發現其文物的珍貴价值,也以實物和書信的方式上報了藏經洞的情況,在任期間,做到了“就地封存”。汪宗翰為發現文物價值、真實上報文物價值、妥善保管封存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04年秋,敦煌欠收,民眾作亂,縣令汪宗翰一方面出售自己的畫作、書法等作品,還說服當地富庶人家捐錢捐糧,以助災民度過困境,一方面又號召當地百姓秋種自救等。汪宗翰並不因為由吏部貶職地方縣令而意冷,而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汪宗翰救災政治有方,護文物有功,朝廷賞其戴花翎五品銜。1906調蘭州,戊申(1908)調署華亭縣事,接補張掖縣知縣。後復調吏部,晉封中憲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內閣學士等,誥封奉政大夫(從二品)。
故居和墳墓
清朝敦煌縣令汪宗翰 故居和 墳墓在湖北通山被發現!
湖北日報訊 (記者汪明、通訊員雪雁鳴)2013年12月6日,清朝敦煌縣令汪宗翰的故居和墳墓在通山闖王鎮汪家畈被發現。
清朝敦煌縣令汪宗翰的故居和墳墓在通山縣闖王鎮汪家畈被發現。我省文化名人、湖北日報群工部主任、高級記者楊耕耘,汪宗翰第五代孫汪漢斌,縣黨校常務副校長孔帆升,鹹寧周刊、通山周刊、通山作協等記者作家到該地採訪汪宗翰的生平事跡,在村支部和村民的幫助下,找到了汪宗翰的故居,並在故居後山發現了汪宗翰的墳墓。
1900年,湖北麻城人王圓籙(道士)發現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1902年3月,汪宗翰調任敦煌縣令,王道士向汪宗翰報告了此事,汪宗翰隨即向甘肅學政葉昌熾寫了書面報告,得到的答覆是: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守。汪宗翰隨後趕到藏經洞,組織人員清點封存文物,對莫高窟文物保護起到了一定作用。
 汪宗翰
汪宗翰關於敦煌縣令汪宗翰故居
位於湖北省通山縣闖王鎮汪家畈的老屋。老屋鄉親們對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非常熱情,來到汪宗翰縣令老屋。只見老屋青磚灰瓦,重門深鎖;屋前屋後,荒草淒淒;斷垣殘壁,破敗不堪。從老屋占地面積仍能看到當年輝煌過,熱鬧過,人氣旺盛過。我們站在老屋前長滿雜草的空場上,等待拿鎖匙的人,村主任告訴我們,這空場本是老屋的正堂,遭日本人燒毀了,土改年間分給了當地居民居住,直到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汪漢斌的父親出錢重新把老屋買了回來。幾番尋找仍沒找到開鎖人,經汪漢斌同意,由村主任用石頭砸開後門。
 破敗的老屋雜草叢生
破敗的老屋雜草叢生 故居高處的雕花樑柱
故居高處的雕花樑柱 故居屋裡瓦礫雜草之間
故居屋裡瓦礫雜草之間當門被砸開的瞬間,一股涼氣襲來,與冬日暖陽混合交匯,這一交匯,使歷史重門大開,讓一段破落殘缺的過往展現在我們眼前。大夥讓汪漢斌先進屋,我們尾隨著汪宗翰的第五代長孫,踏進曾經有汪宗翰生活起居的空間裡,踩在瓦礫聲聲,卻千百年不變的土地上。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尋找先人的蹤跡,找尋曾經的尋常百姓生活,曾經的悲歡與離合……屋內隨處是瓦礫,隨處是斷梁腐柱,高處的磚瓦與大小雕畫橫樑,擠擠挨挨,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牆壁上殘留有“打土豪分田地”等帶著時代烙印的標語。這一切,仿佛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顫微微地依門遠望,等待遠方的歸人……
 汪宗翰故居
汪宗翰故居關於敦煌縣令汪宗翰墳墓
從老屋出來,直接上到後山,也就是家譜里說到的“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異乾向有碑。”當叢林裡一座雜草叢生,碑殘冢荒的墳塋出現在眼前時,所有人有些驚慌遺憾地說,完了,碑沒有了!有老人說,墳前的大碑前幾年讓收文物的人買去了,是黑色大理石的,很大很多字。那個讓人買走的碑牌,當是前邊我們在家譜里讀到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
 汪公宗翰大人碑文
汪公宗翰大人碑文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汪漢斌走到墳頭前,搬起一個殘破的白色大理石碑,只見上邊有字,大夥從失望轉為興奮。汪漢斌用雙手拂去碑上的泥土,有字清晰起來,碑中間的字是汪宗翰與夫人方氏名字同刻碑上:“清點吏部主政賜進士出生誥授朝義大夫貢考汪公官聲宗翰府君壽成,汪母方氏壽域佳城”。右側文字是父母生歿年間,左側是立碑時間:“民國八年歲次未秋月吉旦”及立碑子孫的名字。看到這些時,我們都鬆了一口氣, 此墳此碑以及前邊看到的汪氏家譜,足以證明汪宗翰為官時和告老還鄉後的事實,那段有關他的歷史,通過我們的尋找,通過這些文獻的記載,在世人眼前清澈明朗開來,不再是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猜想。
 汪宗翰
汪宗翰闖王鎮一文一武,武有闖王李自成,文有汪宗翰,如果能夠把汪宗翰的故居重新修葺,結合汪氏宗祠一起開發旅遊,告訴世人,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史上,汪宗翰當任縣令時所做的,以及他少年苦讀和告老還鄉後的故事,都是可以挖掘的歷史文化,以此教育後人……
闖王鎮黨委書記王暉表示,一定做好汪宗翰故居和墳墓的保護工作,儘快修復好故居,努力打造好“敦煌縣令汪宗翰故居”這一旅遊品牌,為闖王鎮除了闖王陵外再添一景點。同時也為通山旅遊再添一新的旅遊景觀。
歷史考證
題記 :湖北通山縣政協啟動撰寫《通山古民居》工作,我的任務有汪宗翰故居。前不久,市政協文史委主任王親賢,在縣政協王賢旨副主席、文史委主任方近東等陪同下,考察了闖王鎮汪家畈汪宗翰故居。今日先發一篇寫於2013年關於汪宗翰的舊作,以便讀者了解汪宗翰其人其事……
汪宗翰,字栗庵,湖北通山人,與王道士算是“老鄉”。汪宗翰諳熟歷史文化,在敦煌縣令任上,曾蒐集過當地的一些漢簡。汪不愧為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當他見到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後,立即判斷出了這些經卷的不同一般,1903年冬天,將這一訊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
(一)
那天,久識的楊老師打來電話,說次日來通山,陪汪宗翰的第五代長孫與我相見。除了高興,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一位媒體文化人對歷史的認真和負責。
 2013年冬,汪漢斌在太祖汪宗翰的墓前
2013年冬,汪漢斌在太祖汪宗翰的墓前我與楊老師相識於2012年8月份湖北作家採風團一同去新疆。在參觀敦煌的時候,我為楊老師講述了10年前,即2001年我獨行西北到敦煌,在相關歷史文獻中了解到,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向時任敦煌縣縣令送過經卷,大約是3年後汪宗翰任縣令,王道士也向他遞獻過經卷,汪縣令判斷經卷為重要文物,並書面向蘭州學政葉昌熾匯報過此事。當我非常認真地告訴楊老師,汪縣令是我們通山人時,楊老師說:“只知道與敦煌被發現的兩個重要當事人,王道士與汪縣令都是湖北人,沒想到汪來自你們通山。”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那年,敦煌縣令是嚴澤。一年後由湖南沅江人氏鄔緒棣接任。敦煌的地方官員和士紳有許多人接受過王道士的經卷贈品,有的施主也得到過。但都沒有作為一件大事上報。1902年3月,汪宗翰出任敦煌縣縣令時,也得到了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和絹畫。
劉詩平、孟憲實著《敦煌百年》記載:汪宗翰,字栗庵,湖北通山人,與王道士算是“老鄉”。汪宗翰諳熟歷史文化,在敦煌縣令任上,曾蒐集過當地的一些漢簡。汪不愧為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當他見到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後,立即判斷出了這些經卷的不同一般,1903年冬天,將這一訊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
 劉詩平、孟憲實著《敦煌百年》
劉詩平、孟憲實著《敦煌百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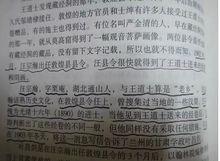 《敦煌百年》文中段落
《敦煌百年》文中段落而這一上報,才讓世界知道了這一文化奇蹟。
我只是觸景生情地為楊老師講述了這么一位人物,在浩瀚滄桑的敦煌史上,汪縣令是淹沒在歷史塵埃里鮮為人知的角色,他甚至不及王道士的名氣,畢竟王道士背負的罵名和沉重更多,而這位當朝縣令,正是他以體制官員的身份,以上書的形式,向朝廷官員匯報了這驚天動地的大發現。然而,清朝政府的腐敗和麻木,一樣沒有引起重視,百年敦煌,成了中華民族苦難心靈的歷程。
楊老師不但是資深媒體人,更是有心人。我講的故事,有意無意地,留在他的心裡。一次同學聚會時,各自講到自己的祖人,發小同學汪漢斌說家族裡出過一位清朝進士,在敦煌任過縣令。因為不了解他任縣令其間是否與敦煌藏品的流失有無關係,反而一直不敢言說。楊老師非常敏感地問這位縣令叫什麼,當他說出汪宗翰三個字時,楊老師馬上為他講了我寫《敦煌感傷》等文中提到的汪縣令,正是汪漢斌的太祖父。這一發現,讓汪漢斌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了楊老師電話聯繫我。
雖然出生在沙洋,汪漢斌自小就知道自己是通山寶石鄉(現更名為闖王鎮)汪家畈人,太祖爺爺的勤學苦讀一直是父親教育他的榜樣。1982年,父親把他送回通山,託付給親戚到通山一中讀高三,並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在汪家畈還有一間祖上留下的老屋,抗戰時曾是通山縣政府所駐,被侵華日軍燒去了一半,土改時分給了當地人居住。1982年父親送他回通山讀書時,又花錢把老屋買了回來,但一直鎖在那裡沒有整修過。一晃,近20年沒有回來過了,90歲的老父更是惦念老屋是否垮掉,汪漢斌這些年忙於事業,無暇回祖屋看看。
茫茫人海,本是通山人的汪漢斌,卻因為我與楊老師的相識與牽引才得以相見。我做夢也不曾想,與楊老師的相遇,在敦煌為他講的故事,是老天埋下的伏筆。這一伏筆,在上帝的揮手之間,掀開一段不為人知的,有關敦煌、有關汪宗翰的,那段塵封在歷史深處的往事。難道,這是天意?難道,汪縣令在天有靈?
 當年在汪宗翰主持下籌建的汪氏宗祠正門
當年在汪宗翰主持下籌建的汪氏宗祠正門
(二)
當楊老師帶著汪漢斌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努力在他身上尋找先祖汪宗翰的影子。我曾經這樣描寫汪縣令:“我想像中的汪縣令,是儒雅而漫不經心的,是飽讀詩書又有些許忠厚的。”握手之間,只見他低頭含笑,憨厚少言,連聲道“慚愧”。並說,到目前為止他沒有寫過關於家族這位一直引以為驕傲的太祖,而我這個外人卻寫過他太祖不少文字。我笑說這是緣分,我始終相信,冥冥中我和你太祖是有緣的,總是感覺他在天之靈囑託我什麼似的。2001年,獨行西北,正是發現了汪縣令,才讓我寫下《敦煌感傷》;2009年寫《一蓑風雨百年情》,是讀過《敦煌感傷》的朋友在闖王鎮芭蕉灣發現了汪縣令送給姑母80壽辰的牌匾;2010年再寫《用文字帶你回家鄉》,那時沒有更詳實的資料汪縣令了解更多,只聽人說他出任敦煌縣令後沒有回過故鄉,寫這一篇時我甚至傷感流淚,總是感覺有一雙憂鬱的眼在天上看著我;去年,從新疆回來後寫下的《佛國》一文也寫到他……
 當年在汪宗翰主持下籌建的汪氏宗祠
當年在汪宗翰主持下籌建的汪氏宗祠汪漢斌的沉默讓人有些沉重。剎那,我似乎看到了汪宗翰的身影,漫不經心,憂鬱寡言,內斂沉穩。聽我滔滔之後,含笑道:太祖在67歲時告老還鄉,而且他的墳墓就在汪家畈。這話讓我大吃一驚!甚至些許興奮,但還是將信將疑。畢竟他自己也有幾十年沒有回了,他的話能算數嗎?他太祖的墳墓還會存在嗎?汪漢斌看出了我的疑惑,於是告訴我他有個在橫石醫院(現更名為九宮山鎮衛生院)退休的表哥,叫陶祖旭,他知道的更多。那么,揭開歷史的面紗,了解更多的汪宗翰,得從這位叫陶祖旭的汪漢斌的表哥開始!
車子出發了,電話聯繫上了汪漢斌的表哥,讓他在衛生院等我們。從縣城到九宮山鎮30分鐘的路程,見到表哥陶祖旭,這位老中醫,乾淨幹練中透著文氣,見面便斥責汪漢斌:你太祖的墳幾十年不回來祭拜,讓它雜草叢生,石碑殘破,修譜也沒有回音,祖宗祠修建落成族人找不到你們,怎么可以這樣忘本呢?汪漢斌面對表哥的斥責,沉默不語。
車子再次出發,向不遠處的汪家畈而去。車內,我和陶祖旭老人聊了起來。老人說他和漢斌是舅母親,陶父是汪漢斌的嫡親舅舅,汪的母親是他的親姑母。我迫不及待地問,汪宗翰當年確實是告老還鄉了的嗎?老人爽朗地大聲道:是的!回來時67歲,90歲的老娘還在,當67歲的兒子在堂上拜老娘時,受拜後的老娘竟安詳地走了。老人多有福啊!水有源木有根,說汪宗翰,還得從他的母親說起……於是,老人開始為我們講述那些不為人知的,汪家家族的如煙往事……
 現在的汪氏宗祠外貌
現在的汪氏宗祠外貌 現在的汪氏宗祠內貌
現在的汪氏宗祠內貌 祠堂內-文高天下-牌匾
祠堂內-文高天下-牌匾(三)
汪宗翰的母親叫巧姑娘,為什麼叫巧姑娘,這裡邊有傳奇故事。巧姑娘出生時,已是家裡的第八個女兒,這個女兒的出生,為已經生出七個女兒未盼來兒子的母親痛心和不齒,於是狠心用雙手把女兒掐死。就在山上挖好了坑埋葬這個不幸生命的那一刻,已經沒有呼吸的女嬰突然哭出聲來。於是,這個不招人喜歡的生命頑強地活了下來,並取名為巧姑娘。
 2017年5月政協一行在汪氏宗祠
2017年5月政協一行在汪氏宗祠巧姑娘長大後嫁給汪宗翰的父親,育有三個兒子。汪父是生意人,以販賣茶葉苧麻掙得一份不薄的家業,經常走南闖北的父親,因為生意上的事,有一次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和江邊上的一位寡婦好上了,並答應將來有一天會帶她回老家做二房。在汪父離開上海回老家時,寡婦變賣部分家產,貼補汪父把生意做大,可是汪父回老家後卻再也沒有回到上海。面對一去不復返的男人,寡婦在悲憤交加中,一索懸樑結果了性命。後來,寡婦的屋子開始鬧鬼,沒人敢住。傳說一位來自湖北通山的水客(跑碼頭的生意人),因不怕鬼而住進了寡婦的屋子,迷糊中做一夢,夢見一女子問他是否是湖北通山人,是否知道有個叫汪家畈的地方,並讓他帶她回汪家畈。水客問如何帶她,女子說,只要過河上船下碼頭時叫一聲她的名字即可,並以一枚金釵致謝。水客醒來,看到桌上真有一枚金釵。於是在回家的時候,只要遇到上船過碼頭總會叫上女子的名字,直至到當年的寶石鄉汪家畈。
 破敗的老屋雜草叢生
破敗的老屋雜草叢生奇怪的事發生了!汪宗翰一兄一弟不明原因暴死,父親一夜之間半瘋半癲。面對致命的打擊,巧姑娘痛問丈夫是否做了惡事。在汪父去世前,突然清醒地把妻子和兒子汪宗翰叫到身邊,告訴妻兒他曾經在上海的那段姻緣,並要妻子答應,不但要教育兒子為人正派好好讀書諸惡不做,同時要她把兒子寫給(過繼)上海那位女子為兒子,給她名份,說兩個兒子的離世就是遭的報應。
丈夫去世後,巧姑娘帶著兒子,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用盡全力供養兒子汪宗翰讀書。汪宗翰不負母望,用心苦讀,而且讀書天份很高。夏天為了躲避蚊子的叮咬,把雙腳泡在水桶里讀書;冬天為了節約柴火和避寒,常常到對面山上宋朝建的一座叫“雲梯寺”的寺廟用功學習。傳說中汪宗翰記憶力超強,看人賣肉,誰買了幾斤幾兩,一頭豬賣了多少客,共賣出多少肉,收銀錢多少,他都能一一背得下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光緒十六年(1890),汪宗翰考上了進士。巧姑娘教子有方和汪宗翰苦讀的故事,在當地,至今被傳為佳話。值得一提的是,自汪宗翰之後到汪漢斌,汪家一直是一子單傳。
 查汪氏宗譜
查汪氏宗譜陶老人真實的講述,把我們帶進汪家百年前風雨飄搖,悲歡離合的往事深深處,不能釋懷。聽完祖人的故事,只見汪漢斌更加沉默了。很快,落回現實,回到眼前,氣派恢弘的汪家祠堂已在眼前……
(四)
 汪宗翰
汪宗翰記得2009年尋找汪宗翰的蹤跡時,只剩門樓,屋內書聲朗朗的祠堂,如今卻氣勢宏偉,飛檐翹角,煥然一新。一對高大的石獅子雄居門前,正門兩側柱子上的對聯,還是我09年看到的那一幅:“綠水環門錦漲潭花三月暖,丹爐列嶂香飄煙樹五雲高”。陶老說這是前年修建的新祠堂,並對此聯倒背如流。聞訊趕來的村主任告訴我們,2011年正月十五,由汪濟世支書發起,並要求他遠在蘇州做生意的弟弟汪義芳出資100萬元做首建資金,及各汪姓鄉民集資建成,並說門前的對聯仍是1888年間栗庵發起建祠堂時親自擬作,並請書法家王鳳池書寫。不竟感嘆,那年看得書聲朗朗的舊祠堂,有多少汪宗翰運籌帷幄的操勞身影。如今盛世大好,子孫們重建祠堂,合理保留了先祖初始的精神和文化,延續這份血脈。汪縣令雖已作古,他所吟誦的精神點畫仍在。這,當是文化傳承的力量。
從側門跨進祠堂,面積大而寬闊得令人驚異讚嘆,不愧是湖北第一宗祠。只見戲台樓閣,楹聯字賦,漸次遞進;雕樑畫棟,色彩艷麗;廓回柱立,天井見日;門框格子,曲尺訴古;一進幾重,金碧輝煌,氣派十分。既保持了復古風格,又透著現代文明的氣息。“望思、忠孝堂、文高天下、祭如在”等這些傳頌著民俗古風的文化,當讓祖先欣慰怡然。在祠堂最里端的屋內,依次放著汪氏祖人的牌位,紅綢垂吊,龍鳳呈祥,端莊肅穆。個個牌位是列祖列宗的存在,存於天地之間,存於子孫萬代的心靈深處,從而延續香火,教育後人。聽說汪宗翰的後人回來了,附近的鄉民一個個趕來問長問短,感嘆唏噓。村主任對汪漢斌說,建宗祠時找過你們多次,都沒有聯繫上。汪漢斌點燃香火,神情凝重地參拜。雖然這一柱香這一拜來得太遲,畢竟是來了。尋根問祖拜先人,無論你身在何方,無論你官居何職,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沒有人敢說自己沒有根沒有源,沒有縈繞心間的鄉愁。
這時,有人拿來了《汪氏宗譜》上下卷,我們有些興奮地開始翻閱,只見譜上有關汪宗翰的文字記載這樣寫道:“ 會相,潤公次子。字步武,號栗庵,原名耀祖,更名宗翰,晚年自號壠溪,又號退思老人。十九歲冠縣軍,入邑庠。光緒已卯科舉人,揀選知縣,已醜科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庚寅科會試,中九十二名進士,欽點主事,劍(僉)分吏部稽勛司兼考公(功)司行走。在部供職三年,改歸截取,選甘肅鎮原縣知縣,加同知縣(銜)。辛丑,入內廉(入充甘肅)同考官,調補敦煌縣知縣,壬寅三月到任。甲辰,大計卓異,賞戴花翔。丙午二月交卸,晉省充法政學堂教務長差。戊申,調署華亭縣事,又調補張掖,改選口口。在任十數年,行無川費,大府籌款口之,至漢畢(中)。民國軍起,繞道回籍,求讀門不問外事,年六十有七矣。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已七月二十九日辰時,歿於民國九年庚申六月二十七日卯時。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異乾向,有碑。娶方氏,生子一,維覃,煌。生女一,早殤。復娶余氏。”短短几百字,攘颳了汪宗翰不平凡的一生。
翻看家譜時,一位老婦人趕來,看著汪漢斌說,我們汪家有這祠堂還得感謝你家先祖,是他最初發起才有了我們汪姓的發展,他的功德我們世世代代記得呢。當年重建的時候,族裡派人到處找你們,不僅是要你回家認祖,更是對你太祖的世代不忘。一位姓汪的退休副鎮長說,我們不辭辛勞地找你,是因為你才是我們汪家畈首建祠堂者的正宗嫡孫。汪漢斌聽了連連點頭稱是。這些好感與謝意,是因為汪宗翰首建汪家祠堂的功德。這份功德,在鄉民的心裡,不僅是記住,更多的是把這份敬重轉移到了眼前這個正宗嫡孫身上。可見汪宗翰對家族和後人的深遠影響。相比起表哥的斥責,村里人對這位嫡孫更多的是寬厚。
譜文里不但有汪宗翰的出生、讀書、考功名、娶妻生子等記載,也有他為節婦、孺人等人撰寫的序跋。更難得的是,還有他任敦煌縣令時,民眾寫給他的信,相當於現在的“感謝信”,最後落款是“敦煌合邑士民同妻首拜”。同時有“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楊老師連聲道,這太珍貴了!邊說邊擇段而讀:“ ……壬寅,調補敦煌。甫下車,適東鄉水溢,方百里皆成澤國,饑民待哺,請賑未遂。公乃自捐巨款,代籌生計,以蘇民困;造堤梁,修社倉,以興民利;設義塾、建書院、以牖民智。教化大行,風俗丕變。歲癸卯,鄰邑苦蝗,公禱於天,蝗越境而飛,群鴉逐其後,遂不為災,人鹹謂有神功助。敦民頌以‘胸羅星海,心印月泉;慈同千佛,春度兩關’。及‘樂只君子,壽考不忘’牌、傘……”洋洋灑灑的千字碑文,最後落款“翰林院編修年如弟蓮溪吳懷清拜撰。前清歲貢生門人舒祖芬篆額。大冶司法官外孫成清琴書丹”。 所有這些珍貴資料後邊皆注有“選自湖北通山《汪氏宗譜·忠孝堂》民國丁丑年重修本”。楊老師一邊讀一邊為我們釋義。那些越百年之久的字裡行間,再現了汪宗翰的生平事跡,透著他的品行高德,讓後人高山仰止。
(五)
從祠堂出來,來到汪家老屋。只見老屋青磚灰瓦,重門深鎖;屋前屋後,荒草淒淒;斷垣殘壁,破敗不堪。從老屋占地面積仍能看到當年輝煌過,熱鬧過,人氣旺盛過。我們站在老屋前長滿雜草的空場上,等待拿鎖匙的人,村主任告訴我們,這空場本是老屋的正堂,遭日本人燒毀了,土改年間分給了當地居民居住,直到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汪漢斌的父親出錢重新把老屋買了回來。幾番尋找仍沒找到開鎖人,經汪漢斌同意,由村主任用石頭砸開後門。
 和現任闖王鎮李雪梅鎮長一起在故居後側門
和現任闖王鎮李雪梅鎮長一起在故居後側門 故居高處的雕花樑柱
故居高處的雕花樑柱 故居屋裡瓦礫雜草之間
故居屋裡瓦礫雜草之間當門被砸開的瞬間,一股涼氣襲來,與冬日暖陽混合交匯,這一交匯,使歷史重門大開,讓一段破落殘缺的過往展現在我們眼前。大夥讓汪漢斌先進屋,我們尾隨著汪宗翰的第五代長孫,踏進曾經有汪宗翰生活起居的空間裡,踩在瓦礫聲聲,卻千百年不變的土地上。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尋找先人的蹤跡,找尋曾經的尋常百姓生活,曾經的悲歡與離合……屋內隨處是瓦礫,隨處是斷梁腐柱,高處的磚瓦與大小雕畫橫樑,擠擠挨挨,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牆壁上殘留有“打土豪分田地”等帶著時代烙印的標語。這一切,仿佛一位
 王親賢主任考察碑文
王親賢主任考察碑文風燭殘年的老人,顫微微地依門遠望,等待遠方的歸人……
從老屋出來,直接上到後山,也就是家譜里說到的“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異乾向有碑。”當叢林裡一座雜草叢生,碑殘冢荒的墳塋出現在眼前時,所有人有些驚慌遺憾地說,完了,碑沒有了!有老人說,墳前的大碑前幾年讓收文物的人買去了,是黑色大理石的,很大很多字。那個讓人買走的碑牌,當是前邊我們在家譜里讀到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
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汪漢斌走到墳頭前,搬起一個殘破的白色大理石碑,只見上邊有字,大夥從失望轉為興奮。汪漢斌用雙手拂去碑上的泥土,有字清晰起來,碑中間的字是汪宗翰與夫人方氏名字同刻碑上:“清點吏部主政賜進士出生誥授朝義大夫貢考汪公官聲宗翰府君壽成,汪母方氏壽域佳城”。右側文字是父母生歿年間,左側是立碑時間:“民國八年歲次未秋月吉旦”及立碑子孫的名字。看到這些時,我們都鬆了一口氣,此墳此碑以及前邊看到的汪氏家譜,足以證明汪宗翰為官時和告老還鄉後的事實,那段有關他的歷史,通過我們的尋找,通過這些文獻的記載,在世人眼前清澈明朗開來,不再是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猜想。
 汪公宗翰大人碑文
汪公宗翰大人碑文撫正石碑,汪漢斌痴痴地在碑前蹲了許久,然後非常肅穆地跪了下來,深情三拜。這三拜,也讓我這個旁觀者淚濕衣襟……
(六)
尋找有了結果,我們來到闖王鎮政府。
小會議室內,面對闖王鎮的書記和鎮長對汪宗翰這個人物的一臉茫然,在楊老師和我作過簡單介紹後,才了知所以然。楊老師說,闖王鎮一文一武,武有闖王,文有汪宗翰,如果能夠把汪宗翰的故居重新修葺,結合汪氏宗祠一起開發旅遊,告訴世人,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史上,汪宗翰當任縣令時所做的,以及他少年苦讀和告老還鄉後的故事,都是可以挖掘的歷史文化,以此教育後人……
 在闖王鎮政府
在闖王鎮政府汪宗翰這個名字,於我,前前後後十多年,還會更長久地存於心間。一天尋訪過後,萬千感慨,揮之不去。從2001年我到敦煌發現汪宗翰任縣令的這段歷史,到今天和他的曾孫一起隨行尋找,整整13年,十多年在歷史長河只是水一滴,可又是那么長。那一刻,我想到的,是以歷史散文見長的著名作家曾紀鑫老師的一句話:許多時候,歷史真的就是一種緣分。
原文作者:倪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