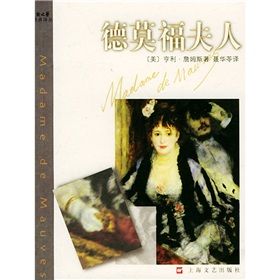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冰清玉潔的美國少女和一個法國名門望族的花花公子的婚姻故事。年輕的美國人郎莫爾到了巴黎,愛上德莫福夫人。德莫福男爵終日花天酒地,荒淫無度,並有個法國情婦;他甚至還鼓勵郎莫爾去勾引自己的妻子。德莫福夫人斷然拒絕了郎莫爾,仍然忠於丈夫。幾年後,郎莫爾才知道,德莫福男爵終於向妻子懺悔,並真的愛上了她;但遭到了她冷峻的拒絕。德莫福男爵最終因絕望而自殺。
作者簡介德莫福夫人
詹姆斯,H.(Henry James 1843-1916) ,小說家。1843年4月15日出生於紐約。父親亨利是哲學家、神學家,長兄威廉是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偽創始人。他生長在一個富有教養的家庭中,象當時許多有素養的美國人一樣,羨慕古老的歐洲文明。自幼往來於歐美之間,1875年起定居倫敦。1915年因美國一時未曾參加世界大戰,忿而加入英國籍。1916年2月28日於倫敦病故。
詹姆斯幼年在家庭教師指導下學習。1862至1864年在哈佛法學院求學,並與著名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威·迪.豪威爾斯相識。1864年開始寫作文學評論與短篇小說。1875至1876年在巴黎結識著名作家屠格涅夫、莫泊桑、福樓拜、都德和左拉,以及英國作家羅·路·斯蒂文森等。他因殘疾未能在南北戰爭時服役。長期以來勤奮寫作,著作浩繁。1911年獲得哈佛大學的榮譽學位,1912年獲得牛津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稱號。1916年英國政府授予他最高文職勳章。
詹姆斯的主要作品是小說,此外也寫了許多文學評論、遊記、傳記和劇本。他的小說常寫美國人和歐洲人交往之間的問題;成人的罪惡如何影響並摧殘了純潔、聰慧的兒童;物質與精神之間的矛盾;藝術家的孤獨,作家和藝術家的生活等:這表明作家對個人道德品質的濃厚興趣。這是深有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所懷有的人文主義傾向,而不是人們所熟悉的對貧苦大眾的人道主義同情。作者讚美優美而淳厚的品德,把個人品質高高置於物質利益甚至文化教養之上,個人品質和他人利益高於一切。
重要的長篇小說有《一個美國人》(1876-1877),《貴婦人的畫像》(1881),《波士頓人》(1885-188g),《卡薩瑪西瑪公主》(1885-1886),《波音敦的珍藏品》(1896),《梅西所知道的》(1897),《未成熟的少年時代》(1899),《聖泉》(1901)和後期的三部作品《鴿翼》(1902)、《專使》(1903)和《金碗》(1904)。
著名的中短篇小說有《黛西·密勒》(1878),《艾斯朋遺稿》(1888),《真正的貨色》(1890),《小學生》(18992),《螺絲在擰緊》(1898),《叢林猛獸》(1903),《快樂的一角》(1909),以及一組描寫作家、藝術家生活的中短篇小說。
詹姆斯寫了許多很有見地的評論文章,涉及英、美、法等國作家,如喬治。艾略特、斯蒂文森、安東尼·特羅洛普、霍桑、愛默生、巴爾扎克、喬治·桑以及屠格涅夫等。文集有《法國詩人和小說家》(1878),《一組不完整的畫像》(1888),《觀感與評論》(1908),《有關小說家的短評》(1914),《筆記與評論》(1921)等。他的遊記有《大西洋彼岸素描》(1875),《所到各地圖景》(1883),《在法國的一次小小旅遊》(1885),《在英國的時候》(1905),《美國所見》(1907),《在義大利的時候》(1909)。自傳三種:《童年及其他》(1913),《作為兒子與兄弟》(1914),《中年》(1917)。
目錄
關於《德莫福夫人》
德莫福夫人
精彩書摘
這位陌生的太太,乍看之下,也許並不是個美人,也不像個美國人,但再過細一看,就會發覺她的確長得很美,也的確是個美國人。她生得窈窕姣美,臉色本是蒼白的,卻泛著一層淡淡的紅暈,顯然是剛剛激動過一陣子的。最使郎莫爾心動的,是她臉上那一對柔美的、無精打采的灰色眸子,配上一張特別富於表情而隨時預備說話的嘴。她的前額,若照古美人的標準來說,顯得有一點兒過寬,而她那一頭棕色的濃髮梳的式樣又過了時,那種髮型在當時是非常難看的。她頸子纖細,胸部單薄,但這與她頭部一些利落而迷人的動作卻更相稱,她愛時而把頭向後那么一擺,非常專注的樣子,她那鴿兒似的眸子卻又向旁一瞥。她為人似乎很機警,卻又是冷漠的,安靜而有思想,卻又是忐忑不安的。郎莫爾一下就看出來了,她即使算不上是個艷光逼人的美人兒,至少她這個人是非常逗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印象使得他對她特別大度,不挑三剔四了。他察覺他這一來是打斷了兩位太太的知心話,於是,當他由梅姬的媽媽(卓泊爾太太)那兒得知她要搭六點鐘那趟火車回巴黎之後,便覺得應該是告辭的時候了。他答應和她在車站見面。
也許就是因為這幾句俏皮話傷了德莫福老太太的心,當俞斐美在那兒的期間,老太太多半是耽在她自己的房中,於是,俞斐美那天使般的天真就完全聽任這位男爵去擺布了。然而,最糟糕不過的事,是俞斐美的天真也就因此被挑逗得更其天真了。德莫福先生就是這個女孩粉紅色夢境中英雄的現身,與她幻想中的那個人物竟完全相符合,符合得叫她害怕,就如同她看見了畫中人從畫框中走下來一樣的害怕。他正是35歲,這個年齡,說老吧,卻大有熱情一番的可能,說年輕吧,他所想得出的見解又足可使一個單純的女孩子聽起來認為是個殊榮。他也許比俞斐美那位嚴峻的、唐·吉訶德式的理想人物稍稍漂亮一點兒,但是,他那副漂亮面孔,沒有幾天工夫,她也就看順了眼,就是他長的醜陋,這么幾天她也會看順眼的。他沉靜、厚重、佼佼不凡。他很少講話,就是講,也不之乎者也地咬文嚼字,語調中有一種高雅的味道,一天臨了,那些話還在這個女孩的耳畔繚繞。他很少直接對她獻殷勤,但他偶爾說一兩句話(倘若他只問她是否可以在她面前抽菸),便非常溫存地隨之一笑。
她的確有許多地方是使他迷惑不解的,他對她一無所知,便根據她的婚姻史作了許多推測臆斷。她是為愛情而結婚的,並且是用她全靈魂對這個婚姻作賭注。對於這一點,他深信不疑。她嫁給一個法國人,並不是因為那樣就可靠近巴黎,就可以靠近帽子供應地;他相信,當初她對婚姻幸福的憧憬,與她目前這種便於逛商店、精神枯燥的生活,適得其反。但是,她經過了一個什麼樣的心靈過程(人的心靈不論馳騁得多快,辨別是非的本能總會趕上它,但是那種辨別是非的本能怎么莫名其妙地就停頓了?),她才鍾情於一個輕狂的法國人呢?郎莫爾無需人講,他知道德莫福先生是個輕浮人;他的眼睛、鼻子、嘴以及他的馬車,都印著輕浮的標記。對於法國女人,郎莫爾不怎么寬厚,至少他(所表現的就是如此)不怎么奉承;他曾經鼓著勇氣拿一封介紹信去看一位很好的貴婦人,在他見她第一面之後.立刻寫在他的記事本上的評語是“有如金屬”。他覺得所有的法國女人全是屬於這一類型。德莫福夫人為什麼選擇了一個法國女人的命運呢?她的性格有一種香味兒,那種香味兒就是最亮的金屬也不會有的。有一天,他直率地問她移植到法國來是否對她沒有一點兒損失——是否深深地感到她與“所有這些人”是絕對不同的。她沉默了一會兒,他以為她是在考慮對於他如此沒禮貌地影射她的丈夫是否應該發火。他幾乎寧願她發火;那似乎還可證明她對痛苦的隱忍還有個限度。
……
書摘1
有一會兒,他的話涌到嘴邊,他想說他的時間並沒浪費,但看到她臉上那副誠摯的神情,那一套陳腐的恭維話便咽下去了。她站在那兒,嚴肅之中帶有溫柔,好似一個沒有私慾的天使。郎莫爾感到,倘若把她的話當作是用來引誘他說恭維話的,那就是侮辱了她。“我一兩天就動身,”他回答道,“不過我並不答應你我不回來了。”
“我希望不要那樣,”她僅僅這么說道,“我想我會在這兒耽很久。”
“我要來向你辭行的。”他說道;她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後走進了屋。
他轉過身去,由陽台上慢慢往回走。他覺得,像這樣為了她所堅持的理由而離去,就是表示更了解她,更欽佩她。但是,他心中隱隱約約有些不安,那種不安的情緒,由於半個鐘頭以前她迴避了他所提出的問題,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深了。突然,他在陽台上碰到了德莫福先生,他正靠在欄前,一支雪茄快抽完了。男爵那天的神情,他認為,特別和藹可親,對他伸出了他那漂亮而肥胖的手。郎莫爾站住了;他突然怒火中燒,恨不得大叫著告訴他,他有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告訴他,他連這也不知道應該感到羞愧;告訴他,雖然他那么精明,卻從沒有看進她眼睛的深處。我們知道,男爵認為他自己以前確曾看進過。但是,現在的俞斐美的眼中有點兒什麼是五年以前所沒有的。他們東扯西拉地談了一會兒,德莫福先生用詼諧的語調敘述他的美國之行。他那語調並沒使郎莫爾激動的情緒緩和下來。他似乎認為美國是個大滑稽,而他承認,那滑稽還不錯,他的文雅只使他說到這個地步。郎莫爾一向不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制度臉紅脖子粗地來辯護的人;但男爵那些話證實了他認為法國人淺薄的壞印象是對的。他根本什麼也沒了解到,什麼也沒感受到,什麼也沒體會到。我們這位主人公用眼角瞟了一下他那高貴的側影,暗自想,倘若名門世家的主要好處就是使子孫成為一個如此妄自尊大的笨伯,那他倒要慶幸郎莫爾家是在本世紀內才由一個力爭上遊的木材商人從微賤起家的。德莫福先生當然是不厭其煩地對美國一件怪事,即對女孩子的放縱,大發議論,敘述他如何研究法凼貴族在那兒所得劍的“機會”,住那些研究工作之中,兩個星期的時光,他似乎過得很愜意。“我應該承認,”他說道,“每一次我都被小姐們過度的坦白所鎮服了,她們很會照順自己,比我在法國所看到的一些媽媽們塒她們的女兒照顧得更有效些。”郎莫爾對他這種慷慨的讓步報之以一個最嚴厲的微笑,從心裡詛咒他那自命高人一等的氣派。
最後,他提到他要離開聖日耳曼了,男爵居然對此事大表關切,這未必就逢迎了郎莫爾的心,反而使他感到十分意外。“我非常遺憾,”男爵叫了起來,“我本來希望你在我們這兒過夏的。”郎莫爾囁嚅著說了幾句客套話,心裡卻因為德莫福先生關心他的去留而迷惑不解。“你是德莫福夫人解悶兒的人,”男爵繼續說道,“我告訴你,我衷心感激你的光臨。”
“那對於我也是很大的一個樂趣,”郎莫爾嚴肅地說道,“有一天我還會回來的。”
“請一定回來,”男爵急切地把手搭在他的胳臂上。“你知道,我很信任你!”郎莫爾沉默了一會兒,男爵沉思地抽著雪茄,注視著那裊裊的煙霧。“德莫福夫人是一個相當奇怪的人。”
郎莫爾移動了—下化置,心想,不知他是否要“解釋”一下德莫福夫人這個人。
“因為你既是她同鄉,”男爵繼續說道:“我才放心坦白地講。她只是有一點點病念,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人,這你知道,但有一點點愛胡思亂想,有一點點高不可攀。現在,你知道,她這么樣特別喜歡孤獨。我無法卉她劍任何地方去——去見任何人。我的朋友們見了她的面,她也客客氣氣的,但卻是冷冰凍的。她沒將自己的長處充分發揮出來,每天我都會聽見兩三個朋友對我說:‘你的太太美是美極了;可惜她沒有一點兒精神。’你必定已經看出來了,她真是很有精神的。但說實話,她所需要的只是忘掉她自己。她一個人一坐就是好幾個鐘頭,抱著她的英文書看,從一種陰沉沉的氣氛中看人生,我總覺得那種氣氛就是那些書本散布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懷疑你們的英國作家,”男爵說下去的時候,神態安詳,郎莫爾後來認為那種安詳確實偉大,“是否適於結了婚的年輕女人看。我也不冒充對於他們知道得很多;不過我記得,我們婚後不久,有一天,德莫福夫人自己要為我吟一個什麼華滋華斯的詩,一個叫你們非常佩服的詩人,好像是。我感覺就像是她揪著我的脖子,把我的頭按在一盆白菜湯上面按了半個鐘頭,叫人悶得慌,應該不等別人嚷出來,就先把客廳通通風。但我猜想你是了解他的——了解那個人。我想我太太永也不會原諒我,她發現她嫁的一個人對於文學的欣賞力和對烹調術的欣賞力完傘一樣,我想那一定使她大感意外。但你是一個有各方面修養的人,”男爵說時,一面轉向了郎莫爾,眼睛盯著他表鏈上的鈕子看著,“你什麼都能談,我相信你一定又喜歡繆塞,又喜歡華滋華斯。對她什麼都談談,連繆塞也談。呸,你瞧!我忘記你要走了。那你就儘可能地快回來吧,談談你旅行的情形。要是德莫福夫人也願意出去旅行兩個月,那對她會有益處。那會開開她的眼界,”德莫福先生把他的手杖在空中連連用力晃了好幾下,“那會喚醒她的想像力。她太死板了,你知道,那會讓她明白一個人可以稍為彎一下腰不至於把他折斷。”
他停了一會兒,使勁抽了兩三口煙。然後又轉向郎莫爾,微微點了一下頭,帶著信任的微笑:“我希望你佩服我的坦白。我不會對‘我們’之中任何人講這些話。”
黃昏將近,那一抹留戀不退的餘輝好似成為一片淡金色的微粒浮掠於天際。郎莫爾站著凝視著那些光亮的微粒:他幾乎可以把它們幻想成一群嗡嗡的小蟲子,低吟著一句復唱的歌詞:“她很有精神,她很有精神。”“不錯,她是很有。”他呆板地說道,一面轉向了男爵。德莫福先牛盯了他一眼,仿佛是問他到底在談什麼鬼事。“她是很有智慧,”郎莫爾慢悠悠地說道,“很莢,很賢惠。”
德莫福先乍有一會兒忙著點燃另一支雪茄,點燃之後,便報之以他那信任的微笑,“我懷疑你是在認為我對我太太不公平,小心,小心,年輕人;那樣的猜測是很危險的。一般說來,一個男人對他的太太總足很公平的。比我們對別人的太太,”男爵大笑著叫道,“公平得多!”
郎莫爾日後回憶起來,就用這種想法來支持男爵話中所含的善意:就是認為他當初沒有估量出這一番話底下有一個多么陰沉的深淵。只有有一種由淵底傳來的漸形深沉的回音冥冥之中在他耳畔繚繞。在目前,他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渴望走開,大嚷德莫福先生是一個夜郎自大的傻瓜。他匆忙向他道了聲晚安,並且,他說,這也就算是向他辭行了。
“一定啦,嗯,一定走啦?”德莫福先生問道,幾乎是獨斷地。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