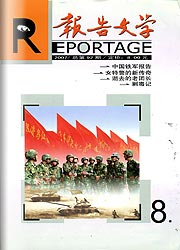徐學龍和他的徒弟們龔國強
前 言這是一次全球40年來烈度最大的地震,又引發了一次世所罕見的海嘯,給印度洋沿岸地區造成巨大的自然災難:十幾米高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勢,瘋狂而兇狠地撲向海島、撲向大陸。肆虐之處,滿目狼藉。一排排房屋如積木般被衝垮,一輛輛汽車像落葉在駭浪中漂浮。這次地震引發的海嘯,席捲印度洋沿岸的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緬甸等國……
國際社會紛紛對受災國表示慰問,並積極提供援助。2005年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乘專機於5日晚抵達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出席將於6日舉行的東協地震和海嘯災後問題領導人特別會議。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溫總理還帶著中國雜技團抵達雅加達慰問受災的難民。
晚上就要演出,雜技團的演員們正抓緊休息。小演員袁潔潔卻在房間練起功來。誰知,一不小心她手臂一軟摔了下來,下巴肌肉被撕裂,胸前被鮮血染紅了一片。和潔潔一起進中國雜技團當教練的四舅徐濤,急忙通知隨團醫生,緊急為她縫了三針。常務副團長、國家一級演員、中國雜技家協會副主席孫力力及時趕來看望,她說:“潔潔,摔的嚴重嗎?”
“不要緊的。”
“今晚的演出非同尋常,溫總理和各國首腦都要出席觀看演出,你能演嗎?”
“放心吧,孫團長,俺中!”
“我要的就是這句話。那好,你抓緊休息。”
袁潔潔含著淚點了點頭。孫團長和醫生剛走出房間,為了適應晚上帶傷演出,袁潔潔在四舅徐濤的幫助下,忍著劇痛又練起“下腰”、“雙手頂”和“單手頂”等基功來。只見她滿臉通紅、臉上豆大的汗珠不斷滾落,以致地毯上洇濕一片片汗水……
夜晚,能容納上千人的雅加達頂級劇場內座無虛席。演出在濃郁的中國民族風格、熱烈歡快的樂曲聲中拉開帷幕,中國雜技團以鮮明的民族特色、神奇的雜技技巧、迷人的中國音樂、絢麗的民族服飾,並借鑑舞蹈、戲曲等姐妹藝術,其精湛的表演深深打動了熱情的雅加達觀眾。當舞台上的追光燈定格在袁潔潔和袁飛演出的《頂碗》時,全場的觀眾屏住了氣,注視著小姑娘和小伙子表演的單手“頂上頂”這一高難度技巧……此時,劇場內只能聽到中國民族音樂的配樂聲,當驚險動作成功完成後,劇場內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太棒了!太棒了!”的叫好聲一浪高過一浪。剛完成這一高難度動作的袁潔潔輕輕地抒了一口氣,臉上綻放出自信的笑容。如此驚險的動作,她卻從容、優美地表演,因為她明白,為了台上這30秒的技巧動作,她和姨兄袁飛在台下已經練了上萬次了,所以,她心裡踏實!
此時此刻,觀眾有誰會知道,袁潔潔是忍著劇痛帶傷演出呢。《頂碗》只是袁潔潔表演的節目之一,她還是《七人頂碗》、《頂功二人技巧》等優秀雜技節目的“主角”。在每個節目裡,高難度的組合動作都少不了她,她倒立的基本功嫻熟、過硬,左、右手交替表演如同外國人使用刀叉一樣自如,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倒立,而她倒立起的形體又特別的美,難怪外國同行看了她的演出後,讚嘆她的倒立像是一尊“東方的維納斯”。
花季少年的袁潔潔,顯得小巧玲瓏,平時甜甜的微笑總是掛在小臉上。這位5歲就從事雜技訓練的“老演員”,在雜技舞台上可謂是身經百戰的驍將,小小年紀的她就已隨團演出了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十多年的雜技訓練,烙下渾身的傷痛,但她無怨無悔,這正體現著她對雜技藝術執著的追求。
當袁潔潔走出表演區,著實為她捏了一把汗的孫團長緊緊地擁抱著袁潔潔,激動地說:“好樣的!好樣的!”
袁潔潔羞赧道:“你說中,就中吧。”
站在一旁的共和國文化部藝術局的一位領導人說:“聽口音,潔潔是河南人吧?”
“是的、是的。”
“你是怎么學上雜技的呀?”
“俺是河南省的,在新蔡縣新星雜技藝術學校跟俺二舅徐學龍、四舅徐濤學練的基功;零二年到團里後,孫團長手把手教俺的……”
“喔、喔,真是山溝里飛出來的金鳳凰啊。”
……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雜技以其勇邁、華彩的風姿走向世界,而現在,用“輝煌”一詞來形容今日之中國雜技藝術是再恰當不過了。 中國雜技從1956年開始參加國際比賽並不斷獲得優異成績,二十世紀的最後10年是中國雜技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10年。現代中國雜技的顯著特點是創作思維的更新,它走出了單純追求高難技巧的窠臼,結合舞蹈、音樂、舞台美術等眾多藝術領域的融合,使雜技作品更新、更難、更美,讓雜技節目從編排上就變得精緻、考究,讓人在賞心悅目、精彩紛呈的節目觀賞中,體會到雜技獨特的美的享受!然而,中國雜技在發展中也遇到了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窘況。
市場經濟就像是一個萬花筒,前所未有的新鮮事物不斷被催生出來。1996年以來,演出市場有所疲軟的情況下,駐馬店市雜技團的“外交”、早已諳熟演出市場的徐學龍和同事朱峰,帶一幫“文藝經紀人”先後來到福建省、黑龍江省、安徽省等雜技團,為這些省級大團“跑票”。所謂“跑票”,就是為演出團體安排演出、推銷演出票,按事先達成的協定分成。無論春夏秋冬、嚴寒酷暑,徐學龍和朱峰都堅持在前面“開地”(即到演出所在省、市、縣文化部門開具演出介紹信),他又將同事們分成幾組,每人帶著“尚方寶劍”的介紹信和一匝匝不同場次的演出票,到一個個被“開了地”的省、市、縣和一個個單位,憑著對雜技藝術事業的執著精神,推銷票價不菲的演出票,為省級大團的商業演出也帶來了一片繁榮景象。徐學龍和同事們在“跑票”中,也賺鼓了“腰包”。
1999年金秋的一天,在福建省福州市演出,劇場爆滿,盛況空前。演出結束後,福建省雜技團團長黃國慶十分高興,特意請徐學龍和朱峰喝酒。
“學龍、小朱啊,這段日子劇場是場場爆滿,說明你們跑票很成功啊!來,幹了這杯酒!”
“主要是你們節目演得好。來,咱共同乾杯!”
“節目演的還算可以吧,可我團演員的年齡都偏大了……”
“你團不是有小演員嗎?”
“說出來你們都不相信,我團培養了十幾個小演員,每年花費上百萬元;六年了,還沒有練出像樣的節目呢。現在演出市場競爭這么激烈,我著急呀!”
真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學龍隨口道:“那——我回新蔡給你團培養學員,咋樣?”
“你、你說啥?”黃國慶團長還沒回過神來。
“我是說,回新蔡建立一個雜技學校,專門招收十歲左右的學員訓練基本功。兩年後,這些學員就可以到你們團排練節目了……”
“有把握嗎?”
“兩年後,你交培訓費,我送人才,你只管派人去挑選嘛。”其實學龍心裡根本就沒有底。
“好、好,那太好了!咱們一言為定。來,為我們雜技藝術事業的繁榮、發展——乾杯!”
“乾杯!”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醉意熏熏的徐學龍躺在賓館的床上,翻來覆去卻沒有一點睡意,他在憧憬未來輝煌的雜技事業,心潮澎湃,浮想聯翩。不知不覺中,他進入了夢鄉,夢見他培養的雜技徒弟們一個個飛向了全國各地,飛向了世界舞台,他們正在一展身手……
“這個能我逞定了!”一向脾氣溫和的徐學龍第一次發了火。妻子知道學龍的牛脾氣,只要他認準的事兒,八頭犍牛都拉不過來,就不再叨叨了。一會兒,只見徐學龍騎上機車,一溜青煙駛出了藝校大門。
“你幹啥去呀?”
“你別管!”
徐學龍風馳電掣般地行駛在回老家澗頭鄉的公路上。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很多。他知道,中國雜技源遠流長,大約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萌芽。唐代時,雜技節目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超技藝。自宋代起,雜技藝術開始從宮廷走向民間,創造了名目繁多的新節目。元朝建立後,雜技淪落為走江湖、耍把戲的江湖藝術。清代藝人則多以家庭親屬為基礎“撂地”演出,或靠趕會流動演出,以維持生計。至近代,雜技更被貶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九流”。解放後,雜技藝術終於又獲得新生,尤其是當代中國雜技已成為深受全世界人民喜愛的藝術奇葩,為什麼人們對雜技還存在偏見呢?
他決定從本村和親戚朋友那裡打開突破口,動員他們的孩子到藝校學習,然後逐步擴大影響。
徐學龍剛到魏營大隊徐新莊路壩,就和老鄉們就打上了招呼。徐學龍下了機車,慌忙給老鄉們遞上香菸,寒暄幾句,學龍就說:“我在城裡辦了一個雜技藝術學校,誰家的孩子願意學雜技就去找我?”
“學那弄啥?弄不好,就學壞了。”大炮叔直言道。
“看大炮叔說的,我咋能讓孩子學壞呢?”
“你沒看現在廟會上演的都是啥?小姑娘跳那光屁股舞,連老祖宗的臉都丟光咧。”
“人家那是野班子,咱辦的是學校。孩子練好基本功後,我就送他們去那省、市級雜技團,到時候還出國演出哩。你看——我的閨女、兒子到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都五年了,去法國、英國、比利時好多國家演出,現在不是好好的……”
徐學龍心想,改革開放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也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消費意識、審美欲望有了明顯的變化,促使了文化市場的形成和發育;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不同層次民眾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但是,文化市場在市場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問題——尤其是集鎮廟會、物交會中的色情演出時有發生,個別鄉鎮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農村文化市場管理相對薄弱,致使這一現象大有蔓延之勢。難怪老鄉們擔心讓孩子學藝學壞了,一直困守在黃土地上的鄉親們對藝校產生誤解也在情理之中啊。還是先找親戚的孩子學吧,他們會相信我的。於是,徐學龍告別了老鄉,徑直去尋訪一家家親戚們。
“表弟呀,孩子太小了……”表兄任荒說。
“咱這個行業特殊就特殊在演員必須連童子功,年齡大了練不出來。” 徐學龍耐心解釋。
“俺相信你,那孩子的文化課咋辦呢?”
“你放心吧,學校開有文化課。等到了省、市雜技團,人家那裡也開有文化課,達不到中專文化程度還不中哩。”
“那,俺可把孩子交給你啦!”語氣里充滿了擔心。
“你就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吧。”
功夫不負有心人。就這樣,徐學龍終於把6到14歲他大妹徐玉芝的兒子袁飛、二妹徐桂芝的女兒袁潔潔、三弟徐愛國的女兒徐田田、表弟任荒的兒子任天祥、妻侄趙雙劍、妻妹趙玉芬的女兒陳盼盼、叔伯弟弟徐大林的兒子徐勇威、鄰居孫抗美的兒子孫光輝等18個孩子一個個帶到了學校。
2000年8月16日上午,新蔡縣新星雜技藝術學校就這樣悄悄開學了。沒有鮮花、沒有禮炮,更沒有領導剪彩,只有心血加汗水和8位像徐學龍一樣年輕、執著、富有激情與抱負、不甘平庸的教練、勤雜人員。全校26名第一批徒弟,帶著懷疑與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租來的破舊排練大廳。沉寂五個多月的新星雜技藝術學校頓時充滿了生機。
徐學龍深知,隨著時代的發展,對雜技的審美要求越來越高,他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嚴格把好入學第一關。
開學第一天,學龍和教練們對剛入學的徒弟們又一次進行了檢查。看五官,量身材比例是否勻稱,骨骼和關節是否合理;讓徒弟將手臂伸展開,雙腳直立,看肘關節是否平直,是否有羅圈腿或者扁平足;為了考查徒弟的力量和靈活度,又讓他們做一些倒立、翻跟頭動作。通過檢查,篩選掉幾個不適合學雜技的孩子,學龍又親自將他們送了回家。
中國雜技特別重視腰腿頂功的訓練。雜技藝人,即使是表演古彩戲法的演員也都要有紮實的武功基礎。因此,徐學龍將基功作為重點訓練科目。
“│一0│一0│一二│一0│……”離藝校不遠的體育廣場,徐學龍的徒弟們每天必練的半個小時的跑步出操聲,每天五點半準時劃破清晨的寧靜。6歲的趙傑剛跑了3圈,累得臉色發白、上氣不接下氣,一頭摔到在跑道邊。這下可嚇壞了帶隊的教練徐愛國,他一邊呼喚“傑傑”,一邊掐仁中。一會兒,趙傑才醒了過來。
“傑傑,你可把俺嚇壞了,你先休息、休息。”
“不礙事,俺中。”
“不行,不行,你先走幾圈再說。”
“中、中。”
6點整,徐學龍的徒弟們回到排練廳,教練們分組帶徒弟們練習壓腿、劈叉、下腰和3-5-10分鐘的雙把頂和單把頂等技巧。一天要練500多分鐘的基功和上1個小時的文化課,可見學練強度之大。藝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台上三分鐘,台下三年功”這句藝術諺語,確實道出了學藝的艱辛。當你看到這些小徒弟們練功時嗤牙咧嘴、小臉憋得通紅、眼珠憋得幾乎要掉下時,你是否忍心讓自己的孩子學習雜技嗎?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艱苦、單調、枯燥、乏味的基本功訓練,沒有堅定的信念,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要想堅持下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徒弟們啊,你們都是好樣的。
半年後,徐學龍的徒弟們便開始練習前橋、弧跳、前空翻、後空翻和小翻等筋斗。練筋斗中,摔傷、扭腳、擦破皮都是常有的事,徒弟們早已習以為常,不以為是了。因為他們已深深愛上了雜技藝術,心中的理想是早日邁入聖神的藝術殿堂。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到了2002年的陽春三月。
一天,徐學龍正在排練大廳輔導他的徒弟們,突然,他的手機驟響。手機里清晰地傳來了在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當演員的兒子徐朝峰那熟悉的聲音:“爸,告訴你一個好訊息,我的一個朋友在中國雜技團……”
“慢點說,慢點說,別急……”
“他們團現在急需一個教練和幾個小演員,我已向他們推薦了我四叔和你教的徒弟們。”
“好好,他們啥時來學校挑選演員?”
“大概8月上旬吧。”
“好的,到時再聯繫。你和妹妹要聽領導話,刻苦練功啊!”
“知道咧,昨天團長還在表揚我哩。”
“要謙虛……,就這吧。”
儘管辦藝校僅僅一年零八個月,但是,徐學龍心裡清楚,他的幾個親屬的孩子已可以放飛了。
8月6日下午,中國雜技團、演員出身的常務副團長孫力力,風塵僕僕從北京趕到新蔡。當她走進新星雜技藝術學校排練大廳時,看見徐學龍的徒弟們緊張而有序的練功時,才打消了一路上的疑慮。
“你就是徐朝峰、徐娟娟的爸爸?”性格直爽的孫副團長握著徐學龍的手說。
“是是,我就是。你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你一雙兒女表演的《頂碗》,可為你爭了光啊。”
“那是團領導的栽培。”
……
早已等候在排練大廳的徒弟們,聽了徐學龍的一聲令下,迅速緊張有序的表演起基功來……
慧眼識珠的孫團長,一下子就瞄準了袁飛、袁潔潔、徐田田、任天祥這四個徒弟。原來他們從小就隨父母、親戚練過基功,比起其他徒弟的功底顯得紮實、嫻熟。
“這幾個徒弟,是誰負責訓練的?”孫團長問徐學龍。
“是我和四弟徐濤。”
“明天讓他帶著這四個徒弟和我一塊到北京,我們錄用了。”
這時,大廳里突然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從不喜形於色的徐學龍眼睛潮濕了,心裡涌動著辦藝校以來的酸甜苦辣,不斷地喃喃道:“累死也值了!值了!”
送走了這四個徒弟,不啻是給大家打了一針興奮劑,剩下的二十多個徒弟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美好燦爛的前程正在向他們招手。他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跑步、跳繩、扛槓鈴、壓沙包……常常練得四肢發麻仍咬牙堅持……
2003年盛夏的一天,徐學龍興致勃勃地打通了福建省雜技團黃國慶團長的手機,迫不及待地匯報了徒弟們的練功情況,以兌現“一句戲言”的承諾。學龍根本沒想到,這時的黃團長早被免職,已無權表態招收學員。這一訊息,如同五雷轟頂,打的徐學龍六神無主,差一點亂了方寸。冷靜片刻,他突然想起了黑龍江省雜技團演出公司副總經理朱峰老同事,便立即撥通了他的手機,把與黃團長的通話情況急切地告訴了對方。
“徐老兄,你別急,現在全國雜技團都存在後繼乏人的問題,到處都急需雜技人才,你等我的好訊息吧。”
“老弟,拜託了!”
7月16日,朱峰帶著黑龍江省雜技團的陳岩老師,到新星雜技藝術學校考察。徐學龍的徒弟們,看見省團的老師前來挑選學員,個個生龍活虎、身手不凡,將自己兩年多來刻苦練習的技藝充分展示了出來。
黑龍江省雜技團的陳岩老師說:“沒想到,你們在如此簡陋的學校,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訓練出有如此紮實基功的學員來,真是不簡單哪!”
“過講、過講了,主要是我的徒弟們都非常能吃苦,是他們勤奮苦練的結果,是教練們精心培訓的結果。”
通過精心挑選,黑龍江省雜技團正式錄取了徐高森、趙雙劍、孫光輝、趙傑、徐勇威、陳盼盼、田大志等12名學員。筆者於2006年6月2日採訪時得知,他們從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演出了120場,剛回到哈爾濱市。據說,由陳盼盼、田大志表演的《蹬技》,徐高森、趙雙劍、孫光輝、趙傑、徐勇威表演的《頂技》,正準備參加十月份全國“新苗杯”雜技大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一定會斬關奪隘、脫穎而出,為黑龍江省雜技團爭光,為他們的啟蒙老師徐學龍爭光。
現在的徐學龍真可謂:桃李滿天下。
2004年7月,輸送到上海市徐匯區雜技團的有周大利、孔藝峰、徐堡壘等7個徒弟,目前正在韓國演出。
2005年3月,輸送到雲南省雜技團的有孫冬紅、苗巧巧、張思雨、焦開開、趙東雲等11個徒弟,並聘請該校袁建軍、徐玉芝前去當教練。
2005年8月,輸送到河北省雜技團的有趙樹林、張俊禮2個徒弟;在省團訓練三個月後,正式上台演出《高椅》;筆者於2006年6月10日上午在藝校補充採訪時,徐學龍的徒弟趙樹林正巧打來越洋電話,告訴徐教練他正在美國,這次演出100天。
2005年9月,輸送到浙江省雜技團的有孔峰、徐磊2個徒弟。
2006年3月,輸送到上海雜技團的有薛欣欣、汪新茹、魏惠麗等7個徒弟。
……
新中國建立第八個年頭的仲秋,新蔡縣澗頭公社魏營大隊徐新莊小隊的木匠徐道榮、徐田氏家裡,又誕生了一個小生命。妻子對徐木匠說:“道榮啊,老大叫學文,老二就叫學龍吧?”
“那是為啥啊?”
“龍好啊?龍能辦大事!”
“他能辦啥大事?還是跟我學木匠活吧,咱家祖傳的木業技術不能讓它失傳了!”
“學龍、學龍,你聽見了吧,你爹讓你長大當木匠嘍——”妻子抱著懷裡的兒子,點著他的鼻子逗他玩。
星移斗轉,光陰似箭。靠吃紅薯長大的徐學龍19歲那年,從野里(公社)高中畢業回到家裡,徐木匠對兒子說:“學龍啊,高考也廢除了,咱上面也沒人,誰推薦你去上工農兵大學啊?那是人家有權勢的孩子上的學。你就死了心吧,跟我好好學一門手藝,比啥都強!”
“爹,我總不能幹一輩子木工活吧?”
“先學會再講,藝多不壓身。”
在父親的強硬堅持下,學龍只好學起木匠活來。心靈手巧的徐學龍很快就掌握了劈、鋸、刨、鑿和設計畫線等木工技術。“75.8”洪水下去後,徐學龍帶著兩個徒弟就外出做家具去了。
1976年的陽春三月,焦作藝人侯德山帶著雜技隊來到澗頭公社魏營大隊演出。愛好文藝的大哥徐學文結識了侯德山,在學龍家一住就是兩個月。大哥讓6歲的桂芝、9歲的玉芝兩個妹妹跟侯德山學習雜技。
三年後,侯德山帶著雜技團和四匹大馬從內蒙回到魏營大隊。這時的妹妹桂芝已能演馬術、頂碗和咬花,玉芝能演蹬技和腳踏車。侯德山打算將雜技團改成馬戲團,就讓徐學龍跟團做道具,這一跟就是三年。從此,徐學龍跟雜技、馬戲接下了不解之緣。
每天耳濡目染雜技、馬戲、魔術的徐學龍,看見演員們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和觀眾的熱烈掌聲,心裡總有一種躍躍欲試的衝動。在宿縣演出時,徐學龍觀看了宿縣雜技團演出的雜技《頂桿》,越看越覺得自己也能演好這個節目,就壯著膽子找到侯德山。
“侯老師……我,我……”
“學龍,今個是咋啦?說話咋吞吞吐吐的?”
“我也想學雜技、魔術……我看《頂桿》怪有意思……”
“那咋不中哎,明個你就和李廣文一起練《頂桿》,咋樣?”
“中、中。”
“台上三分鐘,台下三年功。要練就得下功夫啊!”
“中、中。”
徐學龍認準的事兒,就一定會做到底。三個月練習下來,他腦門上磨出了一層厚厚的老繭。他表演的《頂桿》,侯老師點頭認可後,就正式上台演出了。有生以來第一次上舞台表演,他緊張得出了一身冷汗。當觀眾對他的精彩表演報以熱烈的掌聲時,他似乎才回到現實中來。比徐學龍早練《頂桿》半年的李廣文,卻因節目難度太大而半途而廢。
一次在沁陽縣演出,侯老師因害眼疾不能上場,觀眾十分喜愛的魔術眼看要被取消。善動腦筋的徐學龍,平時做魔術道具時,早就把“門子”研究透了,心裡有底的他,深知“救場如救火”,就對侯老師說:“讓我試試吧?”
“有把握嗎?”
“還可以吧。”
就這樣,徐學龍表演的魔術《釣魚》、《換人》、《林鳥歸籠》等節目一舉成功,受到觀眾和全團人員的一致好評。
1980年2月,當時社會還受“極左路線”的影響,乾什麼都受到限制,特別是外出,更是控制的嚴格。侯德山只好到思想觀念比較解放的安徽省臨泉縣開出了演出介紹信,帶領掛牌臨泉馬戲團60多名演職員工,從河南一路演到甘肅的酒泉,為了節約開支和便於運馬,他們搭乘悶罐子火車千里迢迢趕到新疆。在北疆巡迴演出後,趕到石河子演馬戲。一下了車,全團演職員工迅速將棚圈搭建好,就緊鑼密鼓的開了場。當徐學龍表演《頂桿》時,突然,狂風大作,暴雨傾瀉。6米長的桿子“唰”的一下,從學龍的腦門上滑降下來,把學龍兩寸長的頭皮撕了下來,頓時血流如注,封住了雙眼,徐學龍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觀眾一片譁然。演員們七手八腳把他抬到附近醫院搶救,頭皮上縫了8針,休養了兩個月傷口才得以癒合。
第二年,徐學龍隨團從新疆回到家鄉,就與李廣文在安徽蚌埠和河南滑縣兩度成立馬戲團。七年間,他帶團演出從黃山腳下的蚌埠到綠城鄭州,從孔廟曲阜到飛彈發射基地酒泉,從萍鄉的安源煤礦到瓷都景德鎮,從苗族自治區到洞庭湖畔的岳陽樓,從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祖國的南疆……,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
歷經演出市場摔打的徐學龍成熟了。1988年他從開封市雜技團學會了全新的演出運作方式——“跑票”,成為名符其實的“文藝經紀人”。1989年6月,他被駐馬店市雜技團招錄為國家正式演員,兼任該團“外交”,負責聯繫業務。
一天,長年奔波在外地的徐學龍趁假期回到老家。妻子趙素花埋怨道:“你整天就知道跟你的雜技過日子,爹娘都六十多歲的人了,你也不管;我白天要忙農活,夜晚又要照顧老人和孩子,你想累死我啊。乾脆讓朝峰和娟娟兩孩子跟著你吧?”“哎——,你倒提醒了我,乾脆讓兩孩子跟我到雜技團學藝去。”就這樣,徐學龍將孩子帶到駐馬店市雜技團跟團學藝。
這年,國小三年級的朝峰剛剛10歲,還未上學的娟娟7歲,這一對小兄妹從此走上了雜技之路。兄妹倆似乎天生就是吃雜技這碗飯的。別的孩子練雙手頂5分鐘就下來了,他們兄妹倆每次都達到10分鐘以上。兩年後,勤學苦練的這對小兄妹開始搭擋練習《頂碗》這個高難度雜技節目。在父親和小姑徐桂芝的精心指導下,不到半年,兄妹倆就成功的上演了這個節目。
徐學龍在駐馬店市雜技團僅6年中,就先後為該團聯繫辦理了赴日本、美國、加拿大、泰國、加彭、塞內加爾、法國、幾內亞、馬里、比利時、衣索比亞等國家進行友好訪問演出和商業演出的出國護照。1992年4月——8月,徐學龍和一雙兒女隨團在美國奧蘭多市的迪斯尼演出,132天共演出了527場,每天場場爆滿,掌聲不絕於耳。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達20萬人次,美國觀眾稱駐馬店市雜技團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雜技團!”
1996年的初春,金色的陽光,沐浴著北京飛機場。
駐馬店市雜技團的演員們已登上飛往法國巴黎的座機,飛機準時順著跑道緩緩向前行駛,準備起飛。
晴空萬里,艷陽高照,與雜技團演員們喜悅的心境是那么的吻合。這天,是徐學龍終身難忘的一天。作為一團之長的他,與對方國演出公司簽訂了每場演出付團方2000美金及相關事宜的契約後,他親自率領全團演職員工到法國、比利時進行為期3個月的商業演出,心情是何等驕傲和自豪啊。
在巴黎大劇院演出結束後,法國文化經紀人科羅德帶著翻譯,將徐學龍拉到一邊。
“徐團長,聽說今晚演出《頂碗》的演員是你的兒女?”
“是的,是的。怎么了?”徐學龍很詫異,以為出了什麼問題。
“演的太棒了!” 科羅德翹起大拇指說。
“謝謝你的誇獎。”
“我,有個想法,想讓你的兒子、女兒留在法國,我全權負責他倆的生活和學習……” 科羅德習慣的聳著肩頭。
徐學龍急切地問翻譯:“他說什麼呢?”翻譯熟練地說出了科羅德講的意思。
“謝謝你的挽留,不過……”徐學龍心裡沒底。
“他們留下後,我每年給你買好飛機票,來法國看望你的兒女,怎樣?” 科羅德緊追不捨。
“他們不會離開中國的,再說我也捨不得呀!”徐學龍堅定地說。
“那……,我就真的沒辦法了,很遺憾、很遺憾……拜拜。”
三個月的跨國演出,很快就結束了。在國內演出不景氣的情況下,一個市級藝術表演團體,三個月創收近150萬元,在駐馬店九縣一市中,確實是一個奇蹟,一個新版本的“天方夜譚”。
1996年初夏的一天,從駐馬店火車站下車的三位氣宇軒昂、富有藝術氣質的軍人,帶著中央軍委的《特招令》徑直來到市雜技團。原來是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表演《頂碗》的演員腰部有疾,急需物色演員頂替。林副團長、高副團長、王編導慕名找到徐學龍,寒暄後就要求看演員、看節目。一臉嚴肅的團副、編導們,看了徐朝峰、徐娟娟表演的《頂碗》,終於露出了笑臉,拉著徐學龍的手說:“徐團長,感謝你培養了這么出色的好演員啊!這對小兄妹,我們特招了,晚上就跟我們南下吧。”
“謝謝你們的厚愛!”徐學龍激動的嗓子一硬,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朝峰、娟娟,你倆願意去部隊嗎?”林副團長和藹地問道。
“當然願意去啦!”已14歲的娟娟高興的拍著小手和18歲的哥哥朝峰搶著回答。
吃過晚餐,徐學龍在送兒女去火車站的路上,一向不愛多說話的他,這一會兒是千叮嚀、萬囑咐,讓他們一定不要辜負部隊首長的期望,拚出成績再給家裡打電話。南下的列車徐徐開動了,學龍揮手向他們告別,不知是高興,還是離別時的惆悵,不知不覺兩行熱淚滾滾而下……
果然,好長一段時間徐學龍沒有接到兒、女的電話,心裡時常牽掛。後來,朝峰、娟絹報捷的電話頻頻打來:
“爸,俺和哥哥的表演的《頂碗》,在第七屆全軍文藝會演中,得了二等獎哩。”這是女兒娟娟撒嬌的聲音。
“爸,你看電視了嗎?朱鎔基總理訪問丹麥,俺也去了,在首都哥本哈根演出,非常成功!別忘了告訴俺媽——”兒子自豪地說。
“爸、媽,俺已給你們寄去了幾張照片。你猜猜在哪拍的照?……不知道吧。俺對你說,俺在摩洛哥演出,王子、王妃上舞台接見時拍的合影照片。”
——1998年6月12日,徐朝峰、徐娟絹在中央電視台的《曲苑雜壇》欄目中表演《頂碗》,受到觀眾的交口稱讚。
——2002年10月22日,徐朝峰、徐娟絹代表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表演的《現代男女軟功》、《青春的鏇律·滾杯》在“金獅獎”第五屆全國雜技比賽中,分別榮獲金獅獎。
……
中國雜技家協會主席夏菊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5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一代又一代雜技藝術工作者的頑強拼搏和不懈努力下,創作出了一批批具有獨特民族風格、強烈時代氣息和豐富文化內涵的作品。在國際各大雜技賽場上獲得120多塊金牌;在對外演出中占我國文藝演出創匯之首。跟隨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被譽為‘外交先行官’。尤其是這支隊伍長期活躍在城鄉、邊防哨所,極大地豐富了人民民眾和基層部隊的文化生活,積極弘揚著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
在這些巨大成就中,你不認為也有徐學龍和他的徒弟們付出的幾多心血和幾多汗水嗎?他們追求的階段性目標雖然不同,然而,他們鍥而不捨追求的,是共和國輝煌燦爛的明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