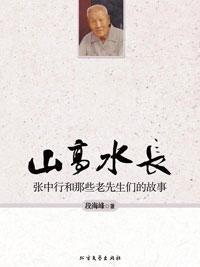內容簡介
《山高水長(張中行和那些老先生們的故事)》分三部分;上下兩輯和美食系列談。其中,上輯主要講述了作者與文藝界那些著名老先生們的故事,如張中行、季羨林、臧克家、汪曾祺、劉心武、吳冠中等;下輯收錄的是作者對生活的認知和體會文;美食系列談,顧名思義講述的是作者與美食間的故事。
內容試讀
第一章憶張中行先生(1)
憶張中行先生
曹君亞瑟打來電話,第一句話就是:“你要節哀!”果然他通報的,是一個我不願意聽到的壞訊息:張中行先生過世了!雖然張先生以九十有七的高齡辭世,我心裡還是有所準備,但得知這樣一位有高名的老人真的走了,我還是唏噓不已。
由於跟張老接觸較多,沉痛之餘,就想寫點什麼。懷念之文,我們讀過不少,我不想把這位我敬仰的大學者寫得過於悲苦,於是不避淺薄,把自己熟知的張老逸聞採擷數章。依京劇慣例,重頭人物出面,必有馬童先上場,翻幾個跟頭,舞兩下槍棒,然後翹指說:“我家老爺……”寫到張中行先生這位讀書界、文史界的重頭人物,我也不妨效馬童之職,先向讀者作一介紹。
張中行先生原名睿,後因字罕用,遂改今名。他1909年生於河北香河縣一農家。由於學業方面興趣廣泛,因而被人推為雜家。他早期的著述,多偏於語文方面,出版有《文言文選讀》、《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等,但真正顯示出張老學識和襟懷的,則是他80歲以後出版的《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禪外說禪》、《詩詞讀寫叢話》、《順生論》等著作。這些著作的出版,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書店自不必說,幾乎全可在地攤上買到!尤其在北京,一些書攤主只要聽說張中行新作出版,馬上進貨,一來他們把能夠出售張中行著作當作提高書攤檔次的手段,二來這類書也確實好銷。一個個體書店的門前,甚至有一個招牌,上寫“本店經銷張中行先生所有著作”之類的宣傳。進得店來,還真不假,差不多最新的張中行著作,他這裡都有。不消說,這位老闆也是“張迷”。一般人如此,名家們亦不例外,王蒙、劉心武、林斤瀾等人,也對張中行表示極大的敬重。
張中行的著作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這要看他的書。以我的孤陋寡聞,怎能窺得其堂奧?不能,也不敢去評價行翁,偷懶,抄《負暄三話》上的介紹:“用意是記可傳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說是當做詩和史寫的,因而筆下總是輕鬆中含有嚴肅,幽默中含有淚水。出版以後,國內外報刊發表多篇評論文章,以為作者有卓識和深情,以沖淡自然之筆寫今世之《世說新語》。”讀書界公認,行翁以悲天憫人之懷,惜古憐今之趣,談古論今,其書格之奇,文筆之高,為近年所罕見,因而形成一股“張中行現象”,讀書人以有沒有讀過張中行著作劃分讀書檔次,以有沒有張中行法書、手澤為炫耀資本。
寫作如此,生活中的張中行先生,也有一顆悲天憫人濟世心。仍是用舉輕若重之法,舉兩件行翁的逸聞。先舉聽說的,行翁所在的出版社,有一位同事丟了1000元錢,很沮喪,眾人好心來勸,效果不佳,丟錢人心情還是不好。行翁聞知,拿出500元去,說:“只當是你丟500元,我丟500元,一個人的不快讓兩個人分擔,不是可以減輕一點嗎?”還有眼見的。前幾年我與出版社李女士去北京組稿,順便將行翁的稿酬3000多元送去。在行翁的辦公室,行翁微笑著遞過一箋空白信紙,囑我寫封信,信中要寫上這筆稿酬有1000元是徐秀姍女士的。原來,由我掛名“主編”,李女士做責任編輯的行翁著作《觀照集》,由徐秀姍女士幫行翁剪貼、排序、複印,還寫了後記,行翁說,按說該把稿酬分她一半才對,但出版社無證明,明給,這個數目恐徐不受,所以請你這位主編寫封信,言明這1000元是徐秀姍的稿酬,白紙黑字,不怕她不信!我遵命,就伏在行翁桌上把信寫好,交行翁看,行翁甚為滿意。
後來行翁來河南作鄭汴洛之游,我與李女士有幸伴以左右,問及假信一事,行翁得意:“徐秀姍果然中計,我把你的信拿給她,她起初還不相信,我說:人家主編的信你也懷疑嗎?她終於還是接了。”
我與行翁交往有數十年,耳聞目睹,受益非淺。據我親見,對於慕名求字者,行翁總是替人家打算:既然來求字,總是捧場的,自己雖然寫得不好,可怎么能拂人家這個面子呢?於是寫。寫完之後,蓋一方“學書不成”的印章,算是自我寬慰。可是這扇門一開,蜂擁而來的文債,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以至於正常的寫作時間也不再能保證。
我們去拜訪他,如果是談話超過午時,他總是提出請吃飯。這樣由他做東,我吃過他多次飯。每次都吃得盡興,酒是行翁自帶,喝得更是恰到好處。他提倡節儉,飯菜總是能夠恰好吃完,而客人也感到酒足飯飽,有時我會想到古典,“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和張中行先生一起吃飯,可以有雙重享受,物質的是肚子吃得舒服,精神的是可以聆聽他的高論。
有一天我去一家書店,熟識的老闆叫道:“張中行還寫了你了!”說著拿出一本張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我一看,還真是有兩處提到賤名。
我最初模仿張中行先生的文風,竟然有些心得。直到後來中國作家協會吸收我為會員時,曾聽說,有評審贊我年輕卻文筆老辣,於是我得以混進中國作協。其實我知道,這是學習張先生風格的結果。
和張中行先生的第一面
有一天,唐明君找到我,遞上一本書:“奇書!”接過一看,是署名張中行著的《負暄瑣話》,書印得不算精美,定價也不高,不像是奇書的樣子。唐君說:“別看外表,看內容。”
第一章憶張中行先生(2)
這書我留下讀了一晚,立即被作者老到的文筆,自如的行文,張弛有度的寫作方式,以及淵博的知識,和名人交往的諸多趣事而吸住了。雖然篇幅不長,卻趣味叢生,寫人寫事,又飽含深情。字裡行間,流露著作者對人生,對社會的悲憫之情。可以說,多年沒有讀過這么痛快的書了!
但是,我還沒有想到過能和作者聯繫上。
事有湊巧,不久以後,編輯部安排我隨總編輯去北京出差,任務是約稿。我和總編輯跑東跑西,到多家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約請一些名人或作者寫稿。在《讀書》雜誌社的地下室里,我們見到《讀書》的吳姓、趙姓兩位女編輯,在和她們聊稿子的過程中,她們提到了張中行的名字。
我在旁邊聽了,心中猛然一喜:“張中行?是那本《負暄瑣話》的作者嗎?”
“誰說不是呢?老先生現在在北京可有名了,是出版界深挖出來的寶貝呢!”趙編輯說。
“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去拜訪,我讀過他的書。”我急切地說。
兩位女編輯答應幫忙,於是一人拿起電話聯繫,我在旁邊聽著,心頭很是感動。都說北京人有優越感,不熱心,看來不是吧。
下午,我和總編輯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這裡,見到了我仰慕的張中行先生。張先生此時正在辦公桌前坐著,見我們來,熱情讓座,第一句話就說:“是《讀書》編輯介紹來的吧,剛才她們已經打過電話了。”
張先生此時已經是八十歲了吧,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精神矍爍,和藹可敬,眼睛相當小,卻很有神。個子總有1.75米吧,加上他瘦,所以顯得更高。坐下彼此相互介紹,張先生很自然地說起自己正在寫作《順生論》,此書還沒有出版,我當然也不會看到,所以只有聽。但是一旦張先生停下來,我卻能插話提問:“張老,您在《負暄瑣話》里,有一段意思我不明白。”這就是優勢,因為細看了《負暄瑣話》,所以提問就比較有的放矢,張先生當然樂意介紹和解釋。
不過,他的解釋在我聽來,卻顯得高深。這不怪張先生,而是怪自己古文功底不夠,因為其中許多是用典,而我卻不能理解,不由得在心裡暗說聲“慚愧”。
隨後我們提出約稿,是我們的雜誌上有一個欄目,叫“名人的遺憾”,希望張先生寫一寫自己的遺憾。
張先生的第一反應,是否認自己是個名人。但是架不住我們勸說,只好答應下來,說:“名人不名人的糊塗帳,只好不論。”
我拿出事先買好的張先生的新著《禪外說禪》,請他題個字,張先生很樂意。他拿出便捷式的小的毛筆,工工整整寫下:“一九九一年段海峰先生枉駕,不棄拙作,囑署名,張中行。”然後是蓋章,他翻檢印章盒子時,同辦公室的人提議:“用負翁嘛。”張先生答應,選出這方印章,蓋在題款下面。
隨後我們提出是否能合個影,留個紀念。張先生當然也答應,拿上他的“博士”帽,拉上同辦公室的人,跟我們走到室外。後來我知道,這帽子,就是《讀書》雜誌的女編輯給用毛線勾的。
我們一一跟張先生合影,然後辭別出來。總編輯提議:“見到這樣的名家,真是應該慶賀一下,走,吃爆肚,喝二鍋頭去。”
和張中行先生的書信往來
現在已經是一個不寫信的時代了。
我做編輯數十年,對於信件往返,早已習以為常。每天,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檢各地來信。一旦看到老友熟悉的筆跡,內心總是充滿了喜悅,而對於那些陌生的信件,也同樣充滿期待,因為你不知道將會有什麼故事。
孔子說他“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我也久矣不復收到來信。對著電腦,電子信箱也空空的時候,就念起和張中行先生的書信往還。
查查張老來信的數量,有三十來封,我時常有一句話可誇口,那就是起碼在我們單位,我保持著與張老最多的書信往來的紀錄。
數量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微雨天氣,看著窗外的風景,翻檢出這位世紀老人的信札,隨便打開幾封來讀,那也是多么有情調的事啊。最有意思的是,當我翻看一些名人的著作時,比如周作人,辜鴻銘,啟功,經常會無意中跟張中行先生聯繫起來,因為這些名人跟他都有多多少少的聯繫。這時再看張中行先生的來信,讀著他那些文白相間、措詞工整的來信,於心情上,就更多了一份親切。
張先生的來信,字型工工整整,頁面整潔,一般以一頁為限,抬頭是稱呼,接著是正文,及至落款,不多不少,正好滿一頁。所以這信,常常成為我學習的模範格式。
收到張先生第一封信時,最為激動。因為他是名人,我只是抱著試試的想法,給他寫了第一封信。至於能否回信,我不敢想。那時有個最基本想法,反正是單位出郵資,我寄信又不花錢,張先生若能回信最好,回不了,我權當練習寫信了。這想法雖然低俗,但卻極為真實。
然而張先生真的回信了,是在冬天。我在此之前,經人介紹,和我們的總編輯一起,去北京他的辦公室,拜訪過他一次。跟所有初次見面的開頭一樣,他先是問我們如何找到他的,同時說,剛才有《讀書》雜誌的編輯給他打過電話,說有兩位河南的編輯將要來訪。我們明白,這是我們事先做的功課起作用了。
當然,更重要的功課,是我們事先都細讀過他的不少文章。說不少,一點也不誇張,那就是我極其認真地讀完了他的《負暄瑣話》,熟知其中的部分內容,並且是帶著幾個問題去看望他的,那么這樣的見面,就很容易進入狀態。我們見過一些來訪者,先是對你表示敬意,然後說早已拜讀過大作,但是一聊起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為他並不了解你,那這樣的談話,就顯得難以深入。現在不同,我們單方面對他熟悉了,所以提出的話題,就很容易讓張先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