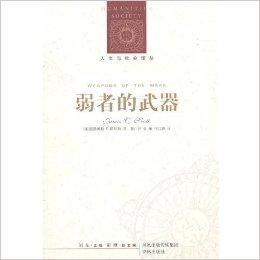作者介紹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畫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係等。主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階級戰爭中的短兵相接
拉扎克
哈吉·“布魯姆”
權力的象徵性平衡
第二章常規的剝削,常規的反抗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作為思想和象徵的反抗
人類行動者的經驗與意識
第三章反抗的景觀
背景:馬來西亞和水稻主產區
中層背景:吉打州和穆達地區的灌溉系統
第四章塞達卡:從1967年到1979年
富與窮
村莊構成
土地占有與使用
租佃的變化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地方機構和經濟權力
第五章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分類
夜行船
綠色革命的階級史
雙耕與雙重看法
從活租到死租
聯合收割機
失去的地盤:土地的獲得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記憶中的村莊
第六章延展事實:意識形態的運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識形態運作
剝削的辭彙表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合理化的剝削
意識形態衝突:村莊大門
意識形態衝突:村莊改進計畫
作為反抗的爭論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戰:謹慎反抗與適度遵從
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障礙
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常規的”反抗
“常規的”鎮壓
常規的順從與不留痕跡的反抗
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謂反抗?
第八章霸權與意識
意識形態鬥爭的日常形式
塞達卡的物質基礎和規範性上層建築
重新思考霸權概念
附 錄
附錄A村莊人口記錄,1967—1979
附錄B不同土地使用類型/農場規模的農場收入比較
(穆達地區,1966、1974和1979年)
附錄C關於土地使用情況變更、淨利潤及政治事務的數據
附錄D飛翔信的譯文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圖書內容
前言
任何研究領域的局限性在與其相關研究的共有定義中最能突顯出來。大量的關於農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關注反抗與革命的問題。平心而論,除了關於親屬關係、儀式、耕作和語言方面一貫的標準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關注集中於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儘管只是曇花一現,卻顯然對國家造成了威脅。我可以想到對此類運動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於一系列相互強化的因素。對左派而言,對農民起義的過度關注顯然受到越戰和現在已經開始消退的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絕對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歷史記錄和檔案鼓勵了這種迷戀,它們從不提及農民,除非農民的行動對國家構成威脅。另一方面,農民只是作為徵召、糧食生產、稅收等方面的匿名“貢獻者”出現在統計數字中。這種視角下的每項研究強調了不同的側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強調外來者——預言家、激進知識分子、政黨——在動員通常懶散、無組織的農民的過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關注的只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最為熟悉那些運動——那些擁有名稱、旗幟、組織機構和正式領導階層的運動。還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確考察那些可能在國家層面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方面有所貢獻。
我認為,這種視角所忽視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貫穿於大部分歷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於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即使當選擇存在時,同一目標能否用不同的策略來實現也是不清楚的。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改變宏大的國家結構和法律缺乏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霍布斯鮑姆所稱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並非偶然,這也是走向結論的第一步:農民階級在政治上是無效的,除非他們被外來者組織和領導。
就其真正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是相當稀少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功——我並不想否認這些成果——通常都會導致一個更大的更具強制力的國家機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養肥自己。
鑒於上述原因,對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稱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鬥爭——農民與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鬥爭。此類鬥爭的大多數形式避免了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在此我能想到的這些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或帥克式——的階級鬥爭形式有其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畫,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與權威對抗。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或進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數努力。我猜想長期以來正是這類反抗最有意義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義的歷史學家布洛赫指出,相對於“農村社區頑強進行的堅韌的、沉默的鬥爭”而言,偉大的千年運動也只是“曇花一現”;這類鬥爭旨在避免對他們的生產剩餘的索要和維護他們對生產資料——如耕地、林場、牧場等的所有權。這一觀點肯定也適用於對新大陸奴隸制的研究。對奴隸與其主人關係的分析不能僅僅去尋找納特·特納或約翰·布朗式罕見的、英雄主義的、注定失敗的舉動,而必須著眼於圍繞工作、食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不斷的瑣碎的衝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他們寧願一點一點地擠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們選擇開小差而不是公開發動兵變,他們寧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搶公共的或私人的糧倉。而一旦農民不再使用這些策略而是採取堂吉訶德式的行動,這通常是大規模鋌而走險的信號。
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技術與農民的社會結構非常適合——農民階級分散在農村中,缺乏正式的組織,最適合於大範圍的游擊式的自衛性的消耗戰。他們的行動拖沓和逃跑等個體行動被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所強化,成千上萬地累積起來,最終會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所構想的政策完全無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動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農民以這種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參與感。打個比方說,當國家的航船擱淺於這些暗礁時,人們通常只注意船隻失事本身,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為可能。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動的顛復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這樣一個目標,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裡度過了兩年(1978—1980)時間。這個村莊被我稱為塞達卡,這並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產區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小村落(有70戶人家),該村在1972年開始引入雙耕。與其他許多“綠色革命”一樣,它使得富人更為富有,而窮人仍然貧窮甚至變得更窮。1976年大型聯合收割機的引進或許更是致命的一擊,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掙工資的機會。在這兩年當中,我設法收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鬥爭——它為反抗寫就了腳本。在本書中,我試圖討論反抗和階級鬥爭的重大主題,以及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態支配問題。
在塞達卡,貧富之間的鬥爭不僅是關於工作、財產權、糧食和金錢的鬥爭,它也是關於占有象徵符號的鬥爭,是有關過去和現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類的鬥爭,是確認理由、評價過失的鬥爭,也是賦予地方歷史黨派意義的鬥爭性努力。這一鬥爭的細節並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後誹謗、流言蜚語、人身攻擊、給人起綽號、肢體語言和無聲的蔑視等,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莊生活的“後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負載權力的情境中——經過精心算計的遵從是普遍和經常的狀態。階級衝突的這一方面的顯著特徵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共享的世界觀。例如,如果沒有關於什麼是越軌、什麼是可恥和無禮的共同標準,那么任何流言蜚語和人身攻擊就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爭論的強烈程度基於這樣的事實:人們所主張的共享價值觀遭到背離。人們爭論的不是價值觀本身,而是這些價值觀適用的事實:誰富、誰窮、何以致富、何以貧窮、誰吝嗇、誰逃避工作等。這些鬥爭除了可以視做動員社會輿論的約束性力量以外,還可視為這一小共同體中窮人為抗拒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和儀式上的邊緣化並堅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嚴而進行的努力。這種視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義為中心”的階級關係分析的價值。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將就更廣泛的意識形態支配和霸權問題進行說明和探討。
在塞達卡度過的14個月中,我有時興高采烈,有時萬分沮喪,有時手足無措,有時辛苦乏味,這些是每個人類學家都能夠體會到的。由於我並非正式的人類學家,因而所有這些經驗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如果沒有貝利給予我的實用的田野研究講座,我將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這些明智的建議的指引下,我仍然對人類學家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處於工作狀態的基本事實缺乏準備。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我去室外活動大半沒有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獨處。我發現需要保持一種審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緘默,這是明智的,但同時也是巨大的心理負擔。隨著我自己的“隱藏的文本”(參見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認識到瓊·杜韋格納德的評論的正確性:“在多數情況下,村莊會向外來研究者做出讓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於隱藏。”我同樣發現鄰居們總是原諒我難免犯的錯誤,在每一點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們對我的不適當行為並不在意,並允許我在他們身邊工作。他們有著既嘲笑我同時又與我友好相處的非凡能力,他們具備劃分界限的尊嚴和勇氣,他們善於社交,經常在非收穫季節就感興趣的話題與我徹夜長談。他們的友善表明,相對於我適應他們來說,他們更好地適應了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義是言辭的感謝不足以表達的。
儘管我努力刪減原稿,但它依然很長。主要原因在於許多特定故事的講述對於揭示階級關係的結構和實踐是絕對重要的。既然每個故事都至少有兩面,因而有必要考慮社會衝突所產生的“羅生門效應”的存在。努力講述這些故事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要將一種貼近底層的階級關係的研究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我認為這些更為巨觀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詳細實例來呈現本質。因而,一個實例不僅是將一般概括具體化的最成功途徑,而且它具有比歸納出的原則更為豐富和複雜的優勢。
在馬來語很難直譯的地方,或馬來語表達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將其加在正文或腳註里。除了對那些外來者所做的正式演講,我從不使用磁帶錄音機進行記錄。我的工作是依靠談話時片斷的筆記或事後馬上進行追記來完成的。由於許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記住的片斷可以憶起,結果使得我所記錄的馬來語有某種類似電報的性質。剛到時,我聽不懂吉打州農村的方言,相當多的村民用他們在市場上所用的更簡單的馬來語對我說話。
我覺得,本書的寫作還有一個特殊緣由。與其他鄉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對象的產物。在我開始研究時,我的想法是展開我的分析,將研究寫出來,並準備一個關於我的發現的簡短的口頭版本,然後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們對此的反應、意見和批評。這些反應將收集在最後一章——作為“村民的回應”的部分,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將其視為那些應該知曉本書內容的人所做的“書評”。事實上,在塞達卡的最後兩個月中,我的確花了更多的時間用於從大多數村民中收集這些意見。在各種各樣的評論中——這些評論通常反映了評論者的階級立場——充滿著一系列針對我所忽視問題的富於洞見的批評、修正和建議。所有這些在改變原有分析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是否應該將我較早的愚鈍的分析交給讀者而只在最後才呈現村民提出的見解呢?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當我動筆時,我發現把我現在已經知道的當做不知道來寫是不可能的,於是我逐步把這些洞見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結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種程度上塞達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並因此使得那些複雜的談話更像是一種獨白。
最後,我要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自覺的地方階級關係的研究。這意味著農民—國家關係顯然存在大量反抗,會明顯缺席,除非它們影響了地方的階級關係。這也意味著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機中都相當重要的族群衝突、宗教運動或抗議也基本上沒有被涉及。本書也不去分析這裡所考察的細微階級關係的經濟起源,這些源頭不難一直追溯到紐約和東京的董事會議上。這還意味著處於省或國家層面的正式的政黨政治也將被忽略。從一個角度看,所有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裡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階級關係是多么重要、多么豐富和複雜,還表明不以國家、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將給我們帶來的潛在發現。
下面這些過於冗長的謝辭意在表明為了進行研究我必須學習的許多東西,同時也表明那些教導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對於塞達卡的那些家庭——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們的名字被隱去——我所欠甚多,這筆債之所以沉重,原因在於我所寫的內容讓不只一個人感到他們的友好被濫用了。當然,對一個專業的外來者而言,那是一種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們將會發現我是以誠實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學識來公正地對待我的所見所聞的。
我的接待單位是位於檳榔嶼州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較社會科學院。作為客人或學者,我是非常幸運的。我要特別感謝學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長兼院長Kamal Salih和院長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謝他們的建議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為吉打州方言的特別輔導老師,幫助我為田野工作進行準備。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對吉打州的穆達工程和與之相關的農業政策進行了許多出色的研究。該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僅幫助我制訂研究計畫,而且還成為我彌足珍貴的朋友和批評者,他們的功勞在書中隨處可見——即使在我決定自行其是的時候。我還要感謝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當然還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於亞羅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部的官員們總是非常慷慨地貢獻他們的時間、他們的統計數據,尤其是他們的豐富經驗。任何發展項目中要找到這樣一些有知識、嚴格而坦率的官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時任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經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給予了很多幫助。
與我的研究路徑互有交叉、對馬來西亞鄉村社會進行研究並著述的“無形學院”的成員們,對於我的理解和分析貢獻良多。由於他們人數眾多,我無疑會有所遺漏。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寧願不被提及,而我還是必須提到這樣一些名字,他們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兩位來耶魯做畢業論文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的教師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給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議和批評。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東京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對塞達卡的土地所有制進行了研究並得出可以利用的結果,如此我才能確定十年間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最後的手稿在同事們細緻的批評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觀。我忍痛割愛,不再爭論那些他們認為荒謬或無關緊要——或兩者兼有——的論題,同時增加了他們認為必要的歷史性和分析性的內容。即使我拒絕他們的看法,我也總是儘量通過加強或改變我的立場來減少直接的攻擊。然而,到此為止吧。如果他們一直完全堅持他們的看法,我還願意繼續修改,並努力調整他們無意造成的混亂。我迫不及待地要回報他們的厚愛。感謝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對,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還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們同意甚至請求閱讀原稿,或許他們看過其中的一些篇章,卻給予了重新的思考。他們知道他們是誰。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來,許多機構的資助使得我和這項研究事業得以持續。我要特別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批准號SOC 7802756)和耶魯大學對我在馬來西亞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項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書的最終草稿和大多數修訂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對書稿傾注過多的精力,並且與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幫助我保持智識上的收穫。由日本大坂的國家民族學博物館主辦、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研討會,有助於使我的觀點更加明晰。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幫助組織的在海牙社會研究所舉行的另一個有著更多爭論的工作討論會,對本書第七章有關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儘管我不清楚這兩次會議的參與者是否完全認同我所提出的論點,但他們至少應該知道他們的著述和批評對本書具有何等重要的價值。
應當感謝的還有下列對本書早期的部分內容給予發表的出版物:《國際政治科學評論》(1973年10月);《東南亞的歷史與農民意識》(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編,“山崎民族學研究”第13期;大坂:國家民族學博物館,1984);《政治人類學》(1982);《馬來西亞研究》1:1(1983年6月,馬來文)。
本書的出版傾注了許多打字員、排版員和編輯的心血,他們高興地看到這一出自他們之手的書稿。其中我特別要感謝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書與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經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說的常規套話。在此我可以說,儘管我努力了,但從未能夠哪怕稍微讓路易絲和孩子們相信,他們也在為我寫作本書出力。
譯後
“弱者的武器”:研究農民政治的底層視角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是處於低下社會地位的小農(peasant)。他們雖然作為農業社會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卻從來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他們即使偶爾出現在歷史記錄中,也不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徵召、稅收、勞動、土地產出和穀物收穫的貢獻者,因而只是在統計學意義上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歷史中的消隱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受注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於,農民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盪,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各個社會的統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復舟”的道理。
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呼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於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於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人們會以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提請決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顯而易見,出於“危機”反應的對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防範對象和憐憫對象而存在的。
以農民的眼光來注視,以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已有的農民社會經典研究無疑不能忽視。詹姆斯·斯科特繼《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之後,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介紹其富於洞察力的研究,對於關注農村社會與農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並批評了許多關於農民革命的研究只對那些在國家層面造成大規模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感興趣。這類研究主要集中於有組織的、正式的、公開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顯然對國家造成威脅,即使只有短暫的片刻。但就發生而言,所謂農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當稀少的,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擊敗;即便是非常罕見地成功了,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區分了所謂“真正的”反抗與象徵的、偶然的甚至附帶性的反抗行動,並且不同意將非正式反抗視為無足輕重和毫無結果的。不難理解,在歷史中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若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農民也因而被認為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除非他們被外來者加以組織和領導。
斯科特以自己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工作材料為證據,指出上述視角所遺漏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多數從屬階級來說是過於奢侈了,因為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有鑒於此,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農民與從他們那裡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常的卻是持續不斷的爭鬥。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畫,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對抗權威。
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於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對抗統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展政策或煩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
這類反抗的技術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因為它們適合於農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特點:一個散布在廣大鄉村的階級,缺少正式的組織和紀律,為了廣泛的游擊式的防禦性鬥爭而裝備起來。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不需證明、沒有期限、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然而農民這些卑微的反抗行動不可小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復。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為的顛復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認為,無論國家會以什麼方式做出反應,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縮小了國家對政策選擇的範圍。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壓力以外,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感。因而,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農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後,斯科特又推出了“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性概念。通過這一概念斯科特進一步闡述底層群體的意識形態特徵,並以此解釋和理解底層群體的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這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是千百萬人日常的民間智慧的重要部分,它們與“公開的文本”的比較為理解支配與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和象徵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的反抗實踐與反抗話語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維繫。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繫意味著不可能將從屬的觀念和象徵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將對統治觀念的隱藏的象徵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鬥爭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計謀(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關鍵在於,隱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行為,它還有助於建構行為。
農民反抗與底層政治的特殊邏輯 “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使得底層政治的偽裝邏輯擴展至它的組織和實質性方面。因為公開的政治活動代價過高,幾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託於非正式的親屬網路、鄰里、朋友和社區而非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市場、鄰居、家庭和社區的集合既為反抗提供了結構,也為其提供了掩護。由於反抗是在小群體和個體層面進行的,即使規模稍大也會使用民間文化的匿名性或種種實際的偽裝,因而適合於對付監視和鎮壓。在這種非正式反抗中,沒有可供逮捕的領導人,沒有可被調查的成員名單,沒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沒有吸引注意的公開活動。可以說它們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於解釋底層政治經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通過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參與者的危險減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生的證據。
底層政治本身的性質及其對立面出於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共同造成一種“合謀的沉默”,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完全抹去。歷史與社會科學由於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鬥爭形式,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為紅外線的底層政治。與那些公開的民主政治、目標明確聲音洪亮的抗議示威不同,這些由從屬群體日常使用的謹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動光譜的可視範圍。
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並賦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農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斯科特將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爭語境聯繫起來。通過深入地分析象徵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方法,達到對於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於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究,他並不否認馬克思關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像,不僅強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他的底層視角使他能夠重新思考霸權(hegemony)概念及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經典概念: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雖然闡明了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徵生產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中的階級關係和大多數情境中的階級衝突。原因在於,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權理論還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在強大的經濟占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我們從這一切當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指望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和持久存在的張力。
從《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到《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我們不難看到,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的行為選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實踐層次上是不斷推進的。如果僅僅關注正式的反抗行動,或如果僅以“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來解釋東南亞農民的行為,我們就無從理解為何當他們進入生存絕境時仍未有公開的反抗;而處於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還有什麼能夠讓他們奮起反抗了。對於農民的政治行動,僅用生存倫理的邏輯無法解釋,還必須加上對壓制制度、暴力強度和意識形態治理的考量。面對強大而嚴密的統治,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於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無從形成對壘的雙方,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扭曲和畸變。這種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卻不可能有助於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或使社會的制度安排變得比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偽裝性,即以表面的順從代替實際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強化了統治權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邏輯中也有可能反而變成強者的工具。
介紹斯科特關於農民反抗和底層政治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的不僅是非正式反抗與底層意識形態長久以來不被注意的實際存在,更有支配與反抗之間複雜和微妙的互動關係。而這些,如果沒有對於農民社會與農民權利的真正關心和理解,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底層視角,是不可能達到的。
本書的翻譯歷經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鄭廣懷翻譯,第五章後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錄由張敏翻譯,何江穗校對復譯了第四、五章;郭於華、郇建立分別校對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後又分別通校全書;索引由郇建立翻譯。本書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農村社會學”課程中列為必讀書目,兩位主要譯者由研究興趣所致也都曾反覆閱讀,但由於譯者是第一次翻譯學術著作,經驗和翻譯水平都尚欠缺;整個譯、校過程其實也是艱難的學習過程,雖不敢言嘔心瀝血,卻也是殫精竭慮,儘管如此,錯誤疏漏仍在所難免。加之斯科特教授這部著作堪稱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類學細緻入微的田野實證材料與關於支配與反抗的宏大理論緊密結合,論述方式鋪陳細密,縱橫捭闔,我們的閱讀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處。所有缺撼不足,還望讀者多予指正為盼。
在翻譯過程中,南開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李利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史雲桐幫助譯校了部分內容。特別需提及的是本譯叢主編劉東先生從選定書目、聯繫作者到譯、校的各種細節問題都給予了不厭其煩的幫助指導,在此深表謝忱。
郭於華
2006年5月於北京
作品評論
一部可能成為經典的令人難忘之作。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東南亞農民社會的人都不能錯過此書。
——《亞洲研究雜誌》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種學報告不能也無法呈現的農民反抗外來侵犯的“全貌”……是對反抗霸權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論和經驗闡釋。
——愛德華·W.薩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