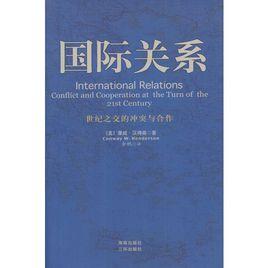發展
建構主義起源於20世紀冷戰結束後,由亞歷山大·溫特在1990年發表了他的期刊文章:“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造成的:實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為新學說奠下了基石。當今世界中的主流觀點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者普遍認為國與國之間受到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深刻影響。而溫特的著作則認為連實力政治也是由社會觀念建構成的,所以對現實主義學說的根基有很大挑戰。1999年,溫特又出版了《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
有影響力的建構主義學者包括瑪莎·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Kathryn Sikkink,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和亞歷山大·溫特。
概念
1989年,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奧努夫(Nicholas Greenwood Onuf)首先提出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這一概念。建構主義之所以得名如此在於它的一個核心觀點:行為體與結構是互相建構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主張套用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國際關係中所存在的社會規範結構而不是經濟物質結構,強調觀念、規範和文化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構性作用。
冷戰的結束與建構主義理論興起有重要關係,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沒有預見到冷戰的結束,而且解釋之都有困難。建構主義則有它的解釋:認為前蘇聯戈巴契夫改革其外交政策是因為他持有“共同安全”這樣的新觀念。
建構主義從許多理論學派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例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的語言學、哈貝馬斯(Jurgen Harbemas)的“話語的權力”、列維·史特勞斯(Levi Strauss)的結構主義、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理論等等。作為一種借鑑社會學研究國際問題的理論,建構主義的根源不能不溯及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韋伯(Max Weber)。關於觀念因素,涂爾幹和韋伯認為康德主義者將精神世界與整個世界割裂開,隔離開科學的方法。而實用主義者卻認為精神生活是毫無意義的,科學家的任務是揭開物質的表層而進人核心的實物。涂爾幹提倡的“第三種派別”認為,觀念因素有其特性,也是個整體,無法簡約為其他因素。同時,觀念又和物質現實一樣是“天然”的.可以用正常的科學模式來研究。建構主義感興趣的理論客體正是觀念。下面我們來看建構主義究竟如何構築它的理論框架。我們將重點放在將之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對比上,以突出它與傳統範式主流理論的區別。
理論框架
與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是,建構主義認為人、組織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社會建構的,並不遵循一個不變的秩序或原理。亞歷山大·溫特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一、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人類社會的主流觀點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質力量驅使成的;二、社會舞台上出現的角色受到的影響來自於他們的認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 。
從本體論而言,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是屬於理性主義。新現實主義以個體經濟學定義個人/公司的方式,把國家定義為利己的、單一性的國際關係理性行為體,國家的利益和身份完全是內部因素決定的,與在國際社會中的活動沒有關係。基歐漢也從曾肯定多元國際行為體的立場後退,承認關於國家行為體的理性主義假定。而建構主義是反理性主義的。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結構不僅僅影響行為體行為,更重要的是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
從世界觀而言,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都接受物質主義理論,不承認觀念的實質性意義。新現實主義的最基本概念—國際體系結構—指的是國家物質力量在國際體系中的分配狀態。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質的,但其作用取決於制度能夠提供的物質回報。建構主義不否認物質的客觀存在,但反對把物質的客觀存在作為解釋行為體行為的惟一和最主要原因的單純物質主義觀點。建構主義是理念主義的觀點,認為權力主要是由觀念和文化情境建構的。權力分配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利益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觀念建構的。也就是說,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他們實際上具有的作用,是因為造就權力和利益的觀念起了作用。
拉吉和霍普夫主要根據認識論對建構主義的流派做了分類。拉吉(John Ruggie)將建構主義大致分成三派:新經典建構主義(Neo-classieal Constructivism)、自然的建構主義(natural construecivism)以及後現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霍普夫(Ted Hopf)對建構主義的分類為:常規的建構主義(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與批評的建構主義(critical constructivism)。在認識論上,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是科學實證主義的歸納式解釋。大部分建構主義者(例如常規建構主義流派)是科學實證主義的個性式解釋。這些建構主義者主要有:溫特(Alexander Wendt)、費麗莫(Marrha Finnemore)、莫塞(Jonathan Mereer)、克萊托奇維爾(Rriedrieh Kratoehwil)、奧納夫(Nieholas Onuf)、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阿德勒(Emanuel Adler)、漢斯(Ernst Haas)、拉吉(John Ruggie)和德斯勒(David Dessler)。反思主義理論,包括一部分建構主義流派(如後現代建構主義或批評建構主義)一般為侄釋性理論,在認識論上是反實證主義的。這些建構主義者主要有:霍夫曼(Mark Hoffman)、艾遜禮(Riehard Ashley)、康培爾(David Campbell)、沃爾克(R.Walker)等。
什麼是科學實證主義?它秉承三個基本原則,即:(1)我們生存的世界其性質與存在既不是邏輯地也不是因果地依賴于思想的;(2)我們關於世界的某些理念是正確的描述一一即使是不完整的描述一一因而是真實的;(3)我們研究的方法使我們能夠發現我們對於世界的某些理念是真實的。反實證主義否定邏輯上及因果上獨立於思想的這樣一種“真實”的存在,或者是不認為我們與可以知道這一“真實”存在的可能性。
主流理論和建構理論雖然都採用科學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但二者的解釋模式不同,前者是歸納式模式,後者是個性化模式。歸納模式是研究者們將事件當作某一類事物的例子之一,是偶然中的必然。例如斯尼德(Jack Snyder)對為何冷戰和平結束的解釋。他說:一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它如何來獲得安全的想法形成的;擴張主義在民主國家不怎么行得通,但在利益集團高度集中化的政治實體中極易盛行;一國的國內政治結構是由其現代化的時間表形成。這些都是歸納,並用它們來解釋冷戰末蘇聯的和平演變。他認為其起因是蘇聯歷史經濟落後造成現代化滯後,在其政治機制當中發展出了新理念:尋求和平的外交政策和融人國際經濟,在冷戰末期,這些理念起到決定性作用。規律及初始狀態表明蘇聯帝國的和平瓦解雖是史無前例的,但也是在該情況下可以被預料到的。這樣該事件被解釋了。個性化模式是,研究者解釋某一事件是通過對導致該事件發生的前後一系列情況進行詳盡的描述。該事件被解釋為具體的一次歷史前後情況的最終點,而不是一類事件中的一例。與歸納化解釋一樣,個性化解釋也必須根據規律,不過是部分規律而不是整體規律,就是每一階段中的規律,而沒有一個貫穿全過程的整體規律。
例如沃爾華斯(William Wohlforth)對蘇聯和平解體的解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說,蘇聯經濟衰弱、地緣政治的脆弱性將改革提上了蘇聯決策的議程。新理念—改變對外及對內政策開始為上層領導人所考慮。在戈巴契夫領導下,從1985年開始,改革是一場邊學邊改的過程,使得蘇聯領導人不斷認識到蘇聯惡劣糟糕的局面。這些領導人在1986一1988期間在軍備控制談判中向西方妥協,希望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以及降低安全成本可以重振蘇聯雄風,等等。這種解釋是對一系列事件的陳述,最後水到渠成。這兩種戰略都是實證主義,不過他們的研究中對問題設定的不同。在歸納法中,研究者會問:這是哪一類的例子?在個性法中,研究者會問:從哪些具體歷史道路上產生了該事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深深植根于歸納式。他們尋求戰爭、革命、威懾、合作、聯盟、經濟一體化等等現象的規律。建構主義則是個性化的解釋,研究國家觀念、身份、國家利益、國際機制、規範、國際結構如何在歷史過程中互動。在方法論上,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是個體主義。建構主義是整體主義。
研究領域
很多建構主義學者通過仔細考量個體和組織的目標、威脅、恐懼、文化、身份和其他因素來分析國際關係。Elizabeth Kier等就曾經向現實主義的軍事、安全理論提出挑戰。另一種思路通過建構主義來了解國家主權的演變。在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中,建構主義還在一個初期發育階段。這個領域的著作包括Jalal Alamgir的《印度的開放經濟政策:全球主義,競爭和延續》 。
通過研究政治、外交辭令對社會現實的影響,建構主義者被認為比現實主義者要更樂觀。
建構主義通常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三足鼎立,有時還會和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提並論。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自認為是“弱式建構主義者”,以與傾向“解構主義”的其他學者劃清界限。激進的建構主義論者進一步質疑“國家”自身作為行動單位的正當性。
代表性人物
1.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
(1)施動者與結構互相建構
建構主義的結構不同於新現實主義的結構。新現實主義的結構是微觀意義上的結構,是物質力量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bilities),它的構成是國家的物質性實力。建構主義的結構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構,主要是觀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構成是行為體的共有觀念。
溫特認為,新現實主義以國家為基本單位,沃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The World System Theory)以世界體系為基本單位,這些基本單位在他們各自的理論中是既定的、不須置疑的。溫特認為這樣他們將體系結構的運作與國家施動者的活動分隔開來了,從而都缺乏對基本單位的理論,無法解釋基本單位的權能,也就無法解釋國家行為。溫特主張更為平衡的施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之間的關係:施動者與結構是相互依存的,施動者是受結構界定的,結構只有通過施動者及其活動的中介才會存在。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建構對於解釋社會行為是很有意義的:並不完全由個體行為就決定了社會形式,也不是完全由社會形式決定了個體行為。
(2)身份、利益與行為
身份指的是行為體是誰或者是什麼的內容。利益指行為體的需求。利益以身份為先決條件,因為行為體在知道自己是誰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由於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內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內容。身份和利益是共同起作用的。僅僅身份本身並不能解釋行為,因為“存在(身份)和需要(利益)畢竟不是一回事”。僅僅利益也不足以解釋行為,利益只是有助於解釋行為的動機,行為還有賴於在一個給定環境中對實現利益的認識。這樣,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兼顧考慮身份、利益、認識,才能解釋行為。溫特以戈巴契夫的“新思維”為例來說明觀念是如何在身份改變過程中起作用的巨側,並使國際關係從一個競爭性安全體系轉變為合作性安全體系。
第一階段是關於身份的共識被打破了。蘇聯的身份本是來源於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相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間聯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身份認識由於許多原因而開始瓦解:蘇聯已沒有能力應對西方的經濟科技及軍事挑戰,政府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衰微,西方保證它無意於入侵蘇聯,這種保證降低了角色改變的成本。共識的瓦解使第二階段成為可能: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原觀念,進而重新審視維持那些觀念的互動的結構。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就反映了他想要使蘇聯擺脫冷戰的思維邏輯,他反對列寧的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衝突不可避免的理論,而且還承認在這一衝突中,蘇聯的挑釁性行動是重要原因。
這樣的重新思考為第三階段的重新實踐鋪了路。對於自我及他者的觀念的重新思考是不夠的,因為舊身份是由與其他行為體的互動體系維持著的,為了改變自我,經常需要改變幫助維持互動體系的他者們的身份和利益。這需要自我採取行動、自我表現,扮演它所想要扮演的新角色,來引導他者重新看待身份,讓他者加人到自我改變的努力過程中去。這一邏輯直接產生於身份形成的鏡相理論(the mirror theory of identity formation),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從東歐撤軍、對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實行不對等裁減、號召防禦性防衛等等這些戈巴契夫的做法,都旨在改變自身角色,而且試圖將西方塑造為“道義上被要求來向蘇聯提供安撫及援助”的角色。
最後,這些實踐行為如果還不能將競爭陛安全體系改變,即如果它們不被他者接受,則自我就處於一種極不利位置,很快面臨枯萎死亡。要成功改變競爭性身份,就必須得到他者的賞識回報,這又會鼓勵自我有更多實踐活動。這樣循環回復,就會對自我及他者的安全有一個正面的身份界定並進而機制化。
(3)無政府狀態的三種文化
經典國際關係理論都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先驗給定的因素,當作國際關係研究的起點。溫特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種體系結構,是國際體系中施動者互動的結果。不同的初始行為,通過互應機制,就可以產生不同特徵的無政府狀態。因此,他反對新現實主義認為的無政府狀態只有一個單一的“邏輯”:自助和充滿競爭的權力政治。他認為至少有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每一種都是由關於自我和他者關係的不同社會共有觀念結構—“敵意”、“競爭”、“友誼”建構而成的。溫特還指出自己這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的政策意義。他說,如果依照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說法,則國家除了以利己方式對待國際環境之外別無選擇。而相比之下,建構主義更加強調對外政策決策者的行為選擇。即使國家在某種文化之中面對某些刺激因素,也總是可能轉化這些刺激因素,並創立新的文化。
2.喬納森·莫塞(Jonathan Mereer)的社會身份理論(SIT,Society Identity Theory)
(1)最小化集團實驗和社會身份理論
莫塞使用“社會身份理論”來解釋“最小化集團”實驗,來為國家身份作出一個社會心理學的解釋。他和溫特一樣,從認同與利益的角度人手。他同意溫特的建構主義的觀點:身份是被建構的,不是既定的。他的觀點是,集團間的對比及競爭是根植於人們的認知及社會身份的。有意思的是,他的結論卻是支持新現實主義的。莫塞介紹了歐洲社會心理學家泰吉菲爾(Henri Tajfel)和特納(John Turner)做的最小化集團的實驗,並引人了社會身份理論進行解釋。莫塞以此說明了在自然狀態下的國家傾向於對於本國和其他國家採取擴大彼此差距的態度。泰吉菲爾的實驗是:首先給被實驗者大略看一下一塊板上的點,讓他們估計報出點數。然後將他們分為兩組,分別被告知多估了或少估了點數。
然後,每個人被帶到一個房間裡,被令將錢幣分成兩份,不分給自己。這樣,這些人知道分配結果對自己並無得失,所以這樣在“自我利益”與“服務於本集團利益”之間並沒有理性聯繫。然後,被實驗者又被令將一些獎品分發給某些個人,這些個人是被說明屬於哪個集團的。沒有什麼實驗可以完全模仿自然狀態下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但最小化集團的實驗設計至少比較接近之。實驗中集團沒有歷史,並不爭奪稀缺資源,沒有反感、自利或互動,所以說是“最小化”。當一個集團成員給另一個集團成員之間分配錢時,喜歡採用相對收益或絕對收益戰略。當一個集團成員在本集團成員與他集團成員之間分配時,基本採用將集團間差異最大地拉開。這一實驗進行了二十年,在威爾斯、荷蘭、前西德、美國、瑞士、香港、紐西蘭等地都做過。
結果表明,當在集團內成員與集團外成員之間分配時,分配者一般會偏向優惠集團內成員,將集團內成員與集團外成員之間的利益差距拉到最大程度。這樣的結果多次重複,無論組多小、利益多小,只要有一個其他組的存在,就會激發產生優惠本組及歧視他組的傾向。簡單地說“打擊他組比純粹收益更重要”。一旦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我們就可以假設不管另一方的行為如何,一方會與另一方競爭。競爭不必被經濟或安全考慮激發,競爭也不一定就是自私的行為,或由於有限資源的原因,相反,競爭源於區別、對比、對於一個正面社會身份的需要。結果,自我與他者在尚未互動之前就是互相競爭的了。華爾茲認為這種競爭源於結構,溫特認為這種競爭源於過程,莫塞的社會身份理論與他們都不同,認為人們對於一個正面的社會身份的認知和需求產生了競爭。從結論上講,這支持了新現實主義的看法: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的準則是自助。社會身份理論為新現實主義的“國家是自顧的”的假設提供了理論的及經驗的支持。
(2)對歐盟的看法
歐盟通常被認為是超越國家利益的典範,而莫塞對歐盟卻另有一種說法。他認為,歐洲一體化背後是一個擴大了的自我,不僅沒有解決自助問題,也不必然導向一個更為他助的世界。例如,沒有理由認為,較之今主流d天的法國身份,所謂歐洲身份將產生更為利他主義的對集團外的安全政策。歐盟也許代表了國家間關係的一個重要轉變,代表國家身份的可塑性,改變國家間關係的可能性,但這並非體系的改變。法國與德國在相互關係上可能已超越了自我中心主義,但在他們與日本的關係中則不會超越。我們越強烈地認同一個集團,則集團內與集團外的差別就越大。歐洲的身份越強大,“我們”與“他們”、“歐洲”與‘舊本”的身份之間差異的感覺就越大。這就是為什麼強烈的群體內主張者也是強烈的反群體外者,為什麼群體自我中心主義、自助、相對收益是國際政治中的永恆所在。
5.瑪莎·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的“規範”(norms)
(1)規範的構成作用和規定作用
規範(norm)指的是行為共同體持有的適當行為的共同預期仁。建構主義者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主流理論把規範看成是協調理性行為體之間行為的手段,這隻指出了規範的一方面作用:規定作用(regulative effeet)。規範還有構成作用(institutive effeet),即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們構成、創造、修正了行為體和利益。規範或者構成認同,或者規定行為,或者兩者兼有。這樣,行為體和結構的互動就通過規範等連線起來。行為體的利益不再是既定的,而是不斷變化和構成的。國家利益不能只從國家內部的客觀條件和物質狀況中推導出來,作為國際社會的規則、制度和價值同樣對國家利益構成影響,這種影響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內化到行為體中,它們不只是限制了國家行為,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國家的偏好。費麗莫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三個案例,從經驗上證實社會規範影響了行為。日內瓦公約沒給國家提供戰略優勢,也沒有幫助國家贏得戰爭。國家批准它們,不是把它們當作實現目的的手段,公約本身就是目的一一肯定世界人民需要何種價值,何種行為是可以接受的。把緩解貧困的目標融人到發展活動中同樣沒有促進任何利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認為這些利益是國家的屬性。援助國和欠已開發國家採取這些政策時,都沒有想到它們會變得更富有,軍事上更安全。他們採取這些政策只是一種表達方式:它們珍視什麼,它們認為什麼是好的和適當的。作為先導國家組成部分的科層組織的建立也是規範的,而不是倫理和道德意義上的。
(2)規範的三個階段
費麗莫具體闡述了規範對國家行為起作用的模式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規範產生”;第二階段是“規範串”,指規範被廣為接受;這兩階段由一個傾斜點分開,指的是一些關鍵的國家行為體接納了規範。最後是內化階段。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費麗莫的研究認為,儘管對於不同規範要求的國家數不同,不過,如果沒有該體系內三分之一國家接受規範,就幾乎不可能出現傾斜點。其二、在傾斜點總是有一些重要的國內運動支持規範,不過傾斜點達到後,就會開始一個不同的機制。在第二階段,國家遵守規範是因為,它們是國際社會中的成員這樣的身份。國家身份從根本上塑造國家行為,而國家身份是由國家在其中活動的文化一機制背景塑造的。是國家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合法性和名譽使得規範串成為可能。規範及觀念本是國際政治研究中受重視的問題之一。
但在五、六十年代行為革命、計量學研究方法興起時,因為觀念和規範現象很難計量,規範研究一度被擱置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用經濟方法研究政治十分流行,加強了棄觀念規範研究於不顧的傾向。八十年代末以來,費麗莫與其他一些建構主義者們的研究是對規範研究的回歸和發展與溫特的帶有濃厚哲學社會學色彩的建構主義論述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費麗莫的著述是“方法論和案例研究的典範”,為規範研究提供了詳盡的案例分析和經驗論證。費麗莫還指出,僅僅斷言“規範重要”對建構主義來說還不夠。哪些規範重要、如何重要、何處重要、為何重要,必須對這些進行實質性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