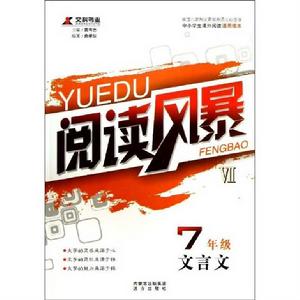原文
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切.每去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則形諸夢.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
翻譯
我在少年時很貧窮,買不起書,但卻非常喜歡書。每次去書店,都貪婪地翻讀,要是價格昂貴無法買下,每天晚上就在夢中想起。曾經寫詩:“學校太遠而且經過集市而發愁,家裡太窮只能在夢中去買書。
《隨園詩話》
清代,袁枚倡導“性靈說”,其專作《隨園詩話》是一部有為之作,有其很強的針對性。
本書所論及的,從詩人的先天資質,到後天的品德修養、讀書學習及社會實踐;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詠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鍊句;從辭采、韻律,到比興、寄託、自然、空靈、曲折等各種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詩的修改、詩的鑑賞、詩的編選,乃至詩話的撰寫,凡是與詩相關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了。
作者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蒼山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慶時期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調做官,曾任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政聲好,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三十三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築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自此,他就在這裡過了近50年的閒適生活,從事詩文著述,編詩話發現人才,獎掖後進,為當時詩壇所宗。袁枚24歲參加朝廷的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總督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於落榜。
著作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隨園食單1卷;散文 ,尺牘,隨園食單說部等30餘種。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古文論者將其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並提。
注釋
1.書肆:書店。
2.諸:兼詞,相當於“之於”。
3.則:就。
4 . 袁 枚:字子才,號簡齋,晚號隨園老人,清代錢塘人,詩人。
5. 少:年少。
6. 則: 就。
7. 然:但是。
8.得:得到。
9.好:喜歡。
10.垂涎翻閱:貪婪地如饑似渴地翻翻看看。
11.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私塾太遠為經過書市而發愁,家裡太窮只能在夢中去買書。
短文作者是清朝袁枚,選自《隨園詩話》,袁枚的代表作是《祭妹文》。
袁枚:清代詩人,散文家。字子才,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作品簡介
曾被魯迅先生稱之為“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從幫忙到扯淡》)《隨園詩話》,是清人眾詩話中最著名的一種。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縣,十三年(1748)辭官而定居於江寧小倉山隨園,故世稱隨園先生,其晚年亦自稱隨園老人或倉山叟。作為“一代騷壇主”,袁枚總領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使沈德潛鼓吹的擬古“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歪風為之一掃,使清代詩壇別開生面。《隨園詩話》正是袁枚為宣傳其“性靈說”美學思想而編撰的著作。
宋人許?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許彥周詩話》)因此詩話著作或以評論為主,或以記事為主,或以考據為主,一般皆屬隨筆性質,篇幅不大。《隨園詩話》當然亦屬隨筆性質,但其主要內容為採錄性靈詩與闡述“性靈說”詩論,間有記事,體例與前人詩話同中有異。它的宗旨是借採錄大量“一片性靈”的詩作論證其“性靈說”的理論,或者說是以“性靈說”的美學思想為標準採集、鼓吹時人的佳作。此書共有二十六卷,(《詩話》十六卷,《詩話補遺》十卷)近五十七萬字,其規模誠屬空前。
《隨園詩話》的精華是其所闡發的“性靈說”美學思想,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譽:“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後世之攻錯。”(《談藝錄》)袁枚也自評,“中間抒自己之見解,發潛德之幽光,尚有可存”(《與畢制府》)。綜觀《隨園詩話》詩論,主旨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的條件,主要在於真情、個性、詩才三要素,並以這三點為軸心生髮出一些具體觀點,從而構成以真情論、個性論與詩才論為內涵的“性靈說”詩論體系。茲略作介紹於下:
一、真情論。《詩話》認為詩人創作首先必須具有真情,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詩人唯有具備真情才能產生創作衝動:“情至不能已,氤氳(yīnyūn)化作詩。”詩作為抒情的藝術自然應該“自寫性情”,並認為“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反對以考據代替性靈。《詩話》尤其推重詩“言男女之情”,以與沈德潛的偽道學觀點相對抗。鑒於詩寫真情,因此標舉詩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強調“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藉以反對“動稱綱常名教”的“詩教”觀。
二、個性論。《詩話》又認為詩人創作需有個性,所謂“作詩,不可以無我”,認為“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因為有“我”,故在藝術構思時則要求有獨創精神,所謂“精心獨運,自出新裁”,才能獨抒性靈,“出新意,去陳言”,寫出迥不猶人的佳作。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個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詩話》主張風格的多樣化,“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因此對王士禎的神韻詩既不推崇,亦不貶斥,指出“不過詩中一格耳”,“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詩話》又著重批判了從明七子到沈德潛的擬古“格調說”及宋詩派末流:“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虛皮傅之見”,“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
三、詩才論。“性靈”既指性情又包括“筆性靈”的含義,表現為才思敏捷。《詩話》認為,“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詩才、天分,但並不廢棄學問,故指出“凡多讀書為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書卷代替靈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氣耳”,為此袁枚反對翁方綱“誤把抄書當作詩”,批評“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基於主詩才與靈性,《詩話》頗重視性靈者創作構思時所產生的“靈機”“興會”這一靈感現象,並推崇“天籟最妙”即藝術表現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為此尤其讚賞“勞人思婦,靜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謠。但袁枚又不反對人功,特別文人詩“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雲天籟,亦須從人力求之”,所謂“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也”。此論頗有藝術辯證法。對於詩歌藝術形象則主張有“生氣”或“生趣”,即靈活、生動而感人,因為“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欲有“生氣”、“生趣”,則語言需生動傳神,“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表現手法以白描為主,“一味白描神活現”,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以免扼殺詩之生氣、生趣。但倘若用典而“無填砌痕”又“貼切”,則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詩論於《詩話》中部分是單獨成條,直接闡述;大多則是結合選詩生髮。詩論的美學思想是《詩話》的選詩標準,它又是在評論選詩的基礎上升華出來的。因此《詩話》內容的基礎正是大量的選詩。袁枚曾說過:“枚平生愛詩如愛色,每讀人一佳句,有如絕代佳人過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無分,而不覺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隨園詩話》之所由作也。”(《答彭賁園先生》)可見其撰寫《隨園詩話》與選詩之密切關係。《詩話》的選詩大致有以下特點:
一、選詩標準較嚴。這主要表現為“詩”為“話”服務。袁枚明確指出:“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則必先有話而後有詩。”其標準是所選抒寫性靈之佳作能印證其“性靈說”的理論。
二、入選詩作者面頗廣。袁枚稱曰:“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入選者既有詩壇高手,亦有無名小卒;既有公卿將軍,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婦閨秀,亦有妓女歌姬;舉凡三教九流,不問性別身份,只要詩佳皆可以詩存人。尤其應注意的是,袁枚對勞人思婦、村氓淺學、小販工匠等下層勞動人民宛如“天籟”、極富性靈的創作尤加讚賞,甚至譽為“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從而摘錄入《詩話》。
三、選錄女子詩尤多。袁枚針對“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習,反其道而行之,聲稱:“余作《詩話》,錄閨秀詩甚多。”其中既有其眾多女弟子的詩,也有素昧平生的閨秀、寡婦,乃至無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詩話》曾選入時氏一家夫人、閨女、兒媳五人之詩,並譽之為“皆詩壇飛將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謂有膽有識。
四、入選詩作題材豐富。《詩話》中抒寫個人悲歡離合之作固然頗多,但亦不乏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好詩,諸如諷刺催租吏的《牛郎織女》,抨擊封建禮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舉八股文的《刺時文》等等,更應提及的是《詩話》蒐集了明季愛國烈女的抗清事跡與遺詩,如記一江陰女子被清兵俘虜後,於赴江死前曾齧指血所題詩:“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義凜然,英氣逼人。此外還選錄不少情詩,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反道學的意義。
《詩話》雖有“集思廣益”等優點,但當時有人訾其“《詩話》收取太濫”亦不無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時並未嚴格執行其選詩標準。他曾承認選詩“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因此《詩話》中無聊應酬之作並不罕見。而入選的某些“情詩”感情也不健康,失之於卑靡輕佻,如所選錄的其從弟香亭的“情詩”即是。記事部分偶有象“兩雄相悅”一類醜聞,而作者對此抱欣賞態度。此外,袁枚還十分相信所謂“詩讖”,選錄了多首,宣揚迷信唯心的思想。《詩話》引用古詩文多不註明出處,引文亦時有謬誤而未曾校訂。這都是《詩話》的缺陷。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後》等文中攻擊《隨園詩話》“論詩全失宗旨”,“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則純系封建衛道士口吻,當然不足為訓。
袁枚《隨園詩話》等著作印行後,“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姚鼐《袁隨園君墓志銘並序》);儘管身後毀譽交半,但《詩話》“家喻戶曉,深入人心”(錢鍾書《談藝錄》),廣為流傳,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性靈派詩人更奉之為詩學圭臬。
《詩話》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餘種著作一起自費付梓印行,並得到畢弇山尚書、孫穭田司馬“為資助刻”。最早版本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倉山房刊本,稍後還有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的《批本隨園詩話》,其批語多為對《詩話》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紹,間亦表示對《詩話》觀點的看法等,雖文字粗疏,見解不高,但可資參考。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印《隨園三十六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詩話》。現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之一的由顧學頡先生校點的《隨園詩話》上下兩集本,此書據乾隆隨園自刻本校訂、標點排印,於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顧學頡先生又於文末附錄了《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語及有關跋語、資料,使之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