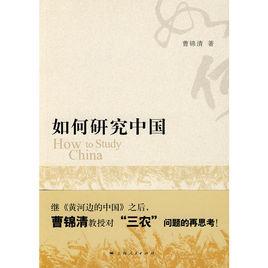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如何研究中國》:繼《黃河邊的中國》之後,曹錦清教授對“三農”問題的再思考。
作者簡介
曹錦清,著名社會學家。1949年生,浙江蘭溪人,現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社會學教授、博導。主要著作有《現代西方人生哲學》、《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國單位現象研究》、《平等論》、《黃河邊的中國》、《中國七問》等。其中《黃河邊的中國》一書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成為觀察研究中國當下農村社會的最權 威、最流行的作品,並榮獲第五屆“上海文學藝術獎”,2005年其英譯本出版。
媒體推薦
土地直到目 前還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職能,所以在統計失業人口的時候,我們只統計有城市戶籍的人口而不統計廣大的農民工。為什麼?因為給了農民一畝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為考慮到這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目 前只能遊走在城鄉之間,能夠介入工業化而無法完成城市化。與其說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安排,還不如說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只能採取這樣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誰會失去土地?一個大的天災,一個大的市場波動,一次較大規模的負債就可能使農民失去土地。
“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也不是減負,它是關係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是應該由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合理公平地分配。在這個問題上,靠市場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場天生是產生不平衡與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國家能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從“小康社會”的提出,到“和諧社會”的建構,這不僅是我們對發展目標的重新厘定,而且表達了我們民族對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確責。“小康”與“和諧”不僅語出先秦儒家,更為有意義的是,它確立了兩千餘年來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目標。
所以我講必須將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使其真正地學會自我管理,學會民主化。使農民成為有組織能力的公民,這個歷史任務要通過農村的組織化來完成。因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體並不完全是政府,而應該是農民自己。農民只能通過組織起來才能夠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
——曹錦清
圖書目錄
序
中國研究的方法
論中國研究的方法
“三農”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三農”研究的基本框架
“三農”問題的思路與出路
四個歷史觀與近六十年的歷史
從“以西方為中心”到“以中國為中心”
理解中國——曹錦清教授訪談錄
《黃河邊的中國》前後的故事
重新發現傳統
論國學的可能意義
宋以來鄉村組織重建——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
儒學復興之路——梁漱溟論東西文化特質
民權與國族——孫中山對東西文化的思考與論述
中國的和平傳統:一個歷史的考察
和諧社會:傳統思想資源及其當代啟示
中國轉型轉向何方
從和諧社會看“三農”問題
社會轉型視野下的新農村建設
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城鄉關係
承包制小農與國家
堅持土地家庭承包制,還是土地私有化
擴大內需,沒有簡單藥方
就業問題是重中之重
代跋:思想為何放棄職守——知識精 英階層責任缺失的社會歷史分析
文摘
他們認為改革開放30年出現了許多問題,尤其是農村出現了好多問題,大量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圈占,很多農民失去土地。他們認為如果產權清晰,這些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一直到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前,還有許多人鼓吹要把土地私有化,要把林地私有化,要把耕地私有化,要把宅基地也私有化。他們說如果作為重要生產資料的土地不能私有化,作為市場經濟是不完備的。
認為市場經濟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都和土地的產權不清有關係,這種觀點我認為也是食洋不化。第一,改革開放之初,尤其是1982年開始實行的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按照人口來均分土地,這一制度是不符合經濟效益最大化原則的,但這是農民唯一能夠接受的公平原則。所以改革開放的起點,真正的起點是農村制度的變動,尤其是土地制度的變動。這種土地制度不是按照市場的原則最佳化配置土地資源,也不允許土地私有化,而是按照人均來加以分配。當時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觀點來說只能做這樣的制度安排。土地直到目 前還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職能,所以在統計失業人口的時候,我們只統計有城市戶籍的人口而不統計廣大的農民工。我們在理論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認農民工處於失業狀態的,為什麼?因為給了農民一畝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為考慮到龐大的農民工這個群體。根據中國第五次農村普查,出鄉打工的農民工1.3億,其中出省打工的5600萬,在鄉內打工的估計有3000萬-4000萬或更多。如此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目 前只能遊走在城鄉之問,能夠介入工業化而無法完成城市化。與其說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安排,還不如說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只能採取這樣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誰會失去土地?承包制的小農,他們能夠穩定自己的土地嗎?一個大的天災,一個大的市場波動,一次較大規模的負債就可能使農民失去土地。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不斷發生。譬如雍正年間,河南發生旱災,因為旱災,所以農民的土地非常便宜,農民為了明 天的糧米不得不出賣土地。結果大量的土地轉移到當時有錢的晉商手裡。
序言
逝者如斯,忽已臨花甲之年。諸生從我歷年的講演、訪談和文章中選出若干匯為一集。出版還是不出版?問題雖沒有哈姆雷特的那么嚴重,但於我卻著實猶豫半年有餘。這些被我遺忘許久的訪談、講演稿重新結集出版,有無必要,對讀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確定。於是諸生邀來出版社的朋友,說此一問題最好交由出版社來判斷。
諸生將文集分為三部分:一談研究方法,二談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三是理解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經他們這一分類,我也對近幾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認識。
遠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針對知識分子集中關注的“應該”,我們轉向“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於是強調以實證為方法。後來才發現,“應該”的背後是“普世說”!而“普世說”背後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方法論。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研究中國問題,不“應該”以“西方為中心”,而“應該”以“中國為中心”。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已經解決了這個近代中國的難題。他說研究中國,要以“中國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並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解決了“古一今”和“中一外”矛盾的長期糾纏。但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背景下的當代中國學術界,“古一今”和“中一西”卻重新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當然,“方法論”背後說到底是個民族自信問題。幸賴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上所取得的輝煌,才多少醫治了我們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讓我們獲得了些許平視(但願不要走向“俯視”他人的另一極端)西方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