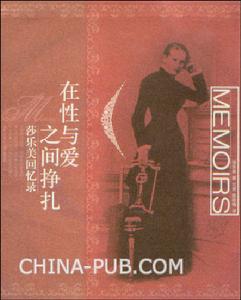基內容簡介
尼采有句名言:“回到女人身邊去,別忘了帶上你的鞭子。”尼采對女人的這種憎惡情結正是緣自本書的作者和主人公——莎樂美。.
“弄瞎我的眼睛,我依然會看見你;塞住我的耳朵,我依然會聽見你……”里爾克的這首感人的情詩是為莎樂美而作。細心的讀者可以從本書的一幅圖片中發現,弗洛伊德的書架上擺放的居然是莎樂美的照片。
作者簡介
莎樂美:德國女作家,生於19世紀中葉,一生經歷了跨世紀和德國婦女解放運動等大事。21歲時寫的詩歌把尼采感動得潸然淚下;24歲出版長篇小說《為上帝而戰》,受到德語文學界的高度讚揚;關於易卜生戲劇中婦女形象的評論使她名聲大振;在精神分析學方面表現出的興趣和才華,令弗洛伊德深為感動;最突出的,還是一系列探討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當時人們這樣評價她,說她的文章,能夠作為婦女解放最為有力的武器。這類文章幾乎把她推到"婦女問題的法官"這樣的位置上。
俄羅斯流亡貴族的掌上明珠,懷疑上帝的叛逆,才華橫溢的作家,特立獨行的女權主義者,不守婦道的出牆紅杏 為尼采所深愛,受弗洛伊德賞識,與里爾克同居同游。
目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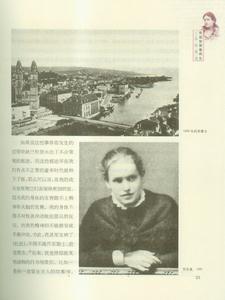 頁內插圖
頁內插圖第1章 被剝奪的神聖空間——體驗上帝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體驗愛情
第3章 尋找兄長般的男人——家庭生活
第4章 流亡途中的烏托邦——體驗祖國俄羅斯
第5章 我們是從哪顆星球上一起掉到這裡的?——和尼採在一起
第6章 另外一種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
第7章 他就是從那深淵裡出來的——和里爾克在一起
第8章 風暴用數不清的花蕾裝飾潮濕的大地——致里爾克
第9章 分擔另一個人的超凡而罕見的命運——弗洛伊德的精神
第10章 太多的願望使我病痛——和沸洛伊德在一起
第11章 長長的花園的盡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第12章 無性的婚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第13章 這回憶不是葬禮——手稿中沒有發表的部分
精彩書摘
在我們家眾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小,也是惟一的女孩。在我關於家庭的體驗中,兄弟姐妹之間的團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直影響著我跟男人之間的關係,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不管什麼時候,每當我認識一個男人,我總會感到在他身上隱藏著兄長的形象。不過,這也跟我那五個兄長的性格有關,尤其是其中的三個,因為老大和老四年輕時就死掉了。儘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滿孤獨的幻想,儘管我的所有思想和志向的發展都跟家族的傳統發生衝突,而且惹出了層出不窮的麻煩,儘管我的後半生一直在國外度過,遠離我愛的人們,但是我跟兄長們的親情一直沒變。我們雖然相隔遙遠。但隨著時光流逝.我的判斷力越來越成熟,這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他們作為人的價值。事實上,在後來的年月里,每當我開始質問或批評我自己的性格,我總是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我跟他們來自同一個家庭。實際上,我碰到的每一個男人,如果他表現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漢的氣概或心靈的溫暖,他就會喚醒我內心中兄長們的形象,這些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在我90歲的老母親去世時,兄長們分給了我雙份的遺產,儘管兩位已經結婚的哥哥有15個孩子要撫養,而我一個都沒有。當我追問遺囑的情況時,他們告訴我說,那是他們決定的事。難道我不知道我一直是他們的“小妹妹”?他們中最年長的——亞歷山大,也叫薩夏”——一直像我們的繼父似的。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親一樣,在許多圈子裡,都非常活躍,而且樂於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在我所聽到的笑聲中,他的是最有感染力的。他的幽默感既采自一顆非常清醒、理性的頭腦,也來自一顆充滿溫暖的心靈;他在幫助別人時,表現得極為自然。在我15歲的時候,當時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會收到他的噩耗的電報。我在震驚之餘,有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反應:“現在誰來保護我?”我的二哥——羅伯特,也叫羅巴(在我們冬天的舞會上,他的馬祖卡舞跳得比誰都優雅)——多才多藝,而且相當敏銳。他本想跟父親一樣做一名軍人,但父親要他做工程師,於是他真的當了工程U幣。三哥叫尤金,也叫任尼亞。他本是天生的外交家,但父親的獨斷專戶三迄壁牛違背自己的意願,成了一名醫生,不過他是個成功的醫生。儘管我的兄長們相互之間有著根本的差異,但他們共同擁有一個傑出的特點:他們都能把自己徹底地奉獻給他們各自的職業技術。我三哥成了一名兒科醫生——甚至在他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他就顯示出了對小孩子的興趣。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一直保持著他的私人空間,像個外交官似的,善於保密。我的另一個童年記憶是:他曾因為我公然抵制家規而指責我。有一回,我狂怒不已,真想把一杯滾燙的牛奶潑到他身上,但我卻反過來潑了自己一身,燙壞了脖子和脊背。我們兄弟姐妹都愛衝動,三哥也不例外,他興高采烈地說:“你瞧,這就是你想幹壞事的下場。”他在40歲時死於肺癆,好多年以後,我才開始更多地理解他。比如,儘管他又高又瘦,一點都談不上英俊,但他總能喚起女人們心中最強烈的激情——雖然他一直沒有選定一個女人作為他人生的伴侶。有時我想,他那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種讓人幾乎無法抵擋的誘惑。有時,他也表現得非常幽默。比如。有一回,在我們一起跳舞的時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換舞伴,於是他那颳得精光的臉寵上有了一綹美麗的假髮,他那瘦削的身上則穿著一件摩登至極的緊身胸衣。在沙龍龍舞舞會上,他收到的絲帶比任何一個女孩都多,這些絲帶都是那些年輕的軍官贈送的,他們不太了解我們的家庭情況,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家有一個還沒有長大的女孩,喜歡獨來獨往。我特別喜歡平底舞鞋,我一開始上舞蹈課就喜歡穿這種舞鞋。我喜歡在大廳的鑲木地板上跳滑步,感覺就像是在冰上。我也會被帶到其他宏大的廳堂里,它們的屋頂高得像教堂似的。我父親的官邸坐落在將軍辦公樓的側翼。有些房間很適合於跳滑步,所以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現在當我回想往事,我仿佛還能看見自己跳著滑步——一直是一個人。
在拜羅伊特呆了一陣子之後,我和尼采打算去圖林根住幾個星期——我們在那兒所住的房子的主人是當地的一個牧師,他碰巧是我在蘇黎世學習時的老師的一個學生,所以我們有同門之誼。一開始,我和尼采似乎對各種各樣無聊的話題都要爭論一番,我至今無法理解那些話題,因為它們沒有事實的基礎。不過,我們很快就把爭論置於腦後了,而我們後來的經歷則非常豐富多彩,而且沒有任何第三者來打擾我們。在這段時間,比在羅馬時期或在旅行時期,我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尼采的思想。除了他當時剛剛完成的《快樂的科學》,我對他其他的任何著作一無所知。在羅馬時,他曾給我們朗誦過《快樂的科學》里的章節。每當尼采朗誦的時候,他和雷的嘴裡會不約而同地進出同樣的詞句。自從尼采和華格納分道揚鑣之後,有一段時間,無論在知識上還是在精神上,他和雷是並駕齊驅的。尼采偏愛格言體寫作——那是他的疾病和生活方式導致的——雷天生也有這種偏好。他的口袋裡常常揣著如拉羅什富科或布呂耶的作品,他在知識界的位置一直動搖不定。那時他正在開始寫作他的第一部小型專著《論虛榮》。而尼采這邊呢,他已經在開始收集他的格言,準備出版《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們在這部作品中感到了尼采這個尋找上帝的人的深刻衝動,他的思想來自宗教,而且正在走向宗教的預言。
我早在那時給雷的一封信中就已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在遇到尼采後不久,就寫信跟瑪爾維達說,尼采是一個具有宗教本性的人。她很不情願接受我的這個看法。今天,我想再次重申這一點。我們會活著看到他成為某種新宗教的預言家,他會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在所有這一切事物上,我和他的所感所非常相像,有些話能異口同聲地說出來。在過去的三周里,我們聊啊聊,幾乎要聊死了。奇怪的是,他幾乎每天能跟我談10個小時。這很奇怪,不過,我們的交談使我們不知不覺走向了陷阱,走向那些令人迷惑的地方,我曾經單獨一個人爬到那陷阱的邊沿,看到下面的深淵。我們就像兩隻山羊,如果有人聽見我們,他可能會以為是兩個鬼魂在談話呢。”
當尼采跟雷談話時,我不可避免地會著迷於他的言語和本性中的某些東西,這些東西是不會得到完滿表達的。對於我來說,其中夾雜著最最孩子氣的回憶或似懂非懂的感受,這些回憶和感受來自我個人不可摧毀的童年回憶。不過,它們還不至於使我成為他的信徒或追隨者:為了把所有這一切都搞明白,我得逃避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猶豫不決。同時,這種痴迷伴隨著某種內在的厭惡情緒。
在我結婚之前的日子裡,保羅·雷曾有意地避開波希米亞文人的圈子,我們交往的範圍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學術界的,但這種情況現在改變了。我從來不曾對文學這樣地感興趣(俄羅斯文學使我感興趣是出於別的原因)。當我涉足文學時,我感到自己很“無知”,對早先時候輕鬆的樂觀主義一無所知,而這場新的爭論就是針對那種樂觀主義發動起來的。不過,那最使我們感動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樂、活躍和自信,甚至於當我們在處理最黯淡無光、最令人壓抑的問題時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國的聲名是個重要的事實。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紹給我,向我朗讀挪威語本的原文,一邊讀一邊還譯成德語。兩座“獨立劇院”出現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先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領導下,不斷地取得勝利。我跟獨立劇院的創始人之一馬克西米連·哈登的友誼也是從那時開始的,而且延續了許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除了格哈德,卡爾·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時都還想在哲學領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時也在提倡對戲劇的熱忱。奧托·哈特勒本積極地參與了進來,與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輕人為了文學和政治目標拋棄了他們的學術雄心。我把許多個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庫聶曼的爭論上了,那時他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要一輩子在大學裡教書。在那些我最親近的人之中,從人性意義上而言,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喬治·勒德布爾:讓我把這些詞句當成對他的問候。
那時我們已經準備搬進第二處公寓,它正好位於森林的邊緣。房子極小,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不需要請人來收拾。那時——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兒的文壇也正在發生類似的變化。那時正值卡諾總統被暗殺,各個方面的人都被卷進了政治的漩渦。安多瓦內的“自由劇院”開張了,它跟柏林的“獨立劇院”相仿佛。呂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霍普特曼的《阿內爾》中的女主人公曾經在柏林由寶拉·康拉德扮演,她後來成了施萊特爾的妻子,安多瓦內把它在舞台上演成一個貧窮\蒼白的街頭小女孩形象。儘管法語時時跟霍普特曼的詩歌發生衝突,如當阿內爾說詞“Fliederduft”(百合花的香氣)時,她不得不說成了一個句子“掃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聞到了百合花的香氣)。後來在俄羅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動心的郇可內爾》:它之所以那樣地令人動心,是因為它用拜占庭風格表現了天堂和救世主,而這種風格是克制的、樸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樣,我跟各種文學圈子頻頻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興趣,只有老一輩文人反對我們。
赫爾曼·邦當時住在聖日耳曼,非常活躍。儘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滿幻想。我現在幾乎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談話,他說,每當他開始一個新的寫詩計畫時,他會恐懼得發抖:他會一直跑到視窗,希望能看到某種他可以用作藉口的東西,那樣他就可以不馬上開始寫。你幾乎能看到藝術創作過程中的那種無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識的最深層,使物象發生明顯的變形;你也可以看到藝術家的恐懼,那種恐懼在轉變的過程中戰勝了他。儘管我很了解赫爾曼·邦的那些曠日持久的問題,但是從那之後,我每次看到他,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懼轉變成一種更加活躍的東西,而且在生理層面上也是如此。我們認識到,邦的小說(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個人記憶,我們也會感覺到那種伴隨他的寫作的恐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