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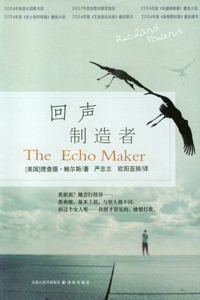 回聲製造者
回聲製造者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苦苦掙扎於自我形象的消解與重組之中。人物自我發現的閒適節奏和大量技術與自然方面的細節有利於充分的探討。小說進而探索了人類自我和人類自身命運的多變性以及把人們與其他造物分開和相連的人的頭腦的不可靠性。
這部小說的行文風格是個既抒情又明晰的奇蹟。
作者簡介
理察·鮑爾斯(1957— ) 美國小說家,曾就讀於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物理系,後獲文學碩士學位。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涉獵考古學、海洋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美學、醫學、音樂等領域。
鮑爾斯是在電視和電腦時代出生的第一代人的代言人,被譽為美國文壇在後品欽時代湧現的最重要、最令人欽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說致力於探索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呈現出鮮明的後現代主義小說的特點,把辭彙上的藝術鑑賞力和結構上的大膽結合得令人眼花繚亂。他大都採用多角度平行敘事的表現手法,以對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增加故事的懸念和複雜性,並提醒讀者:我們從未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時又從未如此孤單。此外,他還注重事實與虛構相結合,並通過不確定性的語言符號系統構建虛擬世界,以揭示現實世界的零散和混亂。鮑爾斯獲得過各種獎項二十多次。
作品導讀
2006年美國全國圖書獎
2007年美國普利茲獎提名
2006年度《華盛頓郵報》最佳小說
2006年度《波士頓環球報》最佳小說
2006年度《芝加哥論壇報》最佳圖書
2006年度《西雅圖時報》最佳圖書
本小說探討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真的是誰。
——《紐約人》
《回聲製造者》……致力於探索現代神經系統科學常常在思考的許多純哲學的問題——意識的根源是什麼?我們極其複雜的大腦是如何工作的?我們每一個人何以成為我們自己?
——J.A.馬吉爾,美國評論家
這部小說寫的並不只是馬克那受損壞的大腦……它總體上聚焦於人類的心靈和人類想理清過去和現在的努力。
——美國《圖書館學刊》
一曲關於人類脆弱性的瘋狂的交響曲……
——美國《娛樂周刊》
圖書譯序
亘古律動,現實回聲
(代譯序)
嚴忠志在2006年美國全國圖書獎的激烈爭奪中,理察·鮑爾斯的《回聲製造者》擊敗眾多競爭者,一舉獲得了小說獎。今年,譯林出版社決定出版此書,將這位著名作家介紹給我國讀者,這無疑是一件值得讚許的事情。
理察·鮑爾斯現任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英語系教授、貝克曼高級研究院研究員,於1998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他上大學時最初學的專業是物理,第一學期便轉為英語,後來於198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那時,鮑爾斯對美國大學嚴格的專業化頗有微詞,認為研究生學習沒有樂趣可言,於是放棄了繼續攻讀博士的想法。畢業之後,鮑爾斯在波士頓當電腦程式員,後來放棄那份工作,專門從事小說創作。
在美國,鮑爾斯被譽為具有豐富科學人文主義思想的作家,他的小說往往自由地徜徉於科學和藝術兩個世界之中,大都帶有特定的技術背景。例如,處女作《三個農民去舞會》中的兩個平行故事之一是關於一位叫彼得·梅斯的技術雜誌編輯的。旅居荷蘭期間創作的《囚徒困境》並置了迪斯尼樂園和核戰爭兩條線索。《金甲蟲變奏曲》涉及遺傳學、音樂和計算機科學,光怪陸離的世界被用來類比人的思維過程。《迷魂行動》的大部分書稿在劍橋大學期間完成,講述了一位年輕醫生是如何面對兒科病房的種種醜惡現狀的。《葛拉蒂2.2》涉及到一種具有人工智慧的計算機軟體。《贏利》考察了一個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化學公司,其中穿插了一個住在該公司下屬一家工廠附近、罹患卵巢癌的婦女的故事。《衝破黑暗》也包含平行敘事結構,其中之一講的是一個試圖建立全新虛擬現實的研究團隊的故事。《我們歌唱的時代》提供了音樂和物理學的淵博知識。
新作《回聲製造者》涉及的專業知識是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和生態學,展現了心智、身體和精神交融一體的圖畫。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在內布拉斯加州的一條車少人稀的公路上,二十七歲的馬克·施盧特出了致命車禍,腦部嚴重創傷。相依為命的姐姐卡琳不得不回到讓她不堪回首的小鎮,照顧命懸一線的弟弟。馬克從昏迷中醒來之後,行為變得怪誕異常,表現出各種各樣的妄想症狀,甚至認為精心照顧他的卡琳是冒名頂替的特工。卡琳與著名認知神經學專家傑拉爾德·韋博取得聯繫。韋博來到內布拉斯加州小鎮卡尼,確診馬克所患的是罕見的雙重錯覺綜合徵。該病患者似乎總是錯認所鍾愛的人,例如母親、父親、配偶。患者辨識他人面部的那部分大腦是完整無缺的,可是由於某種未知原因,處理情感聯繫的那部分與它們分離開來了。
我們知道,在後現代社會中,文化並非統一整體,是充滿矛盾的複雜混合;主體由敘事建構,是複雜的、多元的。《回聲製造者》採用了雙聲語,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理念。鮑爾斯曾說,這部作品的敘事要實現兩個目的,其一是講述一個關於現實世界的故事;其二是要“揭開表面,讓人看到處於敘事下面的沒有定型、臨時改變、非常混亂、遍是裂縫、使人目瞪口呆的東西”。小說大部分敘事聚焦於馬克、卡琳和韋博這三個主要角色,對事件的敘述分別通過他們各自的認知過程一一展現出來,小說的世界就是這些角色的感覺所組合的東西。此外,《回聲製造者》並不是人們常說的科幻小說,我們不妨暫且將它稱為科技小說。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和廣博的知識精心設計了懸念叢生的疑案故事,並且以沙丘鶴遷徙為背景,探討了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和生態學問題。小說分為五個大部分,標題分別是卡琳在醫院裡發現的那張字條上的五行字:我微賤無名/今晚走在北線公路上/上帝引導我到你身邊/這樣,你能活著/然後挽救別人。小說的基本情節以幾個主要角色為中心展開,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技巧。
其一,圍繞著馬克的故事,作者設定了幾個貫穿全書的懸疑:車禍那天夜裡,究竟出現了什麼情況?是誰在開車?是誰打電話報警?是誰在馬克的病床前留下了字條?字條內容暗示,寫字條的人了解車禍的內幕。它是馬克手裡掌握的弄清車禍真相的唯一線索。此外,車禍現場為什麼會留下三組車輪痕跡?另外兩輛車的駕車人是誰?當地開發商挖空心思,希望獲得沙丘鶴遷徙路途中的這片土地。也許馬克知道某些秘密,從而招來殺身之禍。馬克在車禍出現前看到的白色東西是什麼?是沙丘鶴、人影,還是幽靈?是誰救了馬克,馬克應該“挽救”誰?馬克是否能夠找回真實的自我?所謂的“真實自我”究竟是什麼?這一連串疑問吸引讀者刨根問底,隨著跌宕起伏的情節深入閱讀。
其二,卡琳與馬克之間的關係在小說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對推動情節、深化主題起到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卡琳一直擔任馬克的守護天使的角色。車禍之後,姐弟間以前的關係究竟有多少依然保持完整?馬克被雙重錯覺綜合徵所困,拒不承認卡琳是自己的親姐姐,從而讓她的身份意識受到很大衝擊。卡琳能夠讓弟弟恢復正常,重新和她相認嗎?為了發現馬克大腦中影響記憶能力的病症,卡琳應該採取什麼行動?隨著馬克病情的發展,她對自己過去的理解會出現什麼變化?
其三,韋博提供了神經學專業視角,這對強化衝突、豐富情節起到了重要作用。韋博來到小鎮提供幫助,或者說至少為他自己的研究收集素材。他事業成功,婚姻幸福,擁有施盧特姐弟倆完全沒有的東西。但是,他西部之行的時間恰恰與他職業生涯中的一次危機巧合。對馬克的治療效果欠佳,這對韋博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讓他懷疑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思考自己的動機,追問自己的良心、職業道德和倫理價值。推動作品情節的問題還包括:韋博以什麼方式擔當了卡琳姐弟倆的父親的角色?內布拉斯加州之行究竟能否幫他度過這場自我認同危機?
另外,帶有神秘色彩的芭芭拉也增加了情節的懸疑感。芭芭拉是一個外來的陌生人,然而卻是馬克信任的唯一角色。這個女人精明幹練,博學多才,卻幹著醫院護工這份遠遠低於她實際能力的工作,她的真實身份究竟是什麼?她為何待在這個偏遠小鎮?是什麼共同的虛空感讓韋博和芭芭拉走到一起的?為什麼心地善良的芭芭拉總是顯得非常內疚和沮喪?
在小說結尾,圍繞字條和車禍的疑案水落石出。但是,讀者不禁會問:明年這個時候,馬克會承認卡琳嗎?芭芭拉會經受住良心折磨嗎?她會不會逃之夭夭?如果芭芭拉留下來,卡琳是否會諒解芭芭拉的行為?卡琳是否會像卡什曾經放言的那樣,回到他的身邊?心灰意懶的丹尼爾將何去何從?對每個主要角色來說,“微賤無名”意味著什麼?誰將最終得到挽救?
關於這部作品的寓意,評論界眾說紛紜。鮑爾斯在一次訪談中說,儘管這本小說涉及到科學知識,其重點卻不在科技“本身包含的信息,而是韋博(或者卡琳等人)靈魂深處的寓意豐富的材料”。換言之,科學知識在這裡所起的作用是提供理解角色、揭示主題的背景材料。筆者認為,小說作者獨具匠心,使用了若干寓意深遠的隱喻,體現了科學人文主義思想,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和思考,其中最富於啟迪的是沙丘鶴——回聲製造者——和雙重錯覺綜合徵。
在小說中,沙丘鶴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顯然具有豐富的蘊涵。鮑爾斯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時說,小說的靈感來自他偶然見到的沙丘鶴一年一度遷徙的壯觀景象。印第安人認為,沙丘鶴能發出響亮的聲音,所以將這種鳥兒稱為回聲製造者。小說的每一部分都以描寫沙丘鶴開始。例如,小說首先展現的是沙丘鶴聚集的場景:“夜幕來臨,沙丘鶴紛紛降落。它們在空中減速,然後飄然落下。它們從四面八方飛來,十來只結為一群,與暮色一起垂下。”接著,沙丘鶴目擊了車禍。因此,讀者自然會期待,沙丘鶴在作品中應該起到獨特的作用。
一方面,沙丘鶴的命運促使讀者進一步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擴展自己的生態知識,增強自己的生態意識。“那些鳥兒翩翩起舞的動作就像人類的最近親屬,模樣就像人類的最近親屬;它們呼叫,表達意願,生兒育女,在飛行中確定方位,這一切都像人類的血親。在它們的身體組成部分中,有一半仍然和人類的類似。然而,人類卻將它們置之一旁:冒名頂替者……”卡琳的兩個前男友都與它們的存在相關:苦行者丹尼爾是愛鳥人士,知道沙丘鶴是從遠古時代倖存下來活化石,致力於沙丘鶴傳統棲息地的保護工作。卡什是一個利慾薰心的開發商,希望使用保護區內的土地,修建觀鶴設施,他的計畫可能給沙丘鶴帶來滅頂之災。
另一方面,沙丘鶴不僅反映了作品對保護野生動物問題的關注,而且也含有寓言、隱喻和象徵意義,引入了記憶、意識等方面的主題。“這些鳥兒具有某種特殊的功能,在父母帶領它們遷徙之前,就有能力找到數百年前確定的飛行路線。每一隻鶴都記得未來的飛行路線。”“鶴身體中有某種東西被困,困在現在和某個時刻之間。”鳥類一直代表人類靈魂。“這些長著羽毛、高聲鳴叫的‘恐龍’,是自我形成之前生命的最後一種偉大提示。”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生活在含混不清的回聲中。在大自然變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僅僅是匆匆過客:“在人類將自己毀滅數百萬年之後,貓頭鷹的子孫將會把夜晚編成管弦樂曲。沒有什麼東西會記住我們人類。”
《回聲製造者》使用大量筆墨探討意識的性質,展示了回憶與遺忘對角色的影響。一個難以解開的奧秘是,人的大腦是如何留下特定時刻的痕跡,然後用自身掌握的信息來建構人對宇宙意義的理解的。人類記憶的東西不可能完全精確。然而,沙丘鶴卻能在每年的遷徙中準確導航。航線銘印在它們的腦海中,它們的記憶就是地圖。由此看來,沙丘鶴——可能還有大自然——是真實記憶的唯一擁有者。而且,更令人稱奇的是,已經存在了五百萬年之久的沙丘鶴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但卻沒有意識的負擔,它們僅僅按照古老的記憶活動,重複基本的生死輪迴。
讀者不禁要問:這些沙丘鶴究竟製造了什麼“回聲”?對觀鶴遊客、環保人士和普拉特河沿岸居民來說,沙丘鶴意味著什麼?在遷徙的鶴群與馬克遭到破壞的記憶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係?此外,面對時間的不可理解性,沙丘鶴讓人頓生種種感悟。這些精靈身上包含亘古律動,過去與現在融為一體,形成了無盡回聲。在鮑爾斯眼裡,所有小說都是時光寶箱,而《回聲製造者》蘊含的時間更長,內容更豐富,超過了大多數同類作品。
在鮑爾斯的作品中,科學知識或者技術知識常常被用作隱喻,《回聲製造者》中的雙重錯覺綜合徵也起到這樣的作用。雙重錯覺綜合徵是一種錯認綜合徵,可能出現在某些精神疾病中。患者失去語言能力,困在時間之中或者停留在前哺乳動物狀態。情感認可的缺乏壓倒了對記憶的理性組合。換言之: 邏輯依賴感覺。理性編造出非常複雜的非理性說法,以便解釋情感方面的缺陷。這是“毫無掩飾的大腦活動,艱難地認識外界,病人的大腦無法意識到自身受到疾病的困擾”。
罹患雙重錯覺綜合徵的馬克提供了一面鏡子,讓其他角色(和讀者)反思它所揭示的種種問題。該病患者往往覺得,自己最親近、最珍愛的人已經被人暗中帶走,取而代之的是狡猾的冒名頂替者。讀者看到,馬克本來是一個輕鬆活潑的年輕人,住在這個小鎮上,在牛肉加工廠上班,玩電子遊戲打發時光,對生活不持什麼懷疑態度,人生構圖可謂完整無缺。但是,他後來經歷了內心世界從一瞬間到另一瞬間的不斷破裂。他覺得,他的住宅、愛犬等等已經被人替換,出現在他眼前的一切雖然外表與原來一模一樣,然而不過是複製品而已,甚至整個小鎮也已不再是原來的了。雙重錯覺綜合徵導致他徹底困惑,讓他一度回到原始的混沌狀態,過去的生活支離破碎,感知的一切面目全非,這迫使他對自己的身份基礎、家庭基礎、人生基礎產生疑問。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變成了某種回聲製造者。
小說作者藉助馬克的雙重錯覺綜合徵這一獨特視角,探索了關於人的記憶、人的脆弱性以及人腦的模糊認知活動的問題,引導讀者思考意識、互動性、大腦與自我感覺之間的關係,更深刻地意識到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分裂狀態,理解熟悉與陌生的雙重性,尋覓這種雙重性在人的自我觀與外界關係中產生的無盡回聲。
首先是個人對自我身份的定位。在小說中,包括馬克在內的幾個主角以不同方式,全都經歷了身份認同危機,面對了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例如,卡琳的身份是在尋找關愛對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是,她長期以來都被身份認同問題所困,扮演姐姐這個熟悉角色並未改善她的自我定位感。車禍後,身患雙重錯覺綜合徵的馬克對她的態度強化了這一困局,迫使卡琳在更深層面上尋找自我。與之類似,在深入了解馬克病情的過程中,韋博的自滿心態大受觸動,他開始對原來自我認同產生疑惑,懷疑自己畢生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價值,甚至擔心自己的精神是否處於正常狀態。韋博詳細翻閱了過去歲月留下的碎片,開始淡化原來的自我認同感。他深深感悟:“我們沒有家園,沒有可以回歸的完整自我。自我散布在它觀照的一切事物上,被每一縷變化的光線改變。如果說心靈中沒有什麼東西完全是我們的,至少,我們的某個部分是未受約束的,在與他人的接觸中,吸收所有的一切,別人的迴路通過我們循環。”“自我是一棟熊熊燃燒的房子,在你可能做到時要逃出來。”當然,就身份和意識而言,作品還提出了更深層面的問題,例如,人是否像傳統上認為的那樣,受到大腦——或者說靈魂——的支配?或者說,個體是否受到他人定義的影響?如果這樣的定義改變,個體是否會隨之改變?
其次,這部作品可以促使讀者思考與自我敘事的穩定性和可靠性相關的問題,對大腦和記憶的封閉空間的探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人。面對紛繁變化的世界,人們有時候可能會處於情景性雙重錯覺綜合徵狀態之中——某種短暫的心理斷裂現象。人們是否被鎖閉在自己的敘事之中?成為另一個人,成為另一個物種,成為自我的另一變體意味著什麼?此類思考有助於使人意識到,雙重錯覺綜合徵這類狀態不僅僅是一種病態,可能與人的意識之中某些稍縱即逝的瞬間具有某種相似性。如果我們承認自我的某種不確定性,我們就能在心靈深處為容納他人的敘事騰出一定的空間,這樣,我們可以擁有更多寬容,更多理解。馬克的妄想症給人的感覺是,所有現實都是虛擬的。小說給人啟迪,催人思考: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否可能被人們分享?我們是否可以讓別人相信我們的虛擬現實,相信我們充滿希望的生活計畫?我們是否能夠相信他人的虛擬現實和他們的生活計畫?鮑爾斯看來認為,同情是最高形式的想像力,因為同情需要將我們自己與他人大腦之間的想像連線。
再則,對記憶和自我的反思可以與9·11之後的社會心態聯繫起來。讀者看到,恐怖攻擊和正在進行的所謂反恐戰爭就像影子,在小說角色的心靈中徘徊。“9月來臨,後來出現了多次襲擊。”馬克與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也看到了反覆播放、往往在電影中才能見到的慢動作瘋狂場面。在他眼裡,“紐約是飄浮在遠處地平線上的一片黑色羽毛”。車禍發生之前兩周,馬克報名參加國民警衛隊,“他講話的聲音與往常判若兩人,充滿自豪,更加從容,仿佛他已經是士兵了”。然而,車禍發生了,“他的愛國之旅隨之結束”。在小說末尾,韋博再次發現周圍“瀰漫著濃重的戰爭氣氛”,感嘆“他所屬物種的某種東西已經失去控制”。他覺得馬克說得很對:“與意識的這種不斷消失的行為相比,雙重錯覺綜合徵更真實。”
作品暗示,9·11事件讓某些美國人似乎失去了記憶,拒不承認美國憲法中 “人被上帝創造時是平等的”(或者是“受造而平等的”,而不是有人所譯的“生而平等”)這個理念。美國政府就入侵他國領土的行為提出了稀奇古怪、自圓其說的妄想式辯解。我們可以套用韋博的話來評價這種說法:“沒有自我不自欺。”“自我的整個目標是自我延續。”“撒謊、否認、壓抑、虛談:這些並不是病變,它們是意識試圖保持完整的表現。”如果說小說中的馬克苦苦尋覓的字條作者其實近在眼前,現實中的美國人或許也在尋找已經失去的“自我”,尋找國家締造者們崇尚的價值觀。小說敘述者以諷刺的口吻,用這樣的比喻來描述自我:“我們認為自己是統一的、具有獨立自主地位的國家,神經學卻提示說,我們是盲目的元首,被困在總統套房之內,聽到的只有經過專門挑選的顧問們的意見,而整個國家卻正在特定的動員行動中風雨飄搖……”這一番話顯然帶有別樣用意,讀者很容易將它與現實聯想起來。
美國的“自我”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真正的美國是否已被假冒的美國取代?正如韋博夫人在談到美國企業時所說:“我們生活在群體催眠時代。”原來的美國是否類似韋博在神經學著作中提到的那些幻象肢體一樣,它們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依舊讓人覺得活靈活現?在呈現真實自我——或者在表現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國家身份——的要素中,哪些東西是必不可少的?敘事者借卡琳的之口告訴讀者:“整個人類都罹患了雙重錯覺綜合徵。”
鮑爾斯在談到《回聲製造者》的創作時曾說:“這本書主要探討曠日持久、無法避開、淪入昏亂狀態的過程”,旨在“展示人們試圖形成的關於世界和自我的實在、連續、穩定、完美的敘事的一個側面”。這部作品使人深知,大腦是人體尚未充分開發的部位,我們對它的了解越多,我們發現需要了解的越多。在這一領域中,人類剛剛開始取得實質性進展。人腦是如何形成心靈的?心靈是如何理解其他一切的?我們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自我是什麼?意識的神經相關物在大腦的什麼位置?什麼是真實的?什麼不是虛幻的?綜觀歷史,對此類問題的推測性回答一直令人困惑不解。也許,通過閱讀這部小說,讀者可以找到某些經驗性答案;也許,在聆聽大自然的亘古律動時,我們可以發現一陣陣現實回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