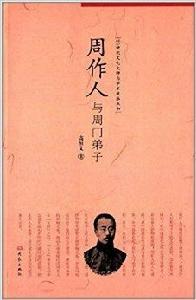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周作人與周門弟子》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高恆文,1962年出生,安徽繁昌人,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天津師範大學教授。出版專著《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東南大學與學衡派》等,發表論文數十篇。
圖書目錄
緒言京派中的京派——一個文學史的命題,一種闡釋周作人的方式
第一章“出家”還是“在家”?——周作人與俞平伯的人生選擇
第二章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第三章《窗》:“人生之藝術化”與“夢的真實與美”——廢名與周作人的人生與藝術的深刻思想共鳴
第四章闡釋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詩”——周作人和廢名對“六朝文章”“晚唐詩”的特殊情懷
第五章“夢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周作人對廢名小說的闡釋
第六章“懷廢名”與嘆知堂——周作人與廢名1937年之後的師生情誼之分析
第七章謝本師:“你也須要安靜”——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係的歷史考察
第八章書信中的故事——周作人與江紹原往來書札箋疏
第九章一種別有意味的對話關係——任訪秋古典文學研究與周作人影響之關係
第十章哪裡來?何處去?——周作人的“五四”文學觀及其與俞平伯、廢名之關係
第十一章“言志”的苦心與文心——周作人1937年至1939年北平“苦住”期間創作之分析
第十二章話里話外:1939年的周作人言論解讀
後記
後記
從開始寫作本書,到今天寫完“緒言”,已經五年過去了。猶記2010年春節南下回故鄉與父母團聚,夜裡在電腦上敲擊鍵盤寫作關於廢名的那幾章的情景。江南的寒冬,恐怕在中國算是最冷的,因為室內沒有暖氣,久坐伏案,愈覺寒氣逼人,但心裡是溫暖的,因為親情,因為對遙遠北國客居之地的眷戀之情。時隔五年,這個春節又是在故鄉度過的,父母身體依然康健,這是最大的寬慰;出版社催稿電郵不斷,我卻感到似乎時光重回,而沒有時間緊迫的壓力。然而畢竟世事滄桑,光陰流逝之中,已有悄然變化,思之令人惘然!當我重回北地,完成“緒言”之際,雖然心中充滿從故鄉帶回的溫暖親情,卻是置身於實實在在的寒冬。
實際寫作時間其實很短,三年前就寫完了主要的篇章。寫作十分順利,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我此前已經開始重新研究周作人,並陸續發表論文。沒有及時出版的原因,在於我事先私自違反叢書規劃,事後又對審稿的修改意見一直猶疑。感謝出版社的寬容,尤其是張前進先生的寬容和耐心,使我避免了違約之失,本書也得以按我原來寫作設計的形式順利出版。
沒有及時出版,竟然因此有時間修改本書的部分章節,在學術刊物和會議上發表。《現代中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學術與文化》《現代中文學刊》《漢語言文學研究》等雜誌,刊發的都是萬字以上乃至將近四萬字的長文,這裡按發表時間再次感謝陳平原、解志熙、喬以鋼、陳子善、孟慶澍諸位。《新華文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人大複印資料”)等雜誌曾先後全文轉載,亦當再次感謝陳漢萍和程光煒、張潔宇諸位。弟子畢婧曾經幫忙核對資料、校對文字等工作,亦當感謝。
本書責任編輯吳韶明先生,春節假日還在抓緊時間審讀書稿,改正文字錯誤,甚至細心核對引文,令人感動;其敬業精神,更令人敬重。 孩子高彌負笈美國留學,這是第二個春節沒有回國,掛念不已!寫作此書的幾年,正是計畫並操辦他留學一切事宜的幾年;一起申請護照、簽證,機場送別十八歲的他第一次並且是隻身去國,宛如昨日!孩子,你的學業、成長,遠比爸爸的學術、工作更為重要!
2014年2月16日,深夜
序言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里,湧現出為數不少的改變歷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出現不僅重塑了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叢書以“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為寫作對象,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在對歷史的回顧中,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叢書可以說是對以師徒關係為中心形成的現代知識群體的研究。中國文化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所謂“道”者,意指“終極真理”“一切的本原”,為師者擔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著“尊師”。現代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土崩瓦解、走向沒落,而新的一切方興未艾、勢不可當。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中,出現了一些為現代中國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開創性的文化大師,他們的出現填補了傳統退位後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為現代人仰慕、尊崇的導師、傳統“聖人”一般的人物。這些大師級人物大都帶有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里斯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馬”一詞,最初用來形容宗教領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後來泛指各類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馬克斯·韋伯認為“克里斯馬”人物以其表現出的某種超凡的品質,“高踞於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馬”現象的出現在其時代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的表現,無論是認為“英雄造時勢”還是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顯的是一種人與時代的互動:一方面“王綱解紐”的時代使這類創世精英脫穎而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銳意求變,率先垂範,成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先覺者、預言家和精神導師,吸引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另一方面,新舊轉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機呼喚著這類人物的出現,以滿足人們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們的心靈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虛、迷茫,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歸宿感。處於由傳統向現代轉換之際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機,人們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體系發生根本動搖,社會亟須一種新的信仰,來重新凝聚散亂的人心,這就為“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提供了眾多的客群和適宜的時代土壤。“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可以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一種導向,進而轉變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使他們“以全新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因此,“克里斯馬”可以表現為一種變革時代的“強大的革命力量”。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迄今共有三種權威類型,它們分別是:傳統的權威、“克里斯馬”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克里斯馬”權威是介於傳統權威和現代法理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的文化現象。
本叢書所包括的文化大師——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穆等大都是在近現代文化學術上創宗立派、開一代風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其中康有為、章太炎兩位是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學兩界的文化大師,對後世影響甚巨。康有為自幼期為聖賢,及長更是以“聖人”自居,不屑於詞章考據之學,而專注於義理之學,養心靜坐。他曾於“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自謂進入了“得道成聖”之境。康有為融會中西,由現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說,在其時代收到了一種石破天驚的破舊立新效果;他積極投身政治、倡導維新變法,並吸引眾多弟子講學論政,其中以梁啓超、陳煥章、徐勤等最為著名,他們形成“康門弟子”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門派,影響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為成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時代變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對象。章太炎則以清末“有學問的革命家”名標青史,他率先倡導民族革命,曾因“蘇報案”入獄三年,出獄之後,革命之志更堅,流亡日本、宣傳革命、聚眾講學,深得進步青年學子的敬仰,在他身邊聚攏了不少傑出人才,其門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成為了其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章太炎的學問“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在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種“究元決疑”的思想家的氣質,以《俱分進化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篇,對時代思潮、人生真諦等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獨特判斷,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至於胡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青年時代的胡適就是一位頗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園春·誓詩》一詞,其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初“發難的信號”。
……
本雅明曾經說過,“所有文明的文獻都同時就是野蠻的文獻”,也就是強調文明與野蠻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時代”為標準,時間並不能將“野蠻”阻斷於過去而在未來造出一個至善無惡的“美麗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發表了他的《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故而至善無惡之境無從達致。歷史樂觀主義的虛妄在於其以對歷史進步主義的信仰放過了對內在於人性深處的“惡”的警覺;以“新舊之別”“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取代了“文明與野蠻”“善與惡”的價值判斷。歷史樂觀主義所持有的線性不可逆的時間觀及源於進化論的人性可臻無限進步論的信念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主導敘事。對這種現代主導敘事的重新審視和反省也是我們今天更為深入地思考現代性問題的必要環節。我們力圖走出那種特定的、單一的、目的性過強的、缺乏距離感的“第一人稱敘事”,以一種更為客觀、多元、審慎的態度來重審、講述中國的“現代百年”,以加深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現實和未來的理解。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學術的進步依賴於一個可以商榷、辯難、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不在於將某種特定時期的特定結論固化為絕對真理,而表現為不斷地證偽與驗錯的過程,在假設與求證、質疑與抗辯中逐漸切近真實,將認識引向深入。從“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人手研究近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叢書的寫作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更為堅實的佳作尚有望於未來。
耿傳明
2010年7月5日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