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去吧,摩西》譜系圖
《去吧,摩西》譜系圖《去吧,摩西》的主人公自然是艾薩克·麥卡斯林。他所屬的麥卡斯林家族是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幾大莊園主家族之一。這部小說就是寫這個家族的兩個支系(白人後裔包括女兒生的“旁系”,以及黑白混血的後裔)幾代人的命運的。所涉及的人物有族長卡洛瑟斯·麥卡斯林的雙生子梯奧菲留斯(布克)與阿摩蒂烏斯(布蒂),當然,還有布克的兒子艾薩克(艾薩克)。“旁系”里有老卡洛瑟斯女兒的外孫麥卡斯林(卡斯)·愛德蒙茲、卡斯的兒子扎卡里(扎克)、孫子卡洛瑟斯(洛斯)。白人人物中比較重要的還有艾薩克的母親索鳳西芭、舅舅休伯特·布錢普。小說的另一人物支系(黑人)姓的就是後面的這個莊園主的姓。老卡洛瑟斯不願讓他與黑女奴(亦即他的女兒)所生的兒子姓自己的姓,這個奴隸只能被稱為托梅(黑女奴名)的圖爾。在圖爾娶了布錢普家的女奴生了孩子後,他的孩子才有了姓——布錢普。而堪稱《去吧,摩西》第二號人物的路喀斯·布錢普就是圖爾的小兒子。而他的妻子莫莉——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福克納家的老女傭卡洛琳·巴爾即是其原型——與外孫賽繆爾分別是“系列小說”的兩篇(前者)與一篇(後者)中的主要人物。為幫助讀者弄清人物之間的關係,譯者特繪製了一張“譜系圖”,附在序言的後面。
《去吧,摩西》寫到的時間,最早的是1859年(追述的部分不算),最晚的則是福克納寫作的“當時”——1941年。大概是:
1859年布克與麥卡斯林·愛德蒙茲去休伯特·布錢普處追捕逃奴托梅的圖爾。布克被扣。布蒂與休伯特打牌,救回布克,並贏得一黑女奴。布克後來娶了索鳳西芭·布錢普,於1867年生下艾薩克。(《話說當年》)
1877年艾薩克十歲。他初次加入獵人的隊伍,進入大森林。(《熊》)
1879年艾薩克十二歲。殺死他的第一隻鹿。法澤斯為他舉行印第安族正式成為獵人的儀式。(《古老的部族》)
1883年艾薩克十六歲。獵人們殺死大熊“老班”。名叫“獅子”的獵狗與法澤斯也都先後死去。艾薩克看家中老賬本,知道了祖先的罪惡。(《熊》)
1885年艾薩克十八歲。他最後一次去大森林中已被賣掉的營地。他悼念法澤斯。(《熊》)
1886年年底,艾薩克去阿肯色州,設法將:1000元給已出嫁的索鳳西芭——路喀斯的姐姐。(《熊》)
1888年艾薩克二十一歲。他決定放棄祖產並搬到鎮上去住。他發現舅舅休伯特贈予的咖啡壺的秘密。(《熊》)
1889年艾薩克結婚。他拒絕了妻子收回莊園的要求。(《熊》)
1895年托梅的圖爾的幼子路喀斯·布錢普二十一歲。他向艾薩克索取應該得到的遺產。(《灶火與爐床》)
1898年扎卡里(扎克)·愛德蒙茲之子卡洛瑟斯(洛斯)誕生,扎克之妻難產死去。路喀斯之妻莫莉去扎克家當乳母。約半年後,路喀斯去“索回”莫莉,後與扎克進行“決鬥”。(《灶火與爐床》)
1906年洛斯八歲。他的種族意識“覺醒”,決定不再與路喀斯之子亨利同吃同睡。(《灶火與爐床》)
1940年莫莉的外孫賽繆爾犯罪被處決。莫莉設法讓其遺體“光榮還鄉”。(《去吧,摩西》)
1941年路喀斯埋藏釀酒器,無意中發現金幣。他迷上挖寶,但最後不得不放棄。(《灶火與爐床》)
1941年艾薩克與洛斯去打獵,他遇見洛斯的情婦,發現她是詹姆士(吉姆)·布錢普——路喀斯長兄——的孫女兒。他看到罪惡循環返回。但他把鑲銀的號角傳給其子。(《三角洲之秋》)
《去吧,摩西》的第三篇《大黑傻子》中的人物、故事均與麥卡斯林家無關。從裡面提到“四五年前路喀斯結婚”一語推定,故事應該發生在1941年。後來,當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問起為何要將這個故事插在這裡時,福克納回答道:因為“大黑傻子和他的妻子租住的是愛德蒙茲的房子”。福克納提供的理由顯然有些勉強。其實這還是出於福克納創作時藝術上的需要。他刻畫了路喀斯·布錢普之後,大概感到言猶未盡,認為總得有一些更悲壯的筆觸,才能全面反映南方黑人生活的圖景。
創作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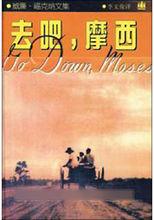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去吧,摩西》
其他版本的《去吧,摩西》美國內戰導致南方歷史的終結。戰後北軍的占領,使南方 經濟和自然遭到了破壞,南方社會得到了解體,但南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著它的南方特性。童年時的福克納仍親眼目睹了南方這個遲暮的“美人”。然而到了20世紀初,情況發生了變化,經過長期的停滯之後,南方重新被帶回到美國以及世界的歷史進程之中,南方經濟逐漸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北方工商業經濟和價值觀念的“南侵”則深刻地改變著南方的農業社會,傳統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也給南方美麗的自然環境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去吧,摩西》記錄下了現代人對傳統的背棄和對自然的瘋狂掠奪,同時也寄託了對南方深深的思念。
作品評析
主題
《去吧,摩西》主題是美國南方的種族關係,但是其中有三篇作品即《古老的部族》、《熊》和《三角洲之秋》卻是側重寫打獵的,人稱“大森林三部曲”。這裡又接觸到一個人類怎樣對待大自然的問題。而艾薩克正是在打獵的過程中,學會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於是,接下去他作出了捨棄有罪惡的祖產的決定。他認為世界應該“在誰也不用個人名義的兄弟友愛氣氛下,共同完整地經營”。然而我們不應認為艾薩克即是福克納。福克納並不認為放棄祖先罪惡的遺產就是問題的終結。從《三角洲之秋》中所寫老卡洛瑟斯的罪孽在後代的身上重新出現,也可以得到證明。此外,福克納在1955年答覆一個訪問者時說:“我認為一個人應該比捨棄做得更多。他應該有更加積極的行動而不能僅僅躲開別人。”接著福克納列舉了自己作品中更加積極的人物,如《墳墓的闖入者》(1948)中的加文·史蒂文斯以及他的外甥。而這個加文·史蒂文斯也就是《去吧,摩西》這篇作品中幫助莫莉大嬸的那位律師。
在《去吧,摩西》中,麥卡斯林家族,如同福克納的家族以及他的其它重要的小說中的人物的家族一樣,有著傳奇式的輝煌的歷史。老卡洛瑟斯和其他拓荒者一樣,從印地安人那兒獲取土地,歷盡艱險,在這片荒蠻的土地上建立了秩序和文明。後來這些家族和南方一樣隨著內戰的結束都衰落下來了。傳奇式的富於浪漫色彩的南方和輝煌的家族史讓福克納無比珍惜,也成了他抗拒粗魯的暴發戶式的北方佬的有力武器。南方社會中所特有的貴族特徵同樣深深吸引了福克納。在《熊》中,愛扎克放棄了財產既是對其先人罪孽的一種救贖行為,也體現了他捨己為人與慷慨的行為,是福克納筆下的美國南方的貴族階層的倫理法則之一。此外,德史本少校邀請獵人參加他的狩獵的行列,分享獵物。胡伯特送給愛扎克,後來又自己盜去的那隻銀杯和金幣,後來麥卡斯林·愛得蒙茲居然自願承擔這筆債務的償還,也說明了這種貴族風度。同樣的風度出現於狩獵的營地上。在那裡,半個月之內,城市裡的一切社會階級觀念,暫時完全被擯棄,所有的人不分尊卑貴賤,生活在一種平等的同志氣氛中。“這些人就像亞瑟王的圓桌武士從來不會缺乏應有的殷勤和禮貌。”
不難看出,《去吧,摩西》一書雖然篇幅不大,卻提供了一整個時期的歷史畫面,概括地反映了美國南方最本質的一些問題。用福克納自己的話說,這裡的故事是“整片南方土地的縮影,是整個南方發展和變遷的歷史”。《熊》里也寫道:“這部編年史本身就是一整個地區的縮影,讓它自我相乘再組合起來也就是整個南方了。”作者採取了“系列小說”的形式,這樣就可以捨棄一般交代性的筆墨而集中經營戲劇性強烈、詩意濃郁的場面,從而獲得一種史詩般的效果。在人物塑造上,這本書一方面刻畫出艾薩克·麥卡斯林這樣的形象,他代表了白人的良知,另一方面又讓我們看到了路喀斯·布錢普靈魂的深處。他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憑藉自己的不屈不撓與聰明才智生存下去的黑人的代表。福克納一直認為黑人很頑強,他們是能夠生存下去並且最終得到自由的。書名的典故也透露了這層意思。
除了慷慨之外,南方人還仿效英國的貴族階層,表現出一種騎士風度。在《話說當年》中,布克兄弟為了追回逃跑到休伯特莊園的托梅的圖爾卻被休伯特兄妹所困。布蒂與休伯特打牌作賭,布蒂贏牌,救出了布克,並贏回了圖爾所愛的女奴。這是典型的南方貴族的見義勇為,豪爽的騎士風度。南方的生活方式也使福克納沉湎其中。他在 《去吧,摩西》中一再加以表現。首先是種植園生活。種植園生活富足而又愜意。在《話說當年》中,赫伯特·布香的大房子後樓有一處地方地板朽壞了,布香始終沒有把它修好。客人總是發現他坐在底下流著泉水的冷藏室里,脫了鞋把腳浸在水裡,一邊啜飲早晨的第一杯酒。種植園生活舒適,僕役成群。但在文章中,福克納沒有大擺闊氣的場面;沒有對絲綢,銀器,家具,月光與香檳酒的大肆渲染的描寫。福克納描寫南方的生活方式,並不是他喜歡南方的財富、良田和華宅,而是他欣賞南方人身上特有的那種對待生活對待人生的態度。其次E 狩獵也是南方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年一次的相會……每年一次慶祝老熊狂暴的不朽的盛典。”早期的拓荒生活和莊園生活使南方人身上有一種親近大自然的浪漫主義傾向。狩獵成了南方人的一種傳統。在《熊》里的狩獵中,白人、紅人和黑人不分等級,種族平等地生活,和諧共處。他們狩獵不時為了殺生取樂、獲利或是炫耀武力;捕獵是他們磨練意志,增加智慧,完美性格的活動。南方人對狩獵生活是無法忘懷的。《三角洲之秋》就講述了快80歲的艾扎克大叔依然不顧年事已高,帶著曾孫去打獵的故事。
另外,福克納還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與現代社會截然相反的南方傳統的價值道德觀。“現代世界是在道德混亂之中。它確是苦於缺乏綱紀、法度,缺乏道德標準和負有某種使命的責任感。在這個世界裡凡是能圖私利、行得通、獲得成功的就是標準。”在這篇小說集裡,作家向我們展現了南方的一系列美德。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令人十分討厭的人物,就連因殺人而被判了死刑的布錢普也是一個令人同情的角色。這些都是南方的傳統美德,也正是北方人所缺乏的。正如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所說的,是要“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是人類昔日的榮耀”。
福克納對故鄉有著深深地熱愛。小時候,他經常由父親帶著到森林裡打獵、釣魚和騎馬。這塊土地生長,養育了他。他和同時代別的作家都不一樣,他選擇故鄉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在那裡,南方種植園之外的是莽莽原野。隨著北方的南侵,北方人和南方的新貴們藉助機器對荒野進行了瘋狂的毀滅性的掠奪。在福克納的記憶里,“那些高高大大的,無窮無盡的十一月的樹木組成了一道密密的林牆,陰森森的簡直無法穿越。”在莽莽蒼蒼的荒野中讓福克納最不能忘懷的是動物。不管是追逐的獵狗還是被追逐的熊,鹿或者松鼠,個個靈性十足。“這些動物混雜在一起,像浮雕似的出現在荒野的背景之前,它們生活在荒野里,受到荒野的驅使與支配,按照古老的毫不通融的規則,進行著一場古老的永不止息的競爭。”它們是森林的主宰。在作家的筆下,它們是完全可以和最優秀的人類相媲美的一群高貴的人;它們仿佛是從童話書中走出來的住在森林中的一群精靈。現代人對自己的同類都瘋狂地殺戮,更不用說對森林中的動物了。現在森林正日益消退,動物的棲身之所越來越小;許多動物都不見了,連剩下來的松鼠和母鹿也無法幸免於難。《三角洲之秋》中的洛斯,雖然是個南方人,但他沾染了現代人所固有的習性,連母鹿都捕殺,無異於竭淵而漁。動物和森林在機器的轟鳴聲中正在永遠地消失著。福克納明白這塊土地是受了詛咒,是注定要滅亡的。福克納對南方自然的描繪逼真傳神,任何企圖評述他對故鄉的熱愛之情的文字都顯得蒼白無力。作家對故鄉的描述越是逼真傳神,就越是襯托出他對故鄉的熱愛之情,也越是體現出他的哀輓之情。
手法
短篇的統一性
福克納在領諾貝爾文學獎時曾經說過,文學家的使命就是去描繪那些掙扎於困境中的靈魂。 因此,在《去吧,摩西》這部由七個不同內容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構成的長篇中,福克納關注了一群陷入不平等種族關係困境中掙扎的靈魂。 這裡有《話說當年》中的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有《灶火與爐床》中的路喀斯,有《大黑傻子》中的賴德,還有《古老的部族》、《熊》、《三角洲之秋》中的主人公艾薩克,《去吧,摩西》中的加文·斯蒂文斯。這是一群掙扎在黑白人種關係困境中的人物。他們努力地與不平等的人種關係抗爭,他們的抗爭又是那么的悲壯。在《去吧,摩西》這七個彼此相關、相互聯繫的短篇故事中,為我們講述了美國南方從1859-1949年將近一個世紀的家族種族故事,以麥卡斯林家族作為敘述的主線,描述了麥卡斯林家族中過去古老的白人與生活在現代的白人之間的矛盾,麥卡斯林家族中的白人成員與家族以外的白種人之間存在的矛盾衝突, 還有麥卡斯林家族內部的黑人與白人、黑人與家族外黑人之間不平等的矛盾存在。
《去吧,摩西》之所以在最初的時候,被大家當作短篇小說來審視,是由於其脫離了具體的關於種族主義的大的解讀語境。 失去了這一種族主義的解讀語境,《去吧,摩西》中的這七部短篇小說就完全可以作為自足的短篇來閱讀。因此,才有了作品開始面試時的誤讀。《去吧,摩西》七個構成部分的排序獨具匠心,具有長篇小說結構的內在統一性特徵。在長篇小說《去吧,摩西》中,福克納獨具匠心地將《話說當年》放在了開始的位置,作為追溯故事的歷史,並且為整部長篇小說的敘述設定了深厚的背景。
《話說當年》的故事不僅僅只是講述了一件美國內戰發生之前的事情,它還涉及了當時美國社會極為敏感的南北美戰爭的矛盾中心,那就是種族問題,奴隸制度。在故事講述的時候,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度還沒有被戰爭的硝煙沖毀,黑人奴隸還被白人莊園主像狗一樣追來追去,並且作為自己個人的私有財產欲奪欲殺,就是《話說當年》中的女奴譚妮·布錢普,一場隨性的撲克牌賭博,就可以將她的命運決定。 福克納將這部以美國內戰開始之前、充滿了矛盾衝突的種族問題作為整部長篇故事的歷史背景,為面其他六部短篇小說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黑人奴隸、種族平等的問題設定了開闊的背景,同時,在這樣一個大的充滿社會矛盾的歷史背景下,小說的人物命運也就在這裡巧妙地埋下了伏筆。
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種族社會矛盾的歷史背景下,長篇小說《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心理才有了關於自己人種問題的糾結與矛盾,就如路喀斯·布錢普,他一方面鄙視著純正的黑人血統,為自己血脈中流淌的白人血液而驕傲,同時,另一方面迴避著自己這種介於黑白人種之間的混血血統。 其實,這不僅只是路喀斯·布錢普一個人的矛盾糾結, 更是當時美國社會整個人種的糾結。 面對著不平等的種族關係,面對著地位懸殊的黑白人種間的主僕關係,對於作為主人的白色人種中有良知的人,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拷問靈魂的糾葛。 就如《去吧,摩西》的主人公艾薩克,作為美國南方莊園主,面對著自己莊園中掙扎的奴隸,他的思想與靈魂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糾纏中,以至於後來只好以放棄繼承財產作為自己解決人種矛盾的方式。 其實,這並不是美國南方種族問題解決的真正核心所在。
福克納這部關於結構充滿爭議的長篇小說《去吧,摩西》,最終以其精心地謀篇布局、宏大的人文主題而使其結構的鬆散性與統一性在敘述中得到了平衡。 大的種族主義問題將七部鬆散的短篇小說統一在自己這一主題框架中,而七個鬆散的短篇小說,又從不同的角度對於曾經困擾了美國南方幾百年的種族問題進行了探討與敘述,進而使這部被世人認為結構鬆散的長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張力。
人物命名
《去吧,摩西》中故事名稱、人名,地名等命名藝術主要是基於聽覺,讀音,形態,語義,以及文學或神話典故的聯繫體現出來的,也體現出作者追求命名藝術的苦心孤詣。
作者還很好地運用了形態學聯繫來進行人物命名。形態學是指對單詞構成的研究與描述,單詞構成包括詞尾變化,派生與合成等。《去吧,摩西》中備受大家尊重,教會“Isaac”(艾薩克)打獵,並執行成年禮儀式,被“Isaac”視為精神之父的“Sam Fathers”(山姆·法澤斯),他的名字來自於“father”的複數形式。在古老的部落中,作者介紹了山姆有兩個父親: 一個是印第安人,另一個是黑人。而山姆從其父母那裡繼承的紅、黑、白三種血統使他具備了忠誠、忍耐、謙虛、仁愛等優秀品格,這令他更加有資格來執行艾薩克的成年禮儀式 。同時“Sam Fathers”這個名字暗示了血統的多樣化,從而體現出作者對南方有全面的認識,也傳遞出作者的意圖。因為“Sam”是暗指美國(山姆大叔)。美國是個文化多元,不同膚色,不同種族聚集的國家。所以福克納也認識到無論是在南方,甚至在美國,不同膚色一起生活這個現實是不可改變的。作為精神之父的“Sam Fathers”的多血統本身也以包容性和多元性而個性鮮明。“Tomey's Turl”(托梅的圖爾)的名字也直接反映了他的身世。老麥卡斯林與自己的黑人女兒“Tomey”(托梅)亂倫後生下了兒子,但是老麥卡斯林並沒有承認他這個黑人兒子。所以兒子的名字說明了他是母親“Tomey”的,而不是“Parent's Turl”。作者通過“Tomey's Turl”這個名字刻畫出一位被父親拋棄的孩子,由此讓讀者心生憐憫。而大黑傻子中的Rider”這個名字也是由“ride”後面加“er”構成。“Rider”的字面意思是騎兵,這也正與“Rider”(賴德)在故事中的表現相吻合。故事中的Rider”身高體壯,豪放不羈。在面對多年作弊欺騙自己和黑人的白人“Birdsong”時,他就如騎兵一樣把這位黑人的敵人一瞬間結束在自己的剃刀之下。但是與“Rider”的形象形成了對比的就是熊這個故事中的人物“Brownly”。“Brown”不用作專門名詞時,表示棕色,所以一方面作者採用了該辭彙中的顏色與人物相聯繫起來的,因為文章中的“Brown”就是一個有色人種。另一方面作者拿“Brownly”與美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廢奴主義者“John Brown”相類比。“John Brown”為了解放黑奴曾在哈勃渡口舉行武裝起義,後被處死。“Brownly 是在“Brown”的基礎上加”ly“來構成的,那么“Brownly”也就意為像布朗那樣的暴力反抗壓迫的人。但是在“Buck”和“Buddy”的文字記載中,“Brownly”是一個既不會計帳寫字,也不會犁地,甚至連牲口在他手裡都會出事的一位黑人。這讓“Buck”(布克)和“Buddy”(布蒂)損失不小,但他們又拿“Brownly”沒有辦法,最後只好給予“Brownly”自由。所以“Brownly”是一位與前面的“Rider”和“John Brown”有區別的一位黑人,他是採用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而獲得自由的典型。
作品影響
在《去吧,摩西》中,福克納通過七個短篇小說,向我們如實地講述了南方往昔的榮耀和傳統;向我們精心描述了散發著濃郁鄉土氣息的他所愛所恨的南方的歷史畫卷。這是一個與現代社會截然相反的世界。然而, 福克納傾心所愛戀的那個南方已離他遠去。痛苦與快樂,希冀與幻滅,懷戀與憤慨在他的心中交織在一起,使他呤唱出了一曲南方悽美的輓歌。這些故事是“整片南方土地的縮影,是整個南方發展和變遷的歷史
相關典故
 摩西
摩西黑人靈歌所提到的摩西(來源於希伯語:מֹשֶׁה),天主教稱為梅瑟,伊斯蘭教稱為穆薩,他的名字在希伯來 語的意思是:從水裡拉上來。因為當時摩西還只是一個嬰兒,被裝在籃子裡,法老的女兒把摩西從水裡救了出來,所以為他取了這個名字。
摩西是先知中最偉大的一個。他是猶太人中最高的領袖,他是戰士、政治家、詩人、道德家、史家、希伯來人的立法者。他曾親自和上帝接談,受他的啟示,領導希伯來民族從埃及遷徙到巴勒斯坦(PALESTINE),解脫他們的奴隸生活。他經過紅海的時候,水也沒有了,渡海如履平地;他途遇高山,高山讓出一條大路。《聖經》上的記載和種種傳說都把摩西當作是人類中最受神的恩寵的先知。
摩西最享盛名時期很可能是公元前十三世紀,因為普遍認為《聖經·出埃及記》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於公元前1237年。一百年以後,穆罕默德認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摩西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裡(甚至包括埃及)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到公元後五百年,他的名氣和聲望同基督教一道傳遍歐洲許多地區。摩西在他死後三千多年的今天,仍同樣受到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還受到許多無神論者的尊敬。
作者簡介
 威廉·福克納
威廉·福克納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出生於沒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在加拿大空軍中服役,戰後曾在大學肄業一年,1925年後專門從事創作。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寫傑弗生鎮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沒落及成員的精神狀態和生活遭遇的《喧譁與騷動》(又譯《聲音與瘋狂》1929);寫安斯・本德侖偕兒子運送妻子靈柩回傑弗生安葬途中經歷種種磨難的《我彌留之際》(1930);寫孤兒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種族偏見的播弄、虐待下悲慘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寫一個有罪孽的莊園主薩德本及其子女和莊園的毀滅性結局的《押沙龍,押沙龍!》(1936);寫新興資產階級弗萊姆・斯諾普斯的冷酷無情及其必然結局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鎮》1957,《大宅》1959)等。福克納在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