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光山縣弦南區第五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弦南區蘇維埃主席、區委書記兼郭家河便衣隊指導員,中共經扶縣(今新縣)縣委書記,鄂東北道委秘書,中共羅(山)禮(山)經(扶)光(山)中心縣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經扶縣委書記,禮山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羅(山)禮(山)經(扶)光(山)中心縣委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經光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羅禮經光中心縣委書記,中共經扶縣委副書記兼縣長,鄂豫區第二專署專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河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監委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省三、四屆政協副主席,省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游擊戰爭時期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紅二十五軍北上長征,離開鄂豫皖蘇區,國民黨調集數十萬大軍“進剿”根據地,蔣介石嚴令其總指揮梁冠英要將鄂豫皖的紅軍“完全撲滅,永絕後患,徹底肅清,以競全功”。國民黨部隊及地主民團、還鄉團在鄂豫皖邊界地區實行大規模的搜山倒林、移民並村、強化保甲制,實行“五家連坐”等辦法,叫囂“車盡塘中水,挖盡共產根”。鄂豫皖蘇區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1935年7月,劉名榜被任命為中共經扶縣(今新縣)縣委書記。他領導新縣黨組織和人民民眾進行反“清剿”鬥爭,為紅軍籌集給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同年8月,中共鄂東北道委書記王福明因病被俘,被光山縣反動民團團總黃善安活埋。黃善安殺人如麻,對紅軍傷病員剖腹挖心,無惡不作。一天傍晚,劉名榜得知黃善安獨自在外過夜,率便衣隊包圍了他的住處,處決了黃善安,打擊了敵人的猖狂氣焰。為深入發動民眾,劉名榜採取“敵上山,我下山”的鬥爭方法,將便衣隊化整為零,與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並調查保、甲長的活動,摸清敵人動向,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不久,他率領便衣隊又消滅了夏家寨反動民團。為紅二十八軍籌積了大批給養,輸送了大批青年參加了紅軍。後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到達鄂東北,表揚他對敵鬥爭的方法。不久,他就擔任了中共羅(山)禮(山)經(扶)光(山)中心縣委書記,領導鄂豫邊區的革命鬥爭。三年游擊戰爭中,劉名榜領導鄂豫邊區的廣大軍民堅持武裝鬥爭,保證了大別山革命火種不滅,紅旗不倒。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持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同年9月,劉名榜率中心縣委機關和便衣隊到達七里坪待命整編。同時,他正確執行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致函國民黨經扶縣長鬍光祿:“值此日寇犯我河山,民族危亡之際,若同室操戈,豆箕相煎,實乃中華民族千古罪人。要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前怨。”胡光祿在民族利益前面也回信劉名榜,對我前往改編的便衣隊已通知沿途各保迎送貴軍,安排食宿。
1938年1月,新四軍成立,3月,四支隊開赴抗日前線。地方黨組織領導人鄭位三、田東、何耀榜、劉名榜、羅厚福等人組成了四支隊後方留守處,劉名榜任留守處副主任。留守處的任務是:為四支隊提供兵員、物力、財力和收容傷病員。劉名榜到達郭家河、白馬山、卡房一帶開展工作,恢復了黨的組織,重建了中共經扶縣委。為支援四支隊前方作戰,恢復民眾生產,劉名榜與國民黨縣政府協商,在卡房古店成立了聯合辦事處,動員民眾回鄉生產,重建家園。之後,在整個八年抗戰時期,劉名榜一直沒有離開過鄂豫皖根據地,使我黨在這裡始終保持著一支武裝力量。特別是到了解放戰爭初期,他和他的游擊隊,再次處於一個極其艱難困苦的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
 劉鄧在大別山上
劉鄧在大別山上1947年8月27日,劉鄧大軍前衛兵團到達大別山。28日,劉鄧大軍第六縱隊十八旅五十二團一營、五十三團一部包圍經扶縣(今新縣)縣城——新集,敵民團武裝千餘人依仗地形負隅頑抗。劉鄧大軍利用密集炮火猛攻,下午4時攻入城內。當時,羅(山)禮(山)經(扶)光(山)中心縣委及其領導的游擊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緊緊依靠根據地民眾,堅持戰鬥在大別山區。當得知劉鄧大軍攻克經扶縣城後,游擊隊員們欣喜若狂。
與此同時,一縱隊在經扶縣西部一帶實施戰略展開,發動民眾,開展地方工作。8月29日,一縱隊到達大別山,由光山縣晏河進入經扶縣吳陳河,在吳陳河召開會議,研究開展地方工作的計畫。會議決定: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率一、二旅為第一梯隊擔任機動指揮作戰的任務;參謀長潘焱率二梯隊帶一個警衛營和炮兵部隊及後方機關進到陡山河、郭家河、檀樹崗地區,開展這一地區工作,並聯絡地方黨和當地游擊隊。之後,潘焱率縱隊直屬隊、後方機關及炮兵部隊沿陡山河、油榨河進至郭家河,在那裡發動民眾,建立根據地。在此,潘焱與堅持在大別山鬥爭的游擊隊負責人劉名榜聯絡上了。兩人一起檢查地方工作,看到沿途民眾發動起來了,很滿意。
29日夜晚,羅禮經光中心縣委書記劉名榜帶領30餘名游擊隊員去經扶縣城和大軍匯合。31日上午,在黃安縣火連畈附近一個叫黃石沖的村子裡,六縱十七旅旅長李德生接見了劉名榜。李德生把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戰略意圖向劉名榜作了介紹,劉名榜把中原突圍以後游擊隊堅持大別山鬥爭的情況及大別山地區的敵情作了較詳細的匯報。李德生說,我聽中央有人說到你,知道你這個人一直堅持大別山區的革命鬥爭。
9月2日晚,鄧小平對民運部長穰明德說:“你已經知道了,我們要在這裡安家落戶,下決心不走了。我們要把經扶縣作為第一個立足點,希望你能在這裡站穩腳跟,堅持下去。這裡曾經是鄂豫皖蘇區的中心,現在仍有游擊隊堅持鬥爭,這是很不容易的。游擊隊負責人叫劉名榜,但他有多少人、多少槍都不清楚。現在就要靠你這個民運部長去找了。你去經扶縣,公開身份是縣長,實際上是縣委書記兼縣長。到新集鎮後,你要馬上出安民布告,建立起民主縣政府,立即開展工作。”
9月3日,穰明德帶近百人進入新集,張貼布告,宣布成立經扶縣愛國民主政府,縣長穰明德。因敵情緊張,當天,穰明德即率隊撤離新集進入西大山。次日,一位在延安抗大二大隊學習過的同志把穰明德帶到經扶縣郭家河地區,在一個靠山的老百姓家裡找到了劉名榜。穰對劉說:“你當縣長,我只當縣委書記。前些時,我以縣長名義出了安民告示,安了民。現在找到了你,我這個縣長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以後就由你來當縣長了。”
9月10日,劉伯承和鄧小平在光山縣南向店附近的西楊崗接見了劉名榜、邱進敏等人,對堅持大別山鬥爭的99名游擊隊戰士表示親切的慰問和勉勵。劉伯承看著大家面黃肌瘦的臉色,親切地說:“你們能堅持到現在,是多么不容易啊!快去洗洗澡理理髮,再好好地休息兩天,一切都給你們安排好了。”鄧小平親切地握著劉名榜的手說:“老劉啊,你們是怎么活過來的?不容易啊!”劉名榜把在大別山堅持鬥爭的情況向劉、鄧作了匯報。鄧小平既高興又嚴肅地說:“對,我們離了黨的領導,活不成!離開了人民,離開了槍桿子,更活不成!”他接著說:“你們都是黨和人民的好戰士,我代表野戰軍的領導同志,向你們表示感謝!”鄧小平還特意讓人殺了一頭豬來招待游擊隊員。
吃罷午飯,野戰軍司令部要游擊隊為部隊保存一批重要物資。這批物資是:100多匹騾馬,10多匹騾子馱的銀元,5匹騾子馱的煙土,還有一大批中州票和冀南票及一門大炮,彈藥等。當時,隨大軍南下的彭曉林任經扶縣政府財政科長,記下了這批物資的具體數目。隨後,穰明德被正式批准任經扶縣委書記,劉名榜任縣長。
從光山縣南向店回來後,縣大隊從後勤部隊手中接收了這批物資。劉名榜和邱進敏他們花了七八天的時間,才把這批物資埋藏好。9月底,敵人對大別山實行重點“圍剿”時,到處查找這批物資。儘管敵人用盡各種方法,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線索。解放軍主力轉回後,經扶縣委、縣政府將這批物資完璧歸趙。
被遺忘的五更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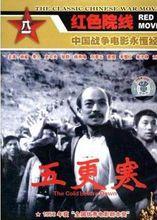 《五更寒》
《五更寒》一個普通農民出身的共產黨人,在土地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在人們難以想像的艱苦環境中,任一個縣的領導達20年之久,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於是,在50年代中期,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著名導演嚴寄洲,以劉名榜為原型,將他的事跡拍成電影《五更寒》。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五更寒》電影正式上映,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他,稱他是“堅持大別山鬥爭的一面紅旗”。可是,《五更寒》這部電影,後來卻遇到了不小的麻煩,屬於比較早就被“極左”思潮否定的影片之一。 《五更寒》劇本是著名部隊劇作家史超在大別山地區親身經歷一段鬥爭生活寫成的。一聽片名就很吸引人,那是摘取了南唐後主李煜寫的《浪淘沙》中詞句:“羅衾不耐五更寒”中後三個字點題,其含義頗為含蓄深遠。《五更寒》描寫的是1946年期間,李先念率領的五師撤離了大別山地區後,留下一支武裝小分隊堅持和數量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作鬥爭的故事。小分隊的戰鬥員們不但要同敵人鬥爭,還要和飢餓和寒冷鬥爭,劇本中展開了一個個極為感人的故事情節,看了令人神往,令人激動,嚴寄洲為之傾倒。
嚴寄洲曾撰文提到:在慶祝中國電影百年華誕期間,一些電視台及報刊雜誌紛紛前來採訪或約稿,要我談談過去導演的一些片子。儘管我一生中執導的片子不少,可是來訪者總讓我談《野火春風斗古城》《英雄虎膽》《海鷹》《哥倆好》等幾部炒了又炒的老片,奇怪的是我早期執導的一部我自認為思想內容、人物塑造、故事情節都還不錯的片子,長年來卻無人問津,成了被遺忘的角落。這部片子名叫《五更寒》,拍攝於距今已經半個世紀的1957年,是我從事電影導演工作以來執導的第四部故事片。
影片投產後,嚴寄洲和選定的主要演員楊威,史可夫、曹櫻、李雪紅、楊秀清、劉季雲、李力、曲雲、黃煥光和周鳳山等,由劇作家史超親自引導,浩浩蕩蕩前去大別山地區體驗生活。他們先到了信陽和開封,史超特地邀請了當年在大別山鬥爭中劉書記的原型真的劉書記一同前往。
進了大別山地區,但見層巒疊嶂,高崖險峻,正是開展游擊戰的理想地形。他們先後到了當年與敵人武裝鬥爭最激烈的光山縣、新縣和黃安縣(今更名紅安縣)一帶,與當地老百姓同吃同住體驗生活。山里老百姓見到當年共同鬥爭的老劉書記回來了都非常親切,熱情接待我們,這給我們體驗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有利條件。尤其是扮演劉書記的楊威更是和真劉書記朝夕相處,談心說憶,仔細揣摩他的舉止言行以及他和民眾親密無間的魚水之情。演員們在生活中加深了對角色的理解。
大別山地區老百姓的生活還是非常艱苦的,他們三天兩頭需要爬山越嶺到當年的鬥爭現場深入觀察和體驗,和老百姓同吃一樣的粗茶淡飯,住一樣透風的房屋。演員們則紛紛找自己扮演角色近似的老鄉一塊兒幹活聊天。更忙碌的是美工師徐潤等人到處速寫具有大別山特有風貌的草圖,服裝道具組的同志則蒐集購買各種道具和老百姓已經不穿的破衣爛衫,因為這些服裝道具靠仿造是很難有真實感的。
根據廠里的調度計畫,拍攝的時間正是盛夏季節,可是這段時間恰逢大別山地區的雨季無法拍攝外景。美工師徐潤解放前在上海做電影美工,很熟悉各處景地的特色,他建議到蘇州木瀆鎮的天平山去看看,除了建築外那裡很像大別山。嚴寄洲當即率領主要創作人員來到天平山,果然這裡峰迴路轉,古木參天,很像大別山的風貌,於是決定把大別山搬到天平山來拍攝。
《五更寒》的拍攝是異常艱苦的,當烈日炎炎氣溫達到三十七、八度以上時,我們還必須冒著酷暑突擊拍攝,每個人都是揮汗如雨,不少人還長了痱子痛癢難忍。我們攝製組住的是一座祠堂和一座大廟。晚上蚊子到處施虐,我們部隊發的蚊帳透氣不暢,不掛又不行,不少人只好抱著草蓆到通風較好的公路大橋上睡覺。由於天氣炎熱,廠里通知給攝製組全體演職員每天報銷降溫費一角錢,對此大家非常滿意。那時拍電影,既無獎金和生活補貼,還要自個兒掏一伙食費和糧票。
在天平山拍攝外景的時候是如此酷熱,可是等到返廠後待要拍攝內景的時候已經是秋涼季節了。這一天,要在攝影棚內搭制的一座貧農王太家小院子內拍攝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劉書記拄著一根樹棍,蹣跚地來到遍地污水的院內,想敲開這個基本民眾的屋門。此時,劉書記已經三天滴水未進了,飢餓和寒冷襲擊著這位可敬的拐腿老人。當時北京氣溫已經很低了,加上又是深夜、我擔心老演員楊威的身體吃不消,不斷催促給攝影棚加送暖風。怎奈攝影棚太寬大,一時半刻很難升溫。此時,楊威身穿破爛不堪的衣衫,肩上披著麻布片走到我面前對我說:“嚴導,來吧!當年大別山鬥爭比現在更苦。”嚴寄洲一聽激動地下令開拍,但見人造雨傾盆而下,陣陣滾雷聲中一道道閃電照亮了劉書記的身影,他蹌踉地走進滿地積水的破院……鏡頭一個一個拍下去,大約拍了三個多鐘頭。嚴寄洲問:“老楊,頂得住嗎?”楊威高興地對我說:“嗨!太好了,太好了!這冷水一澆,把我的感覺全都給澆出來了。”此時,劇務端來兩個饅頭和一小碟鹽蘿蔔給楊威吃。劇務笑對我說:“老楊為了拍這場劉書記餓了三天的戲,今兒晚飯都沒有吃,他說要找出飢餓的感覺。”
《五更寒》終於攝製完成後,八一廠很重視這部影片,還專門出了畫冊,在全國公映之後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各種報刊雜誌紛紛撰文褒揚這部影片,電影文學劇本獲得了電影局優秀電影文學獎,並出版了專集;影片選人了“中國電影周”放映,還製成了連環畫冊。
讚揚者主要稱頌這是一部充滿了革命激情的影片,歌頌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品德。影片真實生動而又富於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成功地塑造了以縣委劉書記為首以及羅文川、巧觀、南國祥、穆英、勞良才、王太等一批革命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曲的光輝形象。一位影評家激動地對我論“別人拍一部影片,總希望劇中有英俊的男主角和靚麗的女主角。可是你這部影片中,卻偏偏以一個年老體弱,而且還瘸了一條腿的瘦老頭子當主角,真是勇氣可佳。”
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我們為影片獲得社會好評而欣喜之時,突然一陣陰風吹來,報刊上開始出現了一些批評文章。《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還設專欄進行不同意見的討論。批評的意見主要都集中在那個特殊人物身上,那個貫串全劇的寡婦巧鳳。批評者指出巧鳳輕佻風騷,是一個不知羞恥的地主小寡婦,她同情和幫助游擊隊是不真實的,是顛倒了階級關係,創作者把她作為一個革命者來描寫是原則立場上的錯誤。
本來批了一陣也就偃旗息鼓過去了,偏偏此時突然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總政文化部創作員寧乾為巧鳳抱不平,寫了一篇為巧鳳辯護的文章,立即引來了鋪天蓋地的反駁批評。
其實影片中說得清清楚楚,巧鳳的家庭出身是窮苦人家,她是被迫嫁給了一個地主的兒子,偏偏這個地主崽子不久便嗚呼哀哉了,於是她便成了地主小寡婦。劇作家賦於她的特徵是舉止妖冶放蕩,說話伶牙俐齒,可是她心裡善良,憎愛分明。她嫁給地主兒子是迫於無奈,她本來熱愛的情人是參加了游擊隊的羅文川,因而她對這支部隊有一種樸素的感情,本能地願意冒著風險幫助他們。這個人物既不落俗套而又性格鮮明,今天看來是無可非議的。據我所知,史超塑造這個人物是有生活原型依據的: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史超和另外幾個同志和敵人周旋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時刻來到深山一戶人家敲開了門,戶主是一個素裝的年輕寡婦,她一見是自己的同志,連忙燒火做飯,史超還和她聊起了身世,後來我們到大別山體驗生活時,史超還專門為我引見了這個同情革命的女子。
然而在那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卻沒有可申辯的。有文章斷言:她既然嫁給了地主兒子,她自然應該算作作地主階級,而地主階級自然就是階級敵人。根據這個邏輯,巧鳳不可能同情革命,不可能為游擊隊打掩護,更不可能給游擊隊提供情報。所以,《五更寒》中描述的這些情節全都是虛假不真實的,巧鳳這個人物是無本之木,無根之浮萍。再聯繫到劇中的縣委組織部長莫文階變節叛變了,一上綱、一上線,啊呀!這還了得,黨的幹部投敵叛變,地主寡婦傾向革命,編導者的立場站到哪兒去了?
看到這批評文章,我心中十分困惑,而且難以接受。影片中的巧鳳言行舉止放蕩不羈,那是由於她的母親是個媒婆,耳濡目染使她外表上看似玩世不恭,可是她的內心卻是飽嘗辛酸。應該說劇作家擺脫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羈絆,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
從此以後,這部所謂大毒草影片便被打入冷宮不得再上映了。而且每到什麼運動一來,《五更寒》這隻死老虎首當其衝,便要拿出來敲打一通,我也難免要“觸及靈魂”的“深刻”檢討一番。不過那時候的批判總算還是“和風細雨”,不打不罵,臭臭你罷了。後來到了那個“史無前例”令人觳觫的“十年大革文化命”(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可不一樣了。那位“旗手”江青罵《五更寒》是宣揚叛徒哲學,於是批判文章也一下子升了溫,上了中央級大報《人民日報》,其中的一篇署名文章把《五更寒》批得體無完膚,上綱上線成了地地道道的一株“大毒草”,我當然也被冊封為“毒草專家”。
1976年,萬惡的“四人幫”終於挎台了,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慶祝新生。被禁錮了十年之久的許多優秀影片紛紛解放復映了,嚴寄洲為之歡呼雀躍,可是不知道為了什麼惟獨對他執導的這部《五更寒》卻仍是無聲無息無人過問,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嚴寄洲實在弄不明白,大家為什麼對待這部影片如此“心有餘悸”而不敢造次?為什麼別的許多影片“解放”了,惟獨這《五更寒》卻石沉大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召開的“新中國電影35周年回顧學術討論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應當為《五更寒》恢復名譽,對過去極“左”思潮給《五更寒》的一些不實之詞應當一概否定。難道這還不夠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