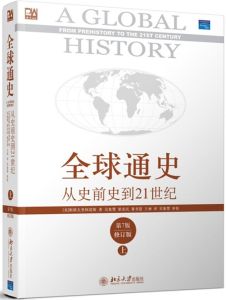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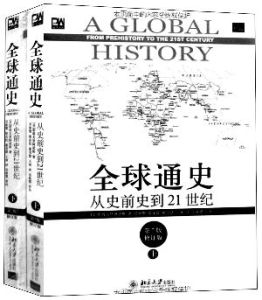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斯塔夫里阿諾斯 譯者:吳象嬰,斯塔夫里阿諾斯,斯塔夫里阿諾斯是美國加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曾獲得過古根海姆獎、福特傑出教師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等一系列學術榮譽。雖然他以《全球通史》聞名全世界,但實際上他著述頗豐,還有大量其他作品為學術界所稱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其他作品還包括《1453年以來的巴爾幹各國》、《奧斯曼帝國:它是歐洲的病人嗎?》、《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和《源自我們過去的生命線:新世界史》等。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已於2004年3月23日在美國加州拉荷亞去世,本書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後版本。
目錄
致讀者:為什麼需要一部21世紀的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諾斯
《全球通史》第7版推薦序劉德斌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樂觀與躊躇高毅
(上冊)
第一編史前人類
第1章人類——食物採集者
第2章人類——食物生產者
歷史對今天的啟示人性的本質
第二編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3章最初的歐亞大陸文明(公元前3500年一公元前1000年)
第4章古典文明使歐亞大陸趨於整體化(公元前1000年一公元500年)
第5章希臘一羅馬文明
第6章印度文明
第7章中國文明
第8章古典文明的終結
歷史對今天的啟示文明:是詛咒還是福音?
第三編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公元500一1500年
第9章中世紀文明使歐亞大陸實現整體化
第10章伊斯蘭教的興起
第11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12章傳統的拜占廷文明
第13章傳統的儒家文明
第14章革命的西方文明
歷史對今天的啟示發展中的社會與“受到阻滯的領先”
第四編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第15章非洲
第16章美洲和澳洲
第17章歐洲擴張前夕的世界
歷史對今天的啟示歷史上的種族
下冊
第五編公元1500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
第18章西方擴張時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
第20章擴張中的西方文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第21章西方文明的擴張:經濟成長和國家建設歷史對今天的啟示歷史與關於歷史的流行理念
第六編新興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七編西方據優勢地位時的世界,1796-1914年
第八編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與成功的世界
辭彙表
索引
編後記
序言
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速度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例如,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我們自然也生活在一個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是一個由西方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著發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結束了這種霸權,世界地圖上一些龐大的歐洲帝國的消失便證明了這一點。地圖上許多地方的名字和顏色都從根本上起了變化,從而反映了已在20世紀中葉以前出現的這一新世界。
我們漸漸不情願地認識到,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傳統的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觀已不合時宜,且具有誤導性。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儘管伴有種種精神求索的陣痛,但世界卻完成了自己從舊到新的轉變。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協會的出現、《世界歷史雜誌》的問世以及本書第l版的出版,皆證實了這種轉變。
這又使我們回到原先的問題上:為什麼本書第1版問世才幾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新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20世紀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20世紀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的結果。這種影響的無處不在,顯見於它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種種巨大的問題”中。例如,20世紀末葉的學生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臉困惑地趴在木製書桌上想,如果這時遭到核彈的襲擊,這些脆弱的木製東西如何抵擋得住呢?
地球母親已產生人類生命;這一代的學生不僅要面對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危險,還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威脅地球母親的危險。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JaquesCoust.eau)已發出警告:“人類在20世紀中對地球造成的傷害也許比在先前全部人類歷史中造成的還要多。”同樣,環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機構”也於1989年下結論說:“到1999年,真正決定人類命運的時刻將要到來。隨著世界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要么團結起來共同扭轉危機,要么陷入環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
由於物種與星球毀滅的黯淡前景,題有諸如《美國世紀的終結》、《世界的終結》、《未來的終結》和《歷史的終結》之類書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繼出版。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不過是長長物種鏈上的小小一環,那么這些令人沮喪的書名也許是對的。現在地球上大約有4000萬個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物種,而在此前的不同時期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也就是說,只有1‰的物種存活了下來,而99.9%的物種都滅絕了。這一紀錄似乎為目前上述“終結”系列著作的熱銷提供了統計學上的支持。
不過,這種統計卻具有誤導性,因為在人類和所有滅絕了的物種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後者的滅絕主要是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例如冰川世紀中發生的那些變化。相反,被賦予高級智慧型的人類則能夠通過使用火種、縫製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來讓環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因此,人類是能夠使環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從而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而不是奴僕的獨一無二的物種。
主人和奴僕之間的決定性差別,可以用人類和天花之間的關係變化來予以戲劇性的說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懼的一種,它最初出現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遠東,8世紀時被傳播到歐洲,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又散布到美洲。隨著歐洲人往其他大陸遷移,天花病毒殺死了無數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以及玻里尼西亞和加勒比海諸島的島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種族滅絕的慘禍。其實,天花病毒也曾在歐洲肆虐,並最終吞噬了歐洲大陸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壞程度與瘟疫相當。
對天花病毒的征服始於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Jenne)發現接種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被隔離在美國和俄國科學家的實驗室里,所以,天花與人類的關係給完全顛倒過來了。已知的最後一個天花病例出現在1977年的索馬里。1980年,人類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學家們一度建議把實驗室中餘留的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樣本也徹底毀掉,以防止它們傳播開來。但是人們延遲了做出這一最後決定的時間,因為這些病毒可能會對將來的研究有用。現在,科學家們已製造出無害的天花DNA片段,並有完整的基因草圖可供研究,這樣,天花病毒的樣本存留與否也就無關緊要了。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董事會一致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定為銷毀全部殘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這一長期以來折磨人類的病毒殺手已被鐐銬鎖牢,等待它從前的受害者確定一個日子來處決(和消滅)它。由此可見,人類已儼然成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物理學家沃納·海森伯格(WernerHeisenberg)總結說:“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對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夥伴或敵人。”但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類的這種首要地位乃我們當今全球性隱憂與恐懼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後,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自己。
這種與我們的內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對抗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不僅僅要求人類獲取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事實證明,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同時,它還要求用正確的倫理導向來確保知識被運用於正確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學革命興起的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Bacon)曾提到過科學革命的潛力,也警告過它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熱情洋溢地讚美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他同時也提到,這種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來加以引導,而且這種追求不應該是“為了自得其樂、爭強好勝、高人一等、追逐名利、爭奪權位,或其他任何類似的卑微目的,而應該是為了改善生活”。
我們可以在每天的電視節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學(I~~ordham)的年度報告《社會健康指數》中痛苦地發現,我們對於培根的警告忽視到了何種程度。上述報告是在青少年自殺率、失業率、吸毒率、高中學生輟學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統計數字的基礎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狀況。結果表明,美國社會健康指數從1970年的75點降到1991年的36點——就連該年度報告的主編都稱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會健康狀況中的這種“可怕的”惡化並不只限於美國。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從早7點到晚7點在巴黎散步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點。他散步時帶了一個計數器,“每當我遇到人們向我推銷我不需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按一下計數器,結果一天下來我總共按了183次。”
類似庫斯托的這種經歷俯拾皆是。無論是在巴黎、雅典,還是在洛杉磯、墨西哥,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但是,作為一個勤于思考的科學家,庫斯托由此開始探究這種個人經歷的社會意義。他在調查中總結出:“控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主義不是個人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我不是生態治國論者,絕不是。但是當你在街上開車看見紅燈的時候,你會停下來。你不會認為紅燈試圖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護你。那么為什麼在經濟學中不會有同樣的事情?責任要靠社會機制而不是個人美德來維繫。”。
庫斯托在《消費者社會是我們的敵人》一文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很重要的,因為消費者社會正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例如在中國,當毛澤東於1949年開始執政時,社會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腳踏車、收音機、手錶、縫紉機。後來,消費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電、冰櫃、機車等。如今,這一單子還在不斷變長,近來增加的大件是汽車。汽車在第三世界億萬“貧苦人民”中已成了社會地位的標誌。在1990—2000年之間,印尼的汽車擁有量從272524輛增長到675000輛左右,印度從354393輛增長到1100000輛,而中國則從420670輛增長到2210000輛。
環保主義者非常擔心這些不斷增加的數以百萬輛計的汽車對全球空氣的影響。不過,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卻指出:是西歐人發起了工業革命並隨後污染了全球的空氣,現在他們不能又讓這些“貧苦的人”固定在“永遠貧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發展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問題。現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對基本原則的時候。那么,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人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麼?當培根強調新興的科學必須被用於“改善生活”,而不是為了諸如“追逐名利、爭奪權位”之類的“卑微目的”時,他已經直面了這一問題。培根還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以下問題:難道人類非得變成經濟動物,只知道專注於膨脹的胃和膨脹的銀行戶頭嗎?
任何社會的首要目標都必須是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須首先提高經濟效率以使這些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但是,如果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滿足,難道人們還必須無視個人、社會和生態的代價而一味強調經濟生產率嗎?對於這個基本問題,人類尚未給予應有的考慮。也正是由於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在全球泛濫,正如庫斯托在巴黎散步時所發現的那樣。
這種躲閃的狀態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因而,人類現在正無可奈何地致力於尋找避免成為“經濟動物”的方法,或者更準確地說,致力於尋找一個“倫理羅盤”來引導技術的發展。這是人類遇到的一個巨大挑戰——人類曇花一現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戰。迄今為止,人類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環境,從而獲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隨著這一地位的獲得,又隨著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當今世界範圍的社會與環境的退化中,人類現在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一挑戰要求他從聰明的靈長類轉化為明智的人類——即從聰明轉變為明智。
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正如在過去反覆經歷並成功地應對了種種挑戰一樣,人類也正在應對今天的挑戰。因此,處於21世紀前夜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和革新,而當今遍布全球的變革則證明了這種革新的廣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國,堅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Shmelev)建議他的同胞們不要害怕失去他們“意識形態的純潔”。甚至在占優勢的種種市場經濟中,資本主義本身也正在以多種供選擇的形態出現。這些形態包括強調不受約束的自由企業制度的美國形態,強調福利國家和工人參與決策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形態,以及不同程度地將國家計畫經濟、被互相連線起來的聯合大企業、大公司的終身雇用制和政府對以出口為目的的國內工業的資助結合在一起的正在擴散的亞洲經濟形態。
這種多樣性表明:21世紀不僅面臨著巨大危險,而且還擁有巨大潛力。雖然歷史學家們沒有魔法師的水晶球,不能確定無疑地預知將來,但是,他們能比較確定地預測到,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地獄,而是一個擁有各種可能性的世紀。至於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夠實現則取決於這本書的讀者,你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的所作所為將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現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騙式的烏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憂天式的悲觀預言,現在到了對現存的慣例和制度做一個冷靜的再評價的時候了,我們應當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拋棄那些不合時宜的——這正是當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本書才有了這個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於這一再評價的過程,從而實現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拋棄他所反對的“卑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