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凱(Laszlo Krasznahorkai,1954- ),匈牙利當代著名作家、音樂家。作為當代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凱1985年以長篇小說《撒旦探戈》轟動文壇,此後被貝拉·塔爾改編為電影。他們的合作延續至今:貝拉·塔爾只拍拉斯洛的小說,拉斯洛只為貝拉·塔爾寫劇本,並參與拍攝的每個重要決定。他們合作的電影包括大獲成功的《撒旦探戈》和《鯨魚馬戲團》(改編自《反抗的憂鬱》)等五部。對於電影《撒旦探戈》,蘇珊·桑塔格曾評論說“片長七小時卻每一分鐘皆雷霆萬鈞,引人入勝。但願在我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 此外,克勞斯瑙霍爾凱還是將200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引薦到德國文學界的人。

生平經歷與跟中國的 緣分
克勞斯瑙霍爾凱與同時期的匈牙利知識分子一樣,免不掉流亡的命運。
1989年匈牙利的劇變並沒有給克勞斯瑙霍爾凱帶來多少興奮與歡娛,雖然他在那兩年之前就已移居到了柏林,免遭迫害,但他對舊體制崩潰之後的祖國給予了同樣嚴苛的評價。在他看來,在那個轉折性的年份之前,匈牙利人的遭遇是軍警、懲罰、禁錮與囚籠,在那之後,失落、物慾、幻滅與蒼白成為籠罩一切人的悲劇。我們也許很難找到像克勞斯瑙霍爾凱這么悲觀失望的東歐人。“我們再也不去想過去的那些事了。”在其他的東歐人以歡快的語調這么說時,你感受到的是一種明快的希望,但克勞斯瑙霍爾凱在這么說時,他表達的是一種鄙夷與迷茫。他提起他與一位匈牙利鄰居的對話。“你還記得嗎,20多年前我們還在這裡一起排著長隊買限量供應的香蕉呢?”他問。“喔,是嗎?我完全忘了,怎么還有那樣的事,不可能吧?”對方反問。人們的回答就像是被揭了舊瘡疤一樣痛苦,遺忘造就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似乎也帶來了幻滅與犬儒。
也許這正使克勞斯瑙霍爾凱將中國選擇為他新的心靈歸宿。他在1991年來到中國各地走訪,他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遇到的所有人的形象,包括一位居住在非常狹小的窩棚里、早起洗臉的農民工,在交談中,克勞斯瑙霍爾凱發現他是一位非常聰明而有見識的人。他還記得當時在夜晚的列車上遇到的一位工程師,向他講述了在荒僻的深山裡修建水壩的故事,在他看來,那是人力所無法完成的神跡。他向遇到的所有人詢問兩個問題:“你知不知道李白?”“你會背李白的詩嗎?”所有人對他的詢問也千篇一律:“你從哪裡來?”“你做什麼工作?”“你每個月掙多少錢?”關注金錢的表象揭示的是一種單純與善良。
但克勞斯瑙霍爾凱頭腦中構建的過於理想化的意象,很快被現實衝擊得體無完膚。他1996年另一場充滿期待的中國之旅以沮喪與幻滅告終,雖說這次他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來沿著李白的足跡在中國大地上行走,但他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或者說發現了被過去的自我幻想所遮蔽的真相。他看到了骯髒的江河、售賣可口可樂的佛寺、以俗艷的方式“翻修”的古蹟、拉著遊人兜售紀念品的和尚、以搖滾樂為背景的武術表演,以及炫耀豪宅與汽車的中國作家。據他的一位中國朋友的記述,西安酒店裡連夜不停的按摩小姐的電話氣得他用德語破口大罵。雖然面對記者的追問,他一直不願對中國有過度的批評,而似乎更樂於貶低自己的祖國,但他回國寫的第二本有關中國的書透露了他的心情,那本書的標題是《天空之下的毀滅與哀愁》。
 克勞斯瑙霍爾凱
克勞斯瑙霍爾凱文壇影響
他的身上堆滿了榮譽,他的好友、已故的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稱他是當今匈牙利最能激盪人心的大師,讓人想起果戈理和麥爾維爾。德國作家塞巴爾德則稱:“克勞斯瑙霍爾凱描繪的景象就像果戈理的《死魂靈》一樣具有普世意義,相比之下,所有當代作品的人文關懷都大為不及。”但他毫無自矜之情,他的語調和緩,表情和善,甚至因為對自己的英語不自信而有些羞怯。在採訪中,他的雙腿一直交叉在一起,那是一種面對筆記本與錄音筆的不安。但當他戴上一頂黑色的禮帽,穿上大衣走進北京街頭的寒風時,他就恢復了原貌——一個冷峻而苛刻地審視全世界的人,一個抵抗一切的人。
同來中國參加此次典禮的波蘭詩人萊貝達與捷克作家哈維爾與克勞斯霍爾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萊貝達講述了他的許多中學同學如何在沉悶壓抑的生活逼迫下自殺,哈維爾則談到他如何因為參加反政府的活動而入獄。對於1989年前後的改變,他們是愛恨分明的,而克勞斯瑙霍爾凱則一直保持著他近乎絕望的悲觀。旁人也許可以將此理解為憤世嫉俗者的故作姿態,但所有真誠的人對現實的認知都具有同等的真實性,即使是一個抵抗一切者的認知。畢竟,憤怒與批判的價值永遠高於附和與讚揚。
與貝拉-塔爾的相遇
克勞斯瑙霍爾凱說:
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識分子有很多時間,每一天都長到不可思議。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這一天會很長,生命會很慢。
在匈牙利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本書幾乎不可能出版。書稿在出版前換了許多人的手,小說最後能出版,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出版社的社長對我說:“我們可以出你的書,但有一個條件,只能印‘最小印數’。”那時的最小印數是10000冊。現在的人會說印10000冊是瘋狂的,出書一般都是2000冊、5000冊,但當時最少就是10000冊,那是個非理性的時代。我覺得當時在高牆後面,當局者覺得困惑,他們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了,而我們那時候還沒感覺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導演貝拉·塔爾打來電話跟我說,想把它拍成電影,我說不行——而我們的友誼就是這么開始了。
代表作
撒旦探戈(Santatango)那是一個農村公社走向瓦解走向滅亡的故事。當時匈牙利正處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塔爾那些異乎尋常的長鏡,非常緩慢,卻都是狠辣的批判。影片的第一個鏡頭,拍攝一群牛,自破落的牛舍里跑出,亂走之餘,還在試圖交配,正好是農村里眾人的寫照。在騙子出現之前,村民已在互相欺騙。酒館裡徹夜的狂歡舞會,喻意村莊裡的淫亂與墮落。狂歡後眾人爛醉,蜘蛛靜靜把網結在他們身上,亦象徵了這群農民無從掙脫的困局。他們總是在濕漉漉的泥濘上走著,後來離開了村莊,滿懷希望要過新生活,到達騙子 Irimiás 給他們的應許之地,卻是一片頹垣敗瓦。他們交出畢生積蓄,沒有買到希望,最後落得離鄉背井各散東西,並換來兩個苦悶的警察在他們背後極盡侮辱的挖苦。大概對這群愚昧的農民而言,人間並無樂土,當下已是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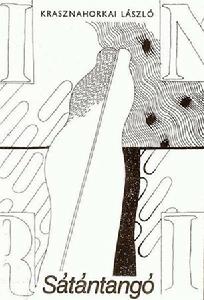 小說《撒旦探戈》
小說《撒旦探戈》電影在不同章節里,以不同角色的視點,重複交代著同一個情節,就把人物的命運交錯在一起。其中老醫生腳步蹣跚前去買酒,途中遇上自殺前夕的小女孩。其他人正在酒館裡開著舞會。小女孩抱著死貓,呼喚醫生,又拉著他,卻被他甩開,然後小女孩轉身逃跑,他想喊住她,但已經太遲了。小女孩彷佛是在作最後的呼救,可是這位酒醉的醫生,早已經沒有救人的力量了。
片長七個多小時,塔爾大概是要讓觀眾隨著角色的腳步,慢慢走入那個封閉無助的世界,其中沒有爆破沒有官能刺激,沒有想當然的煽情,就是這樣緩慢的,一步一步走在泥沼上,而且不見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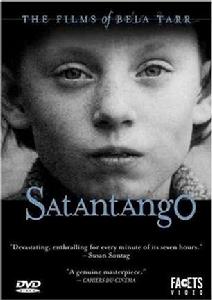 電影《撒旦探戈》
電影《撒旦探戈》克勞斯瑙霍爾凱的另一代表作《反抗的憂鬱》,也被拍成了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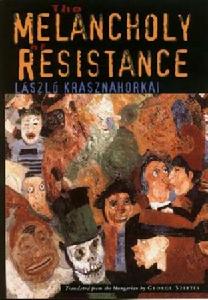 小說《反抗的憂鬱》
小說《反抗的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