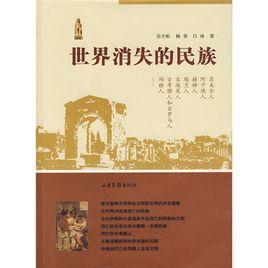內容簡介
該書力圖在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與考古發現的基礎上,追憶那些業已消失民族遠去的背影,梳理民族消亡與新生的歷史脈絡,重現世界古代文明曾經的輝煌與神奇。
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小亞細亞半島的西臺人和伊朗高原的埃蘭人、北非的古埃及人、歐洲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以及中美洲的瑪雅人等,這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偉大民族如今已經湮沒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它們創造的輝煌文明而今只剩下殘垣斷壁與沉默的雕塑、壁畫和泥版。然而,世界歷史的滄海桑田和人類民族的興衰變化,始終是一個令人慾罷不能的話題,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民族與文化的融合問題,更具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書力圖在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與考古發現的基礎上,追憶那些業已消失民族遠去的背影,梳理民族消亡與新生的歷史脈絡,重現世界古代文明曾經的輝煌與神奇。視野開闊,內容廣博,圖片豐富,信息量大,是一本集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於一身的世界文明史普及讀本。
內容簡介
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小亞細亞半島的西臺人和伊朗高原的埃蘭人、北非的古埃及人、歐洲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以及中美洲的瑪雅人等,這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偉大民族如今已經湮沒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它們創造的輝煌文明而今只剩下殘垣斷壁與沉默的雕塑、壁畫和泥版。然而,世界歷史的滄海桑田和人類民族的興衰變化,始終是一個令人慾罷不能的話題,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民族與文化的融合問題,更具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視野開闊,內容廣博,圖片豐富,信息量大,是一本集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於一身的世界文明史普及讀本。
目錄
前言 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歐文明的歷史盛衰
第一章 古代兩河流域消失的民族
西方考古發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譯
古代兩河流域的環境
蘇美爾和阿卡德語文學作品
自然神崇拜宗教信仰
法律和立法理念
科學和藝術遺產
2500年的歷史:從蘇美爾城邦興起到巴比倫帝國消亡
塞姆人的伊辛、拉爾薩和古巴比倫王朝的漢穆臘比一統天下
從阿淑爾城邦到亞述帝國
新巴比倫——兩河流域最後的帝國
第二章 古代伊朗和小亞細亞半島消亡的民族和文明
古代波斯文明的歷史記載和近東楔形文字的破譯
兩河流域文明的孿生兄弟——埃蘭文明
米底帝國和古波斯帝國
西臺文明的發現和文字的破譯
消亡的西臺國家和人民的歷史
第三章 消亡的北非古埃及塞姆——含語民族
金字塔時代的輝煌
中王國時期的發展
新王國和後期埃及
第四章 消亡的古希臘人
史前時代
古風時代
古典時代
地中海世界希臘化時代
第五章 從狼孩建邦到世界帝國的瓦解
平民和貴族的鬥爭與合作建立了羅馬共和國
統一義大利半島
稱霸西部地中海
征服東地中海世界
共和國向帝國的過渡
羅馬帝國的輝煌和瓦解
羅馬的文化遺產
第六章 中美洲滅亡的瑪雅人及其文明
瑪雅人的社會政治演變
瑪雅人的農業
瑪雅人的手工業
瑪雅人的貿易、運輸和貨幣
瑪雅語言文字、宗教、宇宙觀和藝術
文摘
第一章 古代兩河流域消失的民族
起源於今伊拉克南部的兩河流域文明和中國、埃及可稱古代世界最早興起的三大文明。從新石器時代起,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條大河哺育了這一地區許多農業村落。約公元前3000年,從外部遷移到伊拉克南部乾旱無雨地區的蘇美爾人開始利用河水灌溉農田,並在生產中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從而創造出一批人類最早的城市國家和燦爛的蘇美爾文明。在蘇美爾人的影響下,兩河流域本地的說塞姆語的阿卡德人加入了文明歷史的舞台,並先後和蘇美爾人並肩建立了阿卡德和烏爾第三王朝兩個帝國。隨後,蘇美爾人消融於塞姆人之中。塞姆語的漢穆臘比王朝把位於兩河之間最窄處的巴比倫城變為兩河流域南方的中心,發展成為巴比倫帝國;而沙姆西阿達德把底格里斯河岸邊的阿淑爾城發展成為兩河流域北部的中心,建立亞述帝國。兩河流域文明因此以巴比倫-亞述楔形文字文明(現代人文學科亞述學由此得名)而聞名於世。
西方考古發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譯
兩河流域文明和我們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個“死了”的文明。就是說在近現代考古發掘發現這一文明之前,當地的伊斯蘭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於不是兩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繼承者,並不知道這一偉大文明。他們只能把偶爾發現的古代碑銘文字當作神奇物品。當時的世界從《舊約聖經》和幾位古典作家的書中聽到過很少的關於巴比倫和亞述的記載,其中許多是神奇的傳說,真偽難分。公元前5世紀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是現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兩河流域古代城市和傳說的古典作家,他對巴比倫的記載是不太準確的。在他之後的色諾芬於公元前401年率領萬餘希臘僱傭軍經過尼尼微廢墟時已不知道這曾是亞述帝國的首都。400年後,斯特里波提到巴比倫城已完全廢棄。公元299年,羅馬皇帝塞維魯從帕提亞手中奪取了兩河流域,見到了巴比倫的廢墟。此時,兩河流域文明的靈魂——“楔形文字”在近東地區已經完全被希臘文和阿拉美亞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無人能讀寫了。古代兩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於置放廢物每年逐漸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時也用土墊高夯實。當一個城市由於戰爭或其他災害被摧毀後,泥沙不久就積滿了殘垣。當一批新居民來到廢墟重建城市時,他們將殘留的泥牆和廢棄物一齊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於是城市的地面又提高很多。這樣的過程反覆經歷了百年或千年,到這些城市最終被廢棄時,已高出周圍地面許多。風沙塵土最後完全覆蓋了廢墟,把它變成了一個土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居民的變遷,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城市的廢墟,更不必說它們的名字和歷史了。在兩河流域和周圍地區,有千百個這樣的被稱作“tell”的土丘,其中滄海桑田、百般奧秘只有經過考古發掘才能知道。在中世紀的歐洲,曾有兩個旅行學者對鄰近兩河流域的這些土丘發生過興趣。最早的一個是西班牙的猶太教士、圖戴拉城的班傑明。他在書中提到,當他於1160至1173年在近東旅行時,曾看到亞述首都尼尼微的廢丘在摩蘇爾城的對面。17世紀以來,歐洲旅行家開始對一些土丘產生了興趣。義大利人彼特羅·代拉·瓦勒(PietrodellaValle)在1625年發表了他親臨兩河流域的遊記。他不但認出了距希拉鎮60公里的巴比倫遺址,而且把他在巴比倫和烏爾丘上發現的楔形文字銘文磚帶回了歐洲。當然,世上無人能識這種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國人湯姆斯·黑德將其定名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麥王派出一支考察隊前往近東收集和發掘古代文物。隊長數學家卡斯騰·尼布爾(Karsten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遺址波斯波里斯摹繪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銘文(1761-1767)。隨後,許多歐洲人都陸續來到兩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倫等廢墟,收集文物、摹繪銘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國的修道院長約瑟夫·德包尚(deBeauchamp,1785年至1790年到兩河流域)、英國駐巴格達總領事和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勞狄·傑姆斯·瑞齊(Rich,1807-1821)、傑姆斯·白金漢爵士(1816)、羅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拜里葉·弗臘合(Fraser,1834)以及楔形銘文的釋讀者之一的亨瑞·克來斯維克·羅林森(Rawlinson)。1835至1886年,英國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探險隊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兩河的河道和地理風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倫各自挖的幾個小坑外,這些考古先驅者沒有進行發掘活動。
大規模的發掘始於1842年法國駐摩蘇爾領事保羅·埃米勒·鮑塔(Botta)挖掘霍爾薩巴德(Khorsabad),他的發現轟動了整個歐洲:一個亞述人的城市(薩爾貢堡)、宏偉王宮、數對巨形人面獅身石獸、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銘文和其他古物。緊隨其後,1845年,英國的亨瑞·萊亞德在尼姆如德(Nimrud,亞述的卡勒胡城)廢丘和尼尼微遺址發掘出了另兩個深藏地下的亞述宮殿(1846),獲得了價值連城的豐富收穫。1849至1854年,他和羅林森先後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亞述王大量的泥板文書。1877年,兩河流域南方的發掘拉開序幕,法國駐巴斯拉城的副領事厄內斯特-德薩爾宅克(ErnestdeSarzec)先在泰羅丘(Telloh)得到了幾個古代石像,隨後他的連續發掘使第一個蘇美爾人的城市(吉爾蘇)重見天日。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爾根(JacquesdeMorgen)帶領的法國考古隊在兩河流域鄰接的波斯境內發掘了古蘇薩城的遺址,也發現了大批古物,包括漢穆臘比法典石碑在內的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書以及埃蘭語楔形文字文獻。
1843年以來,英法兩國在兩河流域三十多年的頻繁挖掘使世界突然發現了這裡與希臘和埃及的古代遺址一樣存在很多古代財富、藝術品和文獻。於是像古典傳說的大西洋城一樣神秘的巴比倫和亞述帝國突然被世界認識到是一個和中國、希臘、埃及一樣曾經繁榮興旺的偉大文明。它的突然毀滅導致它被世界遺忘了約兩千年,它的重新發現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學的一個巨大的成就。然而,19世紀後半葉的這些發掘屬於考古的英雄時代。鮑塔、萊亞德、德薩爾宅克、羅弗圖斯(loftus)和史密斯這樣的英雄人物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都是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業餘愛好者、探險家和探寶者。他們在兩河流域發掘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石像、浮雕板等藝術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銘和泥板文書)。這種功利性的、掠奪性的發掘使他們沒有時間去注意泥磚建築、破損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藝術品文物和遺址的地層被破壞。儘管有這些缺點,我們還是應該承認英法這些不畏艱難的先驅者開拓了以考古發掘重新揭示燦爛的兩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當伊朗的楔形文字銘文被帶到歐洲後,許多學者試圖讀懂這一神秘文字。1778年,德國人卡斯騰·尼布爾認出他在波斯波里斯發現的幾組簡短銘文是用三種不同類型的楔形符號寫成的三種文字對照本銘文(後知道分別是巴比倫楔文、埃蘭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個字元,最簡單;楔文的寫法和西文一致是從左向右書寫的。這時期,歐洲學界研究伊朗語言的學者們釋讀了“波斯古經”等古波斯語檔案,知道古波斯國王的王銜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個學者對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礎上,德國哥廷根一位27歲的希臘文教師格羅特芬德(Grotefed)猜想三文對照銘文中的符號很少的第一組楔文應是波斯語的拼音文字,而銘文的內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銜。於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國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銜句式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組楔文中的各個楔形符號的音值,結果獲得了成功。構成三個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兒子”等詞的楔形符號的輔音和元音值被解讀出來了,從而確定了這種楔文是波斯語拼音文字。在11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語楔形文字的41個音節符號的讀音和一個單詞分隔設定全被學者們掌握了。然而,由於這些王銜銘文都很短,不能解決古波斯辭彙、語法等基本問題,尤其是學術界不能利用這些信息含量極少的三文對照王銜去釋讀另外兩種用更多的、更為複雜的楔文符號寫成的、非波斯語的銘文和大批的兩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書。
1835年,英國軍官亨瑞·羅林森被任命為波斯庫爾迪斯坦省總督的軍事顧問。年僅25歲的羅林森不但是一個古典語言、歷史學者,而且還正在學習包括波斯語在內的各種語言。剛到近東,對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興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羅特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況下,釋讀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個波斯楔文寫的一個波斯王的名字。隨後他走訪了伊朗西札格羅斯山中的貝希斯敦小鎮附近的一處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銘。岩刻所在處比小鎮高520米,而且從岩刻腳下到銘文頂端是104米高的、人工剷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讀者無法靠近銘文臨摹。由於這一個岩刻銘文長達數百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銘一樣也是用三種不同的楔文寫成的內容一致的三組銘文,摹繪這三組銘文並釋讀其中最簡單的波斯文將是解開楔形文字之謎的關鍵——因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釋讀另兩種複雜的楔形文字。1835至1847年,羅林森多次到貝希斯敦摹寫和拓制岩銘的複本。他做的這項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險的,特別是銘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還塗有一層類似清漆的保護層面,使懸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險。羅林森設法爬到了銘文岩面最底部,開始臨摹銘文。對於最難達到的頂部區的銘文,他把梯子架在銘文區狹窄的底部邊緣,爬上梯子摹繪;梯子夠不到時則在崖頂放下繩子,用繩子捆好自己,吊懸在空中摹繪。就這樣,他歷盡艱難在1835至1837年期間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銘文摹繪,並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獻讀出其中的幾百個地名,從而成功地釋讀了波斯語楔形文字的全部四十多個音節符號。他發現這是波斯王大流士記述自己平息叛亂、成為波斯帝國國王的記功岩刻。1844年,羅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種楔形文字(埃蘭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貝希斯敦,摹繪了岩刻面上最難靠近的第三種楔形文字銘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時,他不得不雇用一個本地攀山男孩幫忙。男孩小心地爬過光滑岩刻平面到達銘文區的上面,然後把隨身帶的木楔錘入岩縫,綁上吊繩,懸在空中,按下面的羅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紙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銘文。在對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銘文的研究中,羅林森利用他讀懂的波斯語楔文去逐步地對照研究另兩種楔形文字。他發現第二種楔形文字(後來稱為埃蘭語楔形文字)有一百多個字元,而第三種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楔形文字)有多達數百個符號。他發現阿卡德語禊文的一些奇怪的特點:一個符號可以有兩個以上的音節值,許多符號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羅林森的釋讀證明了兩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語和兩河流域現代居民的阿拉伯語同屬於塞姆語系。他發表的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銘使許多學者可以投入釋讀楔形文字的國際研究。1851年,羅林森發表了第三種楔形文字的音讀和譯文以及246個符號的音節值和語義,基本上讀懂了塞姆語楔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