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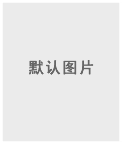 文字
文字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簡介
胡丘陵的第二部長詩
作者簡介
胡丘陵,1982年參加工作,曾任鄉民政助理、財稅所副所長、縣政府辦綜合組長、副主任、縣委辦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鎮黨委書記等職,1998年任衡陽市委組織部副處級組織員,2000年12月任中共常寧市委副書記,現任常寧市市長。國家一級作家
作品賞析
心靈對“廢墟”的詩性命名
——談胡丘陵長詩《2001年,9月11日》
陳超
中國現代詩界一直有一個困擾於心的問題,即詩歌是否需要有強大的社會功能?一些詩人認為,詩歌應以藝術自身為目的,不必承擔什麼社會歷史使命,這樣才會保證詩的純粹;另一些詩人則認為,詩歌就是表達詩人對社會歷史、生存及世上事物的看法,至於詩的表達方式本身,是次要的問題。
如果硬要我在這二者之間選擇,我只好先選擇前者。因為雖然後者有時會使文本顯得重要,但卻只有藝術標準才能決定它究竟算不算詩。幸好不存在這樣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完全可以在詩與思的統一標準下來衡估詩歌。最近,讀了胡丘陵的長詩《2001年,9月11日》,感到這是一部既有飽滿的社會生存和歷史命名力量,又有很高藝術價值的作品。
由於這首詩的題材是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可能會有人懷疑其藝術品位,而另一些人則擔憂它是否能有新意?這使我想到美國“新批評派”理論家艾倫•退特那篇著名的論文《詩人對誰負責?》。這篇文章對那種要么指責詩人不直接對社會事件負責,要么指責詩人不搞“純粹藝術”的人們都有啟示。他說,“硬要詩人自認是社會秩序的立法者,這其實是要詩人丟開詩人的確切責任。詩人的責任本來很簡單,那就是反映人類經驗的真實,而不是說明人類的經驗應該成為什麼。任何時代,概莫能外。詩人對誰負責呢?他對他的良心負責,‘良心’一詞,取它在法文中的含義:知識與判斷的呼應行動。詩人的良心早就知道,在鑑別詩人是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人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嚴格、傳統的標準。無論怎樣嚴峻的危機,都不應該被利用來使我們改變詩人與他周圍的恆定現實的關係。所以,詩人對社會所負的責任絕不是按社會思潮或社會需要去編詩。詩人對什麼負責呢?他只對他作為一個詩人應當具備的德行負責,對他的特別的藝術風骨(aretee)負責;他的責任是精美地掌握他的話語,而且,這種話語不會減損他的意識所傳達給他的關於現實經驗的全部真實性。而迫使詩人不作詩人,去做某種政治思想的宣傳家,這才是不負責任的——哪怕是詩人自己認為這樣乾值得,也依然是對詩歌的不負責任。”這話說得既求實又精彩,對現代詩的本體和功能有著雙重關注,在堅持詩歌獨異的藝術魅力和特殊的揭示生存∕生命的功能上,取得了平衡。真正的詩人不會長久困擾於“是歷史承擔還是藝術迷醉?”這個二元對立的假問題,因為他的歷史承擔也同時是詩藝的承擔,他的迷醉也包含著對歷史之詩與思的迷醉。正如葉芝所言,“誰能將舞蹈和舞者分開?”我滿意地看到,胡丘陵先生也沒有被以上假問題困擾,他以一個詩人的良心和藝術才華,寫出了對“9•11”這一震撼世界的巨大恐怖攻擊事件的感悟。
摧毀世界貿易中心大廈和一部分五角大樓的那場恐怖攻擊,已經過去了四年。除當事人外,悲悼的濃烈氛圍似乎已經過去。但是,胡丘陵的這部長詩依然使我有足夠的興趣去讀。原因就在於,它不僅僅書寫了這個事件,表達了詩人的情感經驗和對當時具體歷史語境的思考;同時更是以現代詩的特殊肌質、構架,嚴密的句群及細節呼應去穿透這個事件本身,表達詩人獨特的感悟和想像。並且,特別顯豁的還有,詩人能將之伸延到更為廣博的人文系譜、歷史、宗教與藝術語境中,以構成此詩深層的“文本間性”。這些長處,就使得它在“事件”過去之後,仍然能不斷縱身躍起,以詩的魅力吸引我們的閱讀。這是詩人承擔意識的勝利,但更為根本的還是詩本身的勝利。“廢墟”廢掉了,詩歌命名的光柱依然明亮。
正如前面退特所言,詩人只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在此,退特的“良心”同時指向社會和藝術形式。後者自不待說,就前者而言,詩人的良心也不會等同於簡單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左派,右派,第X世界,大國沙文主義,原教旨主義厖正是這種在超越事件的同時又更深地浸漬其中進行的詩性的追問、命名的態度,使我對這首詩及作者懷有很強的認同感。詩人沒有過多再現那場恐怖事件的場景,而是以幾個強烈而簡勁的表現性畫面,寫出了事件更促人深思的一面,並有強烈的個人心靈體驗。如這樣的句子,“兩隻原本可愛的鴿子∕吞進了,聖水與仇恨澆灌的幾粒糧食∕和一千零一夜故事∕迷失在,繞樹三匝∕總不能築巢的樓林∕將毀滅的方向,當成∕回家的方向。”這裡,“鴿子”也成為毀滅的實施者,但其內心的真切仇恨、神聖皈依感與種族命運的無告性,也彼此糾葛錯綜而來。“生命和使命,同時撞上∕美利堅,美麗而堅固的大廈∕和8點48分,這一刻骨銘心的時間∕那些叫做石油的文明乳汁∕因為在地下∕或者與伊拉克那些∕也只能在地下生活的兒童∕一起埋葬得太久∕迸出傷口,野蠻地燃燒。”諸如此類源於情感復調的話語,只會發自於一個詩人的“心靈”,而不是做簡單的“價值判斷”的“大腦”。
以心靈對“廢墟”的命名,是詩歌特有的方式,胡丘陵基本做到了這一點。我說過,若問詩歌對“意義”的揭示有何特徵,那就是詩歌源於詩人的心靈,它捍衛了世界以“噬心問題”的形式存在,而不被僵硬的自以為是的理念判斷所簡化和刪除。胡丘陵的詩通篇貫穿著詩的感悟,詩的追問,詩的祈願、詩的批判,和詩的韻律,我聽到了一顆詩心跳動的聲音,它邀約我們共同省悟這個事件背後更為晦澀的歷史——現實——民族——文化——宗教厖糾結,以及伴隨著現代化、全球化進程,整體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和生存困境。所以詩人說,“我的那些從海中打撈的整整齊齊的詩句∕也被撞倒在海里∕東一行,西一行∕至今,還在不知所終的旅途∕到處流浪。”我認為,這也在不期然中道出了詩人的寫作態度。理智是堅硬的,“是非”分明的,它以非矛盾律為前提。而心靈之詩卻應是柔軟的,悲憫的,矛盾糾葛、“不知所終”正是其常態。我想,也正是忠實於古老的心靈詩歌之道,才使這首詩葆有了較深厚的生存體驗和藝術感染力。正如荷馬史詩的作者,並不站在阿喀琉斯或赫克托耳任何一方,他只是以詩的話語重構“事件”,並將之探入到戰爭背後不為人關注的生命意志原動力中去。
然而,不要認為“心靈”是無力的,是對事件實質的“逃避”。不,它才是更為有力的“面對”。我們知道,在這場恐怖時代的種族主義所策劃的襲擊里,幾千人在不到100分鐘內喪生,眾多的人尖叫著從1000多英尺的高處墜落而死,千個家庭失去了親人,1500多名兒童瞬間成了孤兒。還有死於“9•11”事件的非法移民,他們的家庭由於是美國非法居民而無法向政府求助。的確,有不少家庭獲得了慈善捐助,但相對而言,那些喪失生計或生命的最貧困的底層勞動人民,其實並沒有多少人去關心、甚至只是專注於此的報導、談論。詩人的心靈同樣為此而戰慄,但他不是以詩之下駟,去逐視聽傳媒之上駟。他所要完成的不只是對“廢墟”的描述,更是以心靈對廢墟內在涵義的揭示和命名——
“是誰,使一些無辜者/成為另一些無辜者/不共戴天的敵人?”
“為什麼,人生的道路千條萬條∕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啊∕你們為何各自∕只指給他們一條道路?”
“太陽的光亮∕被玻璃幕牆,反射到∕大洋的彼岸∕使那些躺在帳篷中的人∕耿耿難眠。”
“高樓崛起於∕艾略特的荒原∕縱然繁花錦簇∕也免不了,荊棘叢生。”
“不必拉門∕大樓所有的門都為你開著∕可你自己的門∕早已關閉∕別人進不去∕你也出不來∕注定要在煙火中窒息。”
“不要用個人的軀體∕秘密地製造恐怖∕也不要用國家的機器∕公開地製造恐怖∕不要使用人體炸彈∕更不要使用核子炸彈。”厖
如此等等的詩句,無論象徵隱喻,還是直抒胸臆,大都做到了詩與思的忻合。這就使胡丘陵避免了時下某些“社會時事詩”停留於對局部是非的表白,而體現了詩人心靈的感悟力和豐富性。詩人甚至希望以心靈的追問、體驗乃至遲疑,去制約任何形式的獨斷論暴力,他說“用拉薩路沿路乞討的資金/來修復這兩幢大樓吧∕讓每一層,都住著一個∕哈姆雷特。”是的,心靈糾葛的哈姆雷特,正是現代寫作語境下一個合格詩人的形象。與之對應的,是被卡通化的堂吉訶德。
我們還看到,除去詩人以遼闊的視野與眾多古今中外的經典文本構成的“文本間性”對話外,此詩還有由諸多歷史事件構成的廣義的“互文性”。比如,“那些從視窗跳下的冤魂∕從納粹的集中營∕一直跳到南京的土坑∕良知的濃煙∕湮沒世界上∕所有笑聲。”這種由歷史想像力制導的“秘響旁通”,是非常有力的,它使得此詩繁簡相宜,張弛有度,既精敏又放達。這也是心靈變動不居的力量,使我們不只是看到“兩滴眼淚掉了下來∕大西洋鹹了許多”的悲憫與譴責,詩中“鹹了許多”的還有逝去年代歷史的回聲、歷代無辜生命的哀喊或啜泣。
詩人既寫道,“追求用火焰和機關槍∕說話的人們呵∕其實用餐具和酒杯也可以對講”,表達了他反對一切戰爭,企望人類和平自由的心愿;同時又嚴厲譴責了這次巨大的恐怖事件的指揮和實施者,“有些信念越是堅定∕人比其他動物就更為兇殘”,“智慧的恐怖∕比野蠻∕更為恐怖”,“不管做錯了什麼∕還是做對了什麼∕無辜的生命,都不應該∕成為攻擊的對象。”這裡,詩人的立場只是人心的立場、人道的立場、生命價值的立場。而針對許多人將這場恐怖攻擊解讀為“象徵性的政治宣示”,並將跨國資本主義和美國軍國主義联系一體的看法,詩人也表達了自己的心靈之聲:任何意義上的針對平民的大屠殺,都會徹底喪失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信譽,無論是恐怖事件的策劃和實施者,還是大國軍事霸權主義者使用致命武器來對他國平民區的狂轟濫炸,都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和藉口可言。這些根本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某個民族某種宗教,它們都是對全人類的根本犯罪。詩人既以詩性的情境,寫了西方中心論、國際霸權主義、軍事占領、窮兵黷武、後工業膨脹及全球化進程,給第三世界人民帶來的壓迫,也堅決斥責那些恐怖集團以此為說辭,針對西方世界的平民所實施的頻繁的恐怖攻擊。在詩人心靈的天平上,這兩種行徑,只是不同半徑的同心圓,都不具備合法性。同樣,我注意到,詩人沒有簡單認同“國際輿論”將恐怖分子妖魔化,沒有像布希政府那樣將他們說成“瘋狂、病態”,“惡魔、懦夫”,更不曾簡單化地扭曲書寫他們的政治-民族信念。在詩中我還注意到,詩人對宗教本身並無偏見,甚至是懷有敬意的,“有一天,我和高樓一起∕平靜地躺在手術台上∕用宗教的刀,剖開我的胸膛∕慢慢地,醫治創傷,”只不過他希望“誦讀《古蘭經》《聖經》和《佛經》的人∕也讀一讀中國唐人‘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讓地球村莊的人們∕都歡聚在和平的樹蔭下∕共度一回∕詩歌的節日。”因為鑄劍為犁就是詩意的生存,“我們不能,再走那條∕撞得變形的道路∕即使是聖者∕也不應為死亡∕感到高興。”詩人反對那些宗教中原教旨主義的宗派性,但對它們核心價值中深厚的人文主義內涵卻同樣發出了衷心的讚嘆。這些表達是有難度的,意義和技巧的雙重難度,但詩人用心靈的真實解決了困難。
限於篇幅,此文側重談我對這首詩印象深刻的方面,即詩與思的平衡和心靈問題。其實,這首長詩的語言也較為精彩,我將之稱為“異質融匯的話語”。雖然我不能說詩人的話語型式有多少開創性,但能將隱喻、暗示、象徵,與口語、敘述、戲劇獨白奇妙地融匯為一體,而絲毫不顯得“隔”與“澀”,的確體現了詩人較為成熟的筆力和心智。從詩歌格調上,詩人也在輓歌與反諷,體驗與省思之間達成了恰當的平衡。總之,在我看來,這應算是一部“新派時事詩歌”的成功之作,不僅是意味的成功,也是藝術的成功。而回到文章開頭就可以看出,我側重於談其“心靈”的一面,除去篇幅限制外,也是因為它在藝術形式上已經具備了良好的成色。我祝願作者繼續精進,寫出更為有魅力乃至“魔力”的大詩章。
作品人物介紹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影響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評價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成就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榮譽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作品現實意義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相關影視作品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其它
在此處添加文本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