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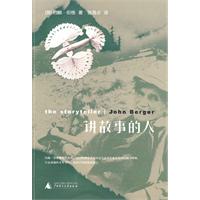 講故事的人
講故事的人約翰·伯格隨筆代表作,定居的耕作者和從遠方面來的旅者物質的融合輝映,行走成就的無界書寫,故事引導的紙間旅行。
我從不曾想把寫作當成一種職業。
這是一個孤棲獨立的行動,練習永遠無法積蓄資歷。
幸運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開始這一行動。
無論政治的抑或是個人的動機促使我寫點什麼,一旦筆尖觸及紙面,寫作便成了賦予經驗以意義的奮鬥。
每個職業都有自己的領地,同時也有其權能的極限。
而在我看來,寫作,卻沒有自己的領地。
寫作不過是去接近所寫經驗的行為,正如(但願)閱讀是去接近所寫文本的行為一樣。
——約翰·伯格
內容簡介
今天,約翰.伯格生活、工作在法國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小村莊。在社區里,人們將他看作一個受歡迎的陌生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將他視為親愛的朋友。人們認可、欣賞他講故事的天賦,而在過去十年里,這個天賦有了極大的進益。
1935年,沃爾特·本雅明寫了一篇非常傑出的隨筆,題為《講故事的人》。約翰·伯格的寫作顯然深受這篇隨筆的影響。本雅明區別出兩種傳統的講故事者:定居的耕作者;從遙遠地方來的旅行者。在他阿爾卑斯山的家裡,我多次從約翰·伯格身上看到這兩種類型的並存。
伯格的思想引導他成為農民,而他作為農民的經驗又影響他的思想,這一點是無法表述的。我們暫且孤立出一個重要的方面:相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宣傳,農民階級保存著一種歷史感,一種時間的經驗。以伯格的話來說,扮演毀滅歷史角色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是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的興趣是切斷與過去的所有聯繫,將所有努力和想像轉向未曾發生的未來。
對於剝削和疏遠,農民是再熟悉不過的;但是,對於自欺,他們卻不那么敏感。正如黑格爾著名的主奴辯證里的奴隸,他們與死亡、世界的基本過程和節奏之間保持著更直接的關係。通過他們自己雙手的勞作,他們生產、安排他們的世界。在他們的軼事和故事裡,甚至在他們的閒話里,他們根據記憶的法則編織自己的歷史。他們知道是誰通過進步得利,他們有時沉默地,有時秘密地保留著一個完全不同世界的夢想。約翰·伯格展示了應當向他們學習的是什麼。
講故事的人將自己的聲音借給他人的經驗。隨筆作家將自己借給特定的場景,或者他所寫作的問題。約翰·伯格本人的事業和思想形成一個語境,只有在這個語境裡,我們才能理解本文集裡的文章。但是更多地了解約翰·伯格的關鍵是為了更有效地向他學習,更深刻地理解他所提出的各種緊迫議題和困難問題。
作者簡介
約翰·伯格,192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
1958年,伯格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我們時代的畫家》,講述一個匈牙利流亡畫家的故事。此書揭露的政治秘聞,以及對繪畫過程細節的刻畫,令讀者誤以為這是一部紀實作品。迫於“文化自由大會”的壓力,出版商在此書上市一個月之後便回收入倉庫。之後發表《克萊夫的腳》和《科克的自由》兩部小說,展示英國都市生活的疏離和憂鬱。1972年,他的電視系列片《觀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時出版配套的圖文冊,遂成藝術批評的經典之作。小說G,一部背景設定於1898年的歐洲的浪漫傳奇,為他贏得了布克獎及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此一時期,伯格亦對社會問題頗為關注,這方面的成果是《幸運的人一個鄉村醫生的故事》和《第七人歐洲農業季節工人》,後者引發了世界範圍內對於農業季節工人的關注。也因為這本書的寫作,伯格選擇定居於法國上薩瓦省一個叫昆西的小村莊。1970年代中期以來,他一直住在那裡。後來,伯格與讓·摩爾合作製作了攝影圖文集《另一種講述的方式》,將對攝影理論的探索與對農民生活經驗的記錄結合在一起。
他對單個藝術家的研究最富盛名的是《畢卡索的成敗》,以及《藝術與革命》,後者的主角乃是蘇聯異議雕塑家內茲韋斯特尼。在1970年代,伯格與瑞典導演阿蘭·坦納合作了幾部電影。由他編劇或合作編劇的電影包括《蠑螈》、《世界的中央》以及《喬納2000年將滿25歲》。
進入80年代,伯格創作了“勞動”三部曲,包括《豬玀的大地》、《歐羅巴往事》、《丁香花與旗幟》,展示出歐洲農民在今日經濟政治轉換過程中所承受的失根狀態與經歷的城市貧困。他新近創作的小說有《婚禮》、《國王:一個街頭故事》,還有一部半自傳性作品《我們在此相遇》。伯格還撰寫了大量有關攝影、藝術、政治與回憶的散文,展示出寬廣的視野和卓越的洞識。這些文章收錄於多部文集,較有影響力者包括《看》、《抵抗的群體》、《約定》、《講故事的人》等。
2008年,伯格憑藉小說FromAtoX再次獲得布克獎提名。
寫作背景
十九世紀有一個傳統,那便是小說家、故事家,甚至於詩人通常會在導言裡為公眾提供他們作品的歷史解釋。一首詩或者一則故事無法迴避去處理一種特殊的經驗:關於這經驗如何與全世界的發展相聯繫,這一點是能夠也應當自寫作本身暗示出來的——這正是語言的共鳴所提出的挑戰(在某種意義上,任何一種語言都像位母親,知道一切);儘管如此,一首詩或者一則故事通常不太可能徹底分辨特殊和普遍之間的關係。而那些企圖這么做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寫成了寓言。於是作者便生起了圍繞著他的作品作解釋的欲望。這個傳統之所以在十九世紀確立,完全是因為那是一個充滿革命性改變的世紀,在那個世紀。個人和歷史之間開始形成一種有意識的關係。而在我們這個世紀,改變的範圍和程度甚至更大。
約翰·伯格在《豬玀大地》的“歷史後記”中如斯開場,這本集子寫的是農民的故事,是他手頭的《勞作》(IntoTheirLabotur)三部曲的第一部。
今天,約翰·伯格因為他的小說、故事、非小說作品——包括幾部藝術批評,以及與攝影家讓·摩爾(JeanMohr)合作的作品——而享有盛名。在他的創作生涯中,約翰·伯格還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隨筆作家,他定期為廣大的讀者寫作。本書所展現的正是他寫作的這個特殊方面。
這是他的第五部隨筆集,就其囊括的時間跨度、寫作類型、所關注的問題而言,這本文集是最為詳盡的。以他最新近的作品為軸心,本書使我們得以管窺他寫作思想的發展。作為約翰·伯格隨筆的代表作,本文集使得我們能夠理解他其他形式和體裁的作品背後的靈光一現。愛情和激情、死亡、力量、勞作、時間的經驗以及我們當下歷史的本性:這些貫穿本文集的主題,不但是約翰·伯格作品的中心,而且也是當代的緊迫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