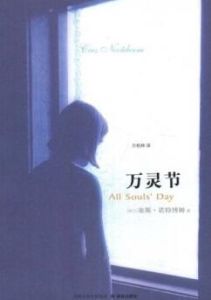編輯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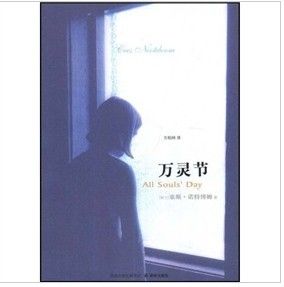 |
| . |
內容簡介
《萬靈節》的主要場景並不是發生在萬靈節,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節日當中。阿瑟是荷蘭的一個記錄片攝影師,除了經常接受國際拍攝任務之外,他還有個愛好,就是拍攝黃昏或者凌晨,其時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個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陽間和冥界的交錯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兒在飛機失事中喪生。其亡靈不時浮上心頭來,而他卻又要努力習慣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無牽掛,卻又藕斷絲連,通過看不見的線路和世界連線。語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們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們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館和寄宿公寓,一個漂浮的世界。紐約,馬德里,柏林”。這漂浮生活中,他落腳最多的是德國柏林。而統一後的柏林本身,也在歷史和現實的明暗交錯之下。歷史的幽靈,仍在這個統一後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個導遊一樣,帶我們進入這座城市的東西方結合處,帶入這個城市的現在和過去,帶入這個城市的靈魂深處。作者簡介
塞斯·諾特博姆(1933- ),現代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語出A.S.拜亞特),生於荷蘭海牙。他是詩人,也是旅行作家和翻譯家,作品中的實驗風格最讓讀者印象深刻。多年來,他遍游歐洲,用文字表達他對生活和自我的思考。他獲得過各種文學獎項,包括P.C.胡福特獎、飛馬文學獎、康斯坦丁·惠更斯獎、奧地利歐洲文學國家獎。近年來,諾特博姆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名單中。媒體評論
《萬靈節》是歐洲小說的精粹,強烈建議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準備一部大型百科全書在手。——澳大利亞《世紀報》和納博科夫一樣,他的小說里滿含暗示,哲思遍布在最平常的敘述中。——《紐約時報書評》
你們存在於特定時間的能力是百限的,你們超越時問而思考的能力則是無限的。——《萬靈節》
關於歷史和時間的流逝,關於一個男人如何著迷地尋找一種方法,以便能清楚地記錄下正在發生、然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形象和聲音。——《紐約時報書評》
前言
塞斯·諾特博姆(CeesNooteboom)是荷蘭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遊記作家、翻譯家。《紐約時報書評》稱其為“20世紀的鄉村說書人”。紐約的《村聲》周報稱其為“作家中的作家,其著作常象徵著藝術本身,其作品中的典故隨手拈來,儘管其作品都不長,但是有些讀者讀起來,可能得重溫一下西方(甚至還有東方)文化和文學史才行”。《華盛頓郵報》說:“諾特博姆作品主題宏大,但他絕非眼高手低之輩。他在尋常事物中灌注哲學思考。他的思想會不經意地突然出現,叫你猝不及防,如同一個荒廢櫥櫃裡藏著的天使。”對中國讀者來說,諾特博姆的名字還略顯陌生,但他的部分作品已經開始引進,如其遊記作品《繞道去聖地亞哥》。《萬靈節》被德國一雜誌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五十部小說之一。萬靈節》(AllSouls’Day)這部小說的書名“萬靈節”不同於我們常說的萬聖節(AllSaints’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萬聖節是11月1日,紀念已經升入天堂的聖徒。而萬靈節則為羅馬天主教、聖公會等宗教的一個節日,在萬聖節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該節日紀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淨,還不能上天堂。和中國清明節一樣,在這一天,人們相信亡靈會歸來。
這部小說的主要場景並不是發生在萬靈節,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節日當中。阿瑟是荷蘭的一個記錄片攝影師,除了經常接受國際拍攝任務之外,他還有個愛好,就是拍攝黃昏或者凌晨,其時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個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陽間和冥界的交錯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兒在飛機失事中喪生。其亡靈不時浮上心頭來,而他卻又要努力習慣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無牽掛,卻又藕斷絲連,通過看不見的線路和世界連線。語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們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們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館和寄宿公寓,一個漂浮的世界。紐約,馬德里,柏林”。這漂浮生活中,他落腳最多的是德國柏林。而統一後的柏林本身,也在歷史和現實的明暗交錯之下。歷史的幽靈,仍在這個統一後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個導遊一樣,帶我們進入這座城市的東西方結合處,帶入這個城市的現在和過去,帶入這個城市的靈魂深處。
阿瑟在這座城市中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國女物理學家、多才多藝的荷蘭雕塑家、口才迷人的德國哲學家。他們常在德國的一家小酒館喝酒,品嘗各種德國傳統美食,如優酪乳酪、燴豬肚、按中世紀食譜做成的黑麵包、做成大教堂狀的香腸大拼盤。他們在一起吃著,聊著,他們的談話充滿智慧。和這樣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點都難。連酒館的老闆舒爾澤先生,也都文質彬彬,如我們所說的儒商。他執意保留德國美食傳統,不叫那全球化中的美式快餐,打敗飲食世界的多姿多彩。幾個德國、荷蘭、俄國知識分子在一起相聚的時候,他們對傳統流連忘返,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對一種動物的滅絕而大呼小叫,而對一道燴豬肚這樣的美食,對格拉斯筆下女子的優雅氣質的滅絕無動於衷,唯有粗俗和無禮代代相傳。
只是曲高者和寡,深刻的人是孤獨的。這群知交一旦離開短暫相聚的酒館,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如陷入了各自的孤島。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萬靈做伴,每個人都有一個難忘的過去要去對付。俄國人季諾碧亞常會記起在俄國吃不飽肚子的那些漫漫長夜。飢餓讓她脫離困境後不停地大吃,吃成了胖子。漫漫長夜中的失眠,讓她習慣了仰望星空,開始熱衷於外星探索。在小說當中,阿瑟還有個紅顏知己,在荷蘭的厄爾娜,他們的友誼讓人看到男女之間也可以這么無限接近卻永不越軌。阿瑟是厄爾娜的禁果,而厄爾娜則是阿瑟永可依靠的安慰,我們誰不希望找到這樣可貴的朋友呢?阿瑟在柏林偶遇一個歷史專業的女博士,同樣來自荷蘭,卻在研究西班牙某箇中世紀女王。在書齋之外,她是空手道高手,是個女妖一般的舞者,是個來無影去無蹤的尤物。博士自有自己的幽靈在折磨她。過去她曾被強暴。往事不堪回首。她縱深一躍,跳到了中世紀的故紙堆中了。
阿瑟愛上了她,愛情讓他日漸走出過去的陰影。可是還不如說是她愛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她卻在黃昏的時候,像貓一樣抓門,進門之後,一言不發,脫個精光,騎到荷蘭攝影師身上。她顯然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女權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動行為,包括打電話找她。這場戀愛注定是一場遊戲一場夢。這遊戲和夢在柏林的圖書館,在日本四國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展開。最後的下場卻是悲劇。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中,相當於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每個人還如同那萬靈節的亡靈一樣不得超脫。然而一些變化確實又在發生,阿瑟在友誼當中找到了安慰,而女博士看來是要心無旁騖、矢志鑽研學問了。
人世間多少這樣的事情在發生著。人類在一男一女的關係上生髮出氣象萬千的故事來。好多事情被埋沒了,然而人類的對話還在綿延不絕,穿越正史的記錄,迴蕩在不間斷的時空之中。人類是孤獨的,當我們將人類歷史當做一條長河的時候,我們又不是孤獨的。書中的德國哲學家阿爾諾舉杯說:“為我們短暫的生命乾杯。為那些遨遊在我們上方的成百上千萬幽靈乾杯……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師……你們永遠都不會孤寂。” 小說中每個人都被過去的幽靈糾纏,而過去合在一起,便是歷史。作家似在暗示,歷史是一種虛構,而文學卻是一種真實。常聽人說: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實的。小說中的女博士在研究一個非常冷僻的課題,中世紀西班牙女王。雖然她最後跑到西班牙國家圖書館找到了資料,可是所有這些資料加在一起,又能說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遙遠的過去,我們對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實就是一個悖論:你寫歷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實,可是你不去想像,如何填補文獻之間的溝壑?作者引用馬可·布洛赫的告誡說:“歷史現象,脫離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則無法理解。”而你若是去想像,就開始在打虛構的擦邊球了。小說的最後一頁,引用的是羅伯特·卡拉素在《卡什亡國考》中的一段話:“近數十載,今人治史,好取毫枝末節,雖渺遠無關亦趨之也。史家吞吐之故紙汗牛充棟,及至成書成文,雖謄錄書手,問津者亦鮮也,而況學人乎?治史者偶可訴諸動機,自我欺哄耳。學者涉於文獻之海,自覺撥雲見日,去偽見真。或飾其文以數字、圖表,自詡科學。然史之轍跡,皆無聲之謎。史料搜羅日眾,則此理益昭昭也。逝者如斯,曩昔之生靈運命,沉寂無邊,自成一體,與前無涉,與後無乾,非名號、公證、文牘之考訂所能涵括也。”然而這個女子卻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紀,我們跟著一道放逐,哲學家阿爾諾也跟著研究起中世紀的音樂來。這小說提到的中世紀聖歌,或是馮·賓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聽。可是今人的演繹,又有多少還是原貌?歷史和現實糾結,故去的親人和自己的生命交錯。亡靈和過去成了生命的場,在我們每個人的周圍。過去看不見,瑣碎,有些正在發生之中就開始被人遺忘,歷史學家不會去關注,它們卻形成了我們的生命,影響著我們各式各樣的決策。科幻小說中常言“回到未來”,而這部小說,則是讓我們邁入過去,因過去寫就了我們的現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也寫道:“於是我們划著船,繼續向前,逆流而上,船毫不停歇地倒退著,駛向過去。”
小說中記載了兩種歷史,一種是史家筆下的歷史,它們是大事、大人物,另外一種歷史是“無名”的歷史,無數發生過的瑣屑之事,它們構成了人類的歷史傳承,雖然它們一直在流逝,甚至還在發生的時候就被人遺忘。沉默寡言的攝影師一邊記載著柏林圍牆倒塌這樣的重大事件,一邊自己在捕捉自己的“無名”歷史:它們是腳印、雪地、倒影、形形色色的聲音……研究歷史的學生奧瑞恩吉的研究則和他的捕捉形成一種有趣的回應。如果說阿瑟在捕捉、挽留當下的歷史,奧瑞恩吉則在回溯歷史,試圖捕捉歷史中的“當下”。兩人奇特的交往就如同一首曲子,兩個主題往來交錯,韻味無窮。
壞小說如可樂,爽快而不健康;好小說如陳年佳釀,入口回味不盡。這小說情節並不曲折,甚至有時候顯得沉悶,但是故事卻很有嚼頭,情節所串起來的那些思考最為精彩。這部小說被評論者稱為“思想小說”(anovelofideas)。故事的每個枝節都被作者用來連綴自己的思緒的片段。我最喜歡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館裡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柏林雪地漫步時的遐想。這些聊天和遐想無所不及。《衛報》說諾特博姆在藝術、哲學、語義學和純粹咬文嚼字的胡說八道上都駕輕就熟。澳大利亞《世紀報》(TheAge)則說讀者最好帶一本百科全書來看此書。從奧德修斯的遠航,到尼采抱著驢子哭泣;從馮·賓根的音樂,到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的畫作,作者的思路四通八達。諾特博姆自由穿梭於歐洲的各國文化之間,以至於阿瑟和女博士的戀愛,反成了冰糖葫蘆中間的那根棍子。 有時候這根棍子還不夠用,不足以串起他的思緒,故而諾特博姆還用了幾個章節的畫外音、插入語。在這幾個章節,作家直接敘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開始講述自己的思想。這樣的頗具實驗色彩的夾敘夾議算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沒有明說這些章節的敘述者是誰,是觀察一切的亡靈,還是作家自己?看過電影《柏林蒼穹下》(WingsofDesire)的朋友們一定都對柏林上空的天使印象深刻。這些天使可以看見所有的人間行為,他們知道一切,但是他們並不干預。這本小說穿插的幾個章節就如同這部電影裡天使的視角,也可以說是作家把希臘戲劇里合唱隊的做法嫁接到小說上的大膽嘗試。通過小說中阿瑟的例子,我們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是要直接進入作品,卻又試圖不留痕跡。阿瑟在亞特拉斯山脈南部一駱駝集市上所拍鏡頭中,曾經留下自己的陰影,而他本人不出現在畫面當中,用阿爾諾的話來說,這是“上鏡而不出鏡的一個辦法”。不管這樣做的是作者本人,還是其筆下的人物,這種作者和作品的有趣互動,都讓人尋思良久。如阿瑟自己所想的那樣,他倒不是想搶自己作品的鏡頭,和作品一起不朽。他不過是一個人間萬象的收集者、狩獵者,他收藏意象、聲音,卻又眼睜睜看著它們的流失。他甚至想進入其中與其一起消逝。
諾特博姆小說的文字有時充滿詩意,有時則有濃厚思辨色彩。作家帶著我們在歐洲思想的溝壑和山巒之間奔走。《萬靈節》中的諾特博姆是一個具有大歐洲情懷的歐洲人,他對德國、西班牙文化的了解恐怕不亞於德國和西班牙人自己。他也時刻在思考德國人的懺悔、憂鬱和嚴謹,荷蘭人的敞亮、透明與狡詐的來龍去脈。他眼中的歐洲有時候是一個地形上的整體,“柏林總讓他覺得他是站在一個大平原的中央,而這平原一直延伸到俄羅斯腹地。柏林、華沙、莫斯科,這些都是途中的小站而已”。可是這個整體確實蘊含著諸多不和諧的聲音。“身為外國人,你甚至都不能提‘民主’二字,否則從未參與過殺戮的年輕一輩會警告你不要低估他們的國家,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要。他們會把最近的恐怖事件說給你聽:縱火;某個安哥拉人被人從東德火車上拋下來;某個人拒絕說‘向希特勒致敬’結果差點被光頭黨打死。如果你說這些襲擊實在可怕,實在要去譴責,但是也發生在法國、英國、瑞典”。
諾特博姆也在思考柏林圍牆的倒塌對德國,對歐洲究竟意味著什麼。東德和西德表面上是統一了,然而精神上未必統一。當初統一時種植的熱情種子,最後長成了法爾克廣場那兒歪歪斜斜不成材的小樹。“你可以把柏林圍牆拆掉,但是這牆是不會消失的。”西德人對東德人充滿敵視、猜疑和鄙視。“你還記得當時那歡天喜地的情景嗎?還記得人們在查理檢查站發香蕉的情景嗎?歡迎東部來的兄弟姐妹?你聽過他們最近的談話沒有?老是講他們穿得如何如何,他們言談舉止如何如何。同樣膚色,內里卻有這些種族歧視的話語。老是在說他們什麼什麼不能做,或者是他們如何好吃懶做。‘戰後連我們都沒錢去馬洛卡這些地方度假,他們倒好,成群結隊地去。’‘這些人中間有一半人向國安局出賣另外一半同胞,現在倒好,我們和他們所有這些人捆在一起了。’‘要是照我的意思,柏林圍牆還是不要拆的。’‘不能就這樣把兩個國家捆到一起來,四十年的歷史不能說沒就沒的,他們和我們不一樣。’諸如此類,一個接著
一個說法。”而東德人“覺得自己被人忽悠了”,而兩邊的人都是“對統一簡直一點都不懂。整個國家像裝在盤子上一樣端給了他們,他們卻不知如何下手”。這樣深深的隔閡也如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日漸整合的歐洲之上。統一之後,一樣是背負著各自的歷史,一樣心懷猜疑,一樣相互迴避。想來阿瑟與女博士的愛情,又何嘗不是東西德統一,甚至整個歐洲走向共同體的一個預言!這部作品的翻譯很有挑戰性,其文字常常晦澀難解,作者旁徵博引,也叫人應接不暇。然而這也是和大師過招,過程雖艱苦,卻苦中有樂。在那夜深人靜之時,這個世界上似乎只剩下自己和面前這些文字。翻譯過程中,一些提到的專有名詞譯者略加了注釋,讓有興趣的讀者能及時查考。但為了不影響閱讀,注釋內容有限。書中也使用了拉丁文、俄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等多個語種的文字。為儘量保持作品特色,這些文字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用原文,注釋中給出中文釋義。如再次使用,恐閱讀間隔過久,故用仿宋體,必要時,注釋中再次給出原文。在此書翻譯過程中,得到了眾多朋友的熱心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感謝馬歇爾大學的約翰·霍爾尼亞克先生在我翻譯出現疑難時給予的熱情幫助。感謝住在柏林的黃海星先生在德文上給予的幫助。感謝西班牙馬德里的陸志遠先生在西班牙語和西班牙地名、人名上的幫助和建議。譯林社姚燚老師,說看過我以前翻譯的《河灣》兩遍,實屬知音。受其重託翻譯《萬靈節》,自不敢懈怠。雖明知所有的翻譯相對於原文都是失敗,還盼敗相不是那么難堪。譯文中錯謬和不當之處,懇請原諒!
精彩書摘
阿瑟·唐恩走出舒爾勒書店沒幾步,就意識到有個單詞在他的腦子裡卡住了,而且他已經把那個單詞翻成了自己的母語。他的大腦記起了德文的“歷史”一詞——Geschichte——不過很快又將它翻成了荷蘭語的geschiedenis。不知怎么地,在荷蘭語裡,這個詞沒那么多不祥的意味。他在想這是不是因為這個詞的後綴“nis也是“niche”(壁龕)的意思。怪詞一個。簡短的詞兒。簡而不略,短而不矬,反倒是讓人覺得寬慰,和其他那些短詞大不一樣。畢竟,壁龕是個讓人躲藏的地方,是個可找到藏著的東西的地方。其他語言裡沒這個意思。他開始加快步伐,希望藉此忘掉這個詞,不過這個小招數並未見效,反正在這裡不行,在這座城市不行,因為柏林的每一寸土地都浸在歷史當中。這個詞將會很難忘記。最近,有很多詞卡在他腦子裡了。“卡”這個說法絕對到位:這些詞一旦進了他的腦子,就穩穩噹噹停在了那裡。他還能聽到這些詞:這些詞似乎有個與之相伴的聲音,哪怕他並沒有大聲把它們說出來。有時候它們甚至還有回音。你把它們從它們所屬的句子鏈里拔出來,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敏感的話,它們會變成一種十分古怪的東西,會變得很可怕,你最好不要把玩太久,否則世界會從你的腳下滑走。這都是閒得慌,他想。不過,他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這個樣子。他想起在一本舊課本上看過的關於爪哇人的故事,故事中的爪哇人每當掙到兩毛五分錢的時候,就跑到棕櫚樹下坐著。在那些遠去的殖民時代,兩毛五顯然夠花上一陣子的,因為這人要等這錢花得一分不剩的時候才回去工作。書里說,這一做法讓人噁心,因為你不肯辛苦勞動,哪裡會有進步呢?阿瑟·唐恩風光過。他曾自己當導演,自己當製片,製作過電視記錄片,要是題材夠有意思,他還會親自上陣來攝影。每過一陣子,要是缺錢,或者心情好,他還會給朋友的公司拍拍廣告。要是不經常拍,還是很有意思的。每完成一單後,他就給自己放放假,悠哉幾天。過去他有妻子,也有個孩子,但是他們在飛機失事中死了。他只剩下他們的照片,每次看的時候,都覺得比以前更遙遠了。都過去十年了。有天上午,他們出發去馬拉加,結果就再也沒有回來。這種場景他拍過,卻沒有親眼見過。那金髮碧眼女子,背上背著孩子,小男孩。史基浦機場,排隊驗護照。事實上,這孩子不小了,都不應背著了。他叫她的名字,她轉身。定格,回憶。他們站在那裡,呈九十度角,整整一秒鐘。她抬了抬手,小男孩也揮了揮手,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