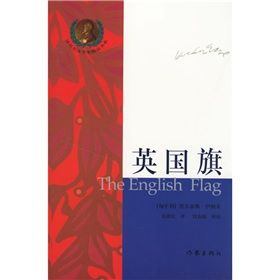內容簡介
從小說的“素材”和小說的結構來看,《英國旗》是《慘敗》以及《為一個未出世孩子的哭禱》的繼續……可以這么說,《英國旗》含括了凱爾泰斯寫作技巧的最典型、最基本的特徵因素。在小說《尋蹤者》中,作者借用卡夫卡式的文學手段處理了一個十分沉重的主題……然而對人或物的處理上,所表達出的並不是卡夫卡式的困惑,而是一種悲劇性的解脫。本書的閱讀是一次孤獨的、震人心魄的心靈歷險。從一開始我們就被“英國旗”這個懸念緊緊地抓住,跟著主人公經歷了一次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心靈歷險。我們和主人公一起在發放“肉票”的時代吃了“不用肉票就能吃到的牛排”,作為一個弱小個體對社會的、脆弱無力的象徵性反抗;我們和主人公一起參加了那個時代日復一日、充斥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政治學習,一起目睹了一個革命者被革命者專政的困惑一幕;我們和主人公一起做了被臨時假釋的鐵欄外的囚徒,忍受著那些瘋狗一樣歇斯底里的狂吠;我們和主人公一起聆聽了那場動人心魄的歌劇《武神頌》,在歌劇院包廂的紅色簾幕後偷享著“非法的自由”……我們和主人公一起望見了那面裹在一輛吉普車車頭的“英國旗”。
作者簡介
凱爾泰斯·伊姆萊,1929年11月9日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歲的凱爾泰斯被投到德國納粹設在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又被轉到了德國境內的布亨瓦爾德集中營,直到1945年被蘇軍解放。1946年在布達佩斯《火花》報社開始了最初的記者生涯,1953年開始自由撰稿人的寫作生涯。先後寫過三部音樂輕喜劇,並獲得成功。六十年代初,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命運無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時代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為素材創作的自傳體小說《命運無常》經過了近十年的輾轉努力,終於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譯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維根斯坦等。
1977年發表兩部中篇小說《尋蹤者》和《偵探故事》,之後相繼出版長篇自傳體小說《慘敗》、《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哭禱》,中篇小說集《英國旗》,日記體文集《船夫日記》及《另一個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語言》與電影劇本《命運無常》等。
曾獲德國布萊登圖書大獎,匈牙利最高國家文學大獎——科舒特獎,德國語言與詩歌學院一等獎,萊比錫書展大獎,德國國家最高文藝獎等多項國際大獎。
200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目錄
他為人類的墮落作證(序)一誰是凱爾泰斯
二他對自己也感到陌生
三尋找失落的命運
四他為什麼要表述
五我曾經是凱爾泰斯
六他是孤獨的證人
七一個永遠的精神流亡者
八他是“另一個人”
英國旗
英國旗
筆錄
尋蹤者
做客
另一個人
命運無常
第一部分
1.黃色六角星Ⅰ
2.午飯
3.樓道里
4.告別
5.通行證Ⅰ,母親
6.通行證Ⅱ,弗萊什曼家
7.禮物
8.黃色六角星Ⅱ
9.拘捕
10.白天,兵營內。檢查
11.夜裡,憲兵營內
12.火車Ⅰ,燒磚廠的一組場景
13.火車Ⅱ,夜裡,車廂內
14.一個陌生的地名
第二部分
場景
納粹集中營
1.分組
2.臨時工棚的牆邊
3.布亨瓦爾德Ⅰ
4.布亨瓦爾德Ⅱ。月色皎潔的夜晚
5.澤伊茨。茨特羅姆?邦迪。耳光
6.灰色工作日
7.這是最可愛的一個小時
8.木匣里的思考
9.飢餓狀態Ⅰ
10.飢餓狀態Ⅱ
11.水泥Ⅰ
12.空襲
13.水泥Ⅱ
14.逃犯
15.泥沼
16.中斷
17.影子
18.膝蓋
19.洗澡
20.醫院。飢餓狀態Ⅲ
21.寄生蟲
22.重返布亨瓦爾德
23.三個片段
24.死亡邊緣
25.淋浴噴頭
第三部分
回家
1.奇蹟
2.末日
3.出發
4.抉擇
5.分界線
6.失落的命運
聾啞人的吶喊(後記)
瑞典學院對凱爾泰斯?伊姆萊的褒獎詞(全文)
凱爾泰斯?伊姆萊獲獎演說
找到了!
凱爾泰斯·伊姆萊主要作品
凱爾泰斯·伊姆萊所獲文學獎
精彩書摘
英國旗“……我們的前面是霧,後面是霧,腳下是一個沉陷的國家。”
——巴比契·米哈伊
幾天前——也許是幾個月前——有一群朋友極力鼓動我將這個“英國旗”的故事講出來。假若我幾經思忖,最終還是想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話,那就必須要提一下那本曾使我第一次對“英國旗”萌發感受的讀物,可以這樣形容:那種感受是一種令人齧齒的驚嘆。我要講述一下我當時讀過的書籍,以及我讀書時所懷揣的激情,我要講述一下自己攝取養分的源泉以及取決於什麼樣的偶然性——這就如同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隨著光陰的流逝,我們最終還是了解了我們自己的命運,不管我們所了解的是命運的既定結局,還是命運的無可理喻;我必須要講述一下這種激情究竟是在何時爆發,最終又導向了何處。總而言之,這幾乎需要我講述自己的整個一生。因此,要想講述一個這樣的故事幾乎不大可能,這不僅由於需要有充足的時間,還由於自己對許多事物了解的匱乏。因為,世界上沒有誰能夠僅僅憑著自己所擁有的、尚且迷惑的體驗,就認為自己已經了解了生活,就認為自己看透了這個對他來說——而且特別是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生活旅程,就認為自己了解了生命的過程與出路。因此,要講述這個“英國旗”的故事,我最好還是從理察·華格納開始。從理察·華格納到“英國旗”,雖然有著一條貫穿始終、微妙而確鑿的主線,但是,要講述理察·華格納這個人,則先要從編輯部講起。今天,那個編輯部已經不復存在,而且不僅是編輯部不存在了,就連編輯部所在的那幢房子也早已蹤跡全無。曾幾何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準確地說,是在戰後的三年里),當時的那個編輯部,對我來說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存在——晦暗的走廊,積塵的角落,嗆人的煙瘴,赤裸的燈泡照射著狹小的房間,房間裡總響著電話聲、叫喊聲和急促惱人的打字機聲,並被某種短暫的興奮、持久的焦慮、變幻無端的氛圍,以及那種從各個角落滲出並迅速籠罩住一切的死氣沉沉的恐懼灌得滿滿的。那時候,我總要痛苦地在一個相當早的時刻——每天清晨七點整——到那個現在早已不復存在了的編輯部去上班。當時,我究竟懷了怎樣的希望?——在那個極力鼓動我將“英國旗”的故事寫成小說的朋友群中,我坦白地大聲提出了這個已經深思很久了的問題。我們由於幻覺的作用,所有的人都處於一種被動而坦誠的狀態,於是,我將那個大約二十歲的年輕人認成了、或者說是感受成了“我自己”,現在回想起來,真好像是在看一場電影。想必正是由於這種幻覺的作用,他——或者說是我——也仿佛是在電影中審視他自己(我自己)。另外,這個故事顯然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能夠被人講出來,否則的話,它也會跟其他所有的故事一樣變得無法表述,或者說根本就不曾發生過;即便有誰能夠以某種方式將它講出來,而那個被講出來的故事恐怕也會恰恰跟那個真正想講的故事相矛盾。我覺得,惟獨這條生命——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的生命“可能用語言講述出來”;也惟有這條生命,伴隨著其緊張的神經以及所有痙攣的希望一起,漂泊在一個“可能用語言講述出來”的層面上。這條生命,始終在殫精竭慮地為了生存而希望,而且總是與我今天所懷抱的希望以及我今天所能用語言做出的表述相衝突,總是接連不斷地宣告慘敗,總是接連不斷地陷入無法用語言表述的窘地,總是以“無法用語言表述”的無奈與想“用語言表述”的希望相較量(當然,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徒勞的)。不,在那個地方,在那個時候,這種想“用語言表述”的希望恰恰導向了一個目的,就是要將那種“無法用語言表述”的無奈(或者說要將其生命的本質)隱在朦朧之中,就是要將那條在黑暗中躑躅、在黑暗中摸索、並拖著黑暗之沉重的生命隱在朦朧之中。因為,這個年輕人(我)只有這樣才能夠生存下去。我通過閱讀、通過自我存在層面的表層肌膚接觸世界,仿佛隔了一層防護衣。那個由於讀書而被削弱、而被遠離、甚至被摧毀了的世界,曾經是我的一個雖然虛假卻可以獨自為生的世界,甚至有時是我可以承受的世界。因此,對於那個編輯部來說,我最終失蹤的那個瞬間,是一個可以預料的結局,因為……也可以這么說,我的失蹤只是對那個社會而言——假若那個社會確實曾經存在過的話,或者說,假若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東西確是社會的話——對於那個社會來說,我失蹤了。有時,我像一條被人暴打的狗一樣“嘶嘶”哀吟;有時,我像一匹飢餓的土狼一樣“哞哞”嗥叫;而對於那些餓瘋了的丐幫來說,我永遠是一堆可以被廝咬的食物;對於我自己來說,我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失蹤了,甚至險些喪掉了性命。但是,即便在我生活的低谷——至少在當時,在我尚未墜入後來的一次次越來越深、深不見底的低谷之前,我這樣認為——即便在這個低谷里,仍然存在著“可以用語言表述的可能性”,就像是一架攝像機,就像是一個正在改拍的一部庸俗小說的攝影機鏡頭。但是,至於這部影片我都在哪兒拍過?片名到底叫什麼?講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都一概不知。現在,我早就不讀那類無聊的閒書了,原因是有一回,當我翻看一本庸俗小說的時候,忽然捕捉到一個突如其來的閃念:我根本不在乎到底誰是小說里的殺人犯。在這個充滿殺戮的世界裡絞盡腦汁地琢磨“到底誰是殺人犯”,這不但使人困惑、使人惱火,而且還毫無意義,因為: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是殺人犯!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當時,我根本未曾想過使用這種措辭來表述,也未曾透視到自己四十年前所懷揣的希望的現實價值。其實,那是一個事實,是許許多多雖然簡單之極但顯然又不是最無關緊要的諸多事實中的一個,我不僅曾在那個環境中生存過,並且必須要生存下去(因為,我想活著)。在我看來,故事中這個嗜好歷險的男主人公——大概是一位私人偵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每當他準備投入一次需要冒生命危險的行動之前,總要用一小杯威士忌、一個女人或者用其他的什麼來“犒勞一下自己”。有的時候,他則鑽進汽車,衝上國家公路,一陣盲無目標、狂不可遏的疾馳也能夠使他滿足。這部偵探小說教給了我一個道理,在持久的煎熬之中偶然會有短暫的間歇,在那一刻,人們需要瞬間的愉悅: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膽量像現在這樣表述,即便有過,至多也是作為一種罪惡來表述的。在那段時間裡,編輯部里瀰漫著死亡的威脅,更確切地講:那是一種要命的無聊,這種無聊也不亞於致命的危險,每天的無聊都是新的,而每天的無聊有時又同出一轍。在那段時間裡,經過短暫的、毫無原由的間歇之後,又會繼續發放一些主要用於肉食品定量供應的“副食品券”。然而,這些“票券”——尤其是“肉票”——的發放簡直就是多餘的,因為,投入市場的肉食品數量遠遠少於所發放的“肉票”數量。當時,在編輯部隔壁新開了、也許是重新開了一家與“卡爾文百貨商店”同名的餐館——“卡爾文飯店”(由於這家店的主人是外國人,所以那裡的經營也自由些:因為這家店歸屬於占領者所有),這裡不但可以買到肉,甚至可以不用“肉票”就買到,不過,這裡的肉價要比市場價高一倍(或者說,假如其他地方也供應肉食品的話,這裡的肉價要比其他地方貴一倍)。那時,我一旦預感到在編輯部里又有某種“無聊之極的致命危險”正在窺伺著我——人們通常體面地稱之為“開會”——我就會提前“犒勞一下自己”,去“卡爾文飯店”吃一塊炸肉排(我經常將提前領取的下月薪水也透支出去,這就跟工資預支制度一樣,也變成了一種“制度”。但是,顯然由於某種健忘症,即便在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早已然失效之後,而這個“制度”卻還會繼續生效)。無論我將面對多少、無論我要面對何種“無聊之極的致命危險”,我都會有意識地先“犒勞一下自己”,可以這么說,這是我的一種準備,一個秘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自由意識。而這種自由意識,潛藏在我不用“肉票”就可以買到的炸肉排里,潛藏在我每個月預領的工資里,除了我,沒有人可以知道它;頂多是那個跑堂,但是他知道的也只是——我吃的炸肉排;頂多是那個收款員,但是她知道的也只是——我預支的工資。就這樣,這種“犒勞”幫我超脫了那一天所有的卑賤、羞恥與侮辱。在那個時期的每一日每一天,每一個從日出到日落的日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