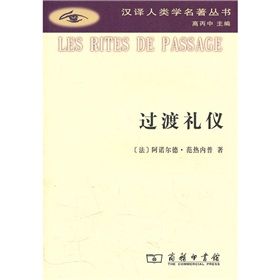內容簡介
出生、結婚、懷孕、死亡、季節轉換等地位變化的事件,往往會以過渡禮儀來加以標識。這部首版於1909年的著作,對儀式機制和人類行為研究的貢獻是多方面和意義深遠的。正如當代美國著名民俗學家鄧迪斯所評價的,“也許可以公平地說,民俗學分析性著作對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沒有一部可超過這一經典研究。”
目錄
作者的話1第一章禮儀分類2
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個體人生階段;禮儀研究;泛靈論學派與感染論學派;動力論學派;禮儀之分類:泛靈性與動力性,感應性與感染性,主動性與被動性,直接性與間接性;過渡禮儀模式;神聖之概念;宗教與巫術
第二章地域過渡13
前線與邊界線;過渡之禁忌;神聖區域;門、門坎、門梁;過渡之神靈;進入禮儀;奠基祭祀;啟程禮儀
第三章個體與群體22
陌生人境況與特性;陌生人之聚合禮儀;共餐;作為聚合禮儀之交換;兄弟結盟;問候禮儀;性交聚合禮儀;陌生人之安宿;旅行:分別禮儀與回歸禮儀;收養;主人之改變;爭吵、血仇、和平
第四章懷孕與分娩34
迴避、禁忌、預示與感應禮儀;處於邊緣期之懷孕;再結合禮儀與社會地位恢復;分娩禮儀之社會特徵
第五章誕生與童年41
臍帶切割;誕生前胎兒位置;分隔禮儀與聚合禮儀;印度、中國;命名;浸洗;向日月敬獻
第六章成人禮儀51
生理成熟與社會成熟;割禮;身體肢解;圖騰氏族;巫術一宗教性組織;秘密社會;政治社會與戰爭;年齡段;古代神秘禮儀;共同宗教:浸洗禮;宗教派會;聖女與神娼;階層、等級、職業;神父與巫師之神職授予;酋長與國王之加冕;革除與排除;邊緣期
第七章訂婚與結婚87
處於邊緣期之訂婚;構成訂婚與結婚儀式之禮儀種類;婚姻之社會與經濟特徵;處於多妻婚與多夫婚之邊緣;分隔禮儀:視為掠奪婚或強姦婚之禮儀;特定性交團結禮儀;基於父母之團結禮儀;本地團結禮儀;分隔禮儀;聚合禮儀;邊緣期之長度及其意義;集體婚禮;結婚儀式、收養儀式、加冕儀式及成人儀式之相似;離婚禮儀
第八章喪葬·107
分隔禮儀、邊緣禮儀與聚合禮儀在喪葬儀式中之相對重要性;作為分隔禮儀與邊緣禮儀之祭喪;喪葬的兩階段;此世至彼世之旅程;死亡過渡之地域障礙;向亡者社會之聚合;冥世構成;古埃及亡者之每日復生;冥世之眾多;不符合冥世常規之死亡;再生禮儀與輪迴禮儀;為亡者下葬、建墳或墓地之禮儀;分隔禮儀與聚合禮儀之列舉
第九章其他類型過渡禮儀121
可單獨考慮之若干過渡禮儀:1)頭髮;2)面罩;3)特別語言;4)性行為禮儀;5)鞭打;6)首次;年令儀式、季令儀式、月令儀式、日令儀式;死亡與再生;祭獻、朝覲、發誓;各類邊緣;古埃及對應之儀禮體系
第十章結論137
索引142
附錄:部分術語譯名對照表150
譯後記·153
前言
學術並非都是繃著臉講大道理,研究也不限於泡圖書館。有這樣一種學術研究,研究者對一個地方、一群人感興趣,懷著浪漫的想像跑到那裡生活,在與人親密接觸的過程中獲得他們生活的故事,最後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開始有條有理地敘述那裡的所見所聞——很遺憾,人類學的這種研究路徑在中國還是很冷清。“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民族國家都要培育一個號稱“社會科學”(廣義的社會科學包括人文學科)的專業群體。這個群體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無論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個本分,就是把呈現“社會事實”作為職業的基礎。社會科學的分工比較細密或者說比較發達的許多國家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發展出一種扎進社區里搜尋社會事實、然後用敘述體加以呈現的精緻方法和文體,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義是指對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現象的記述,希羅多德對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險家的遊記,那些最早與“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傳教士以及殖民時代“帝國官員”們關於土著人的報告,都被歸入“民族志”這個廣義的文體。這些大雜燴的內容可以被歸入一個文體,主要基於兩大因素:一是它們在風格上的異域情調(exotic)或新異感,二是它們表征著一個有著內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體(族群)。
精彩書摘
一個社會類似於一幢分成若干房間和走廊的房子。某社會文明形式與我們所處社會越接近,其內部結構劃分就越精細,而互通之門則越寬敞。反之,在半文明社會,每個區段都被精心隔離開,相互過渡必須經過一定形式和儀式,其方式與上一章所論述之地域過渡禮儀極其相似。每一個體或群體,在沒有通過出生或特別獲得的手段而具有進入某房屋的權力,並立即成為該區段之常規成員前,是處於一種隔離狀態。這種隔離有兩層意義,或分開或合併在一起:該個體很脆弱,因為他處於特定群體或社會之外部;但他也很強大,因為相關群體之成員構成世俗世界,而他處於神聖范疇。因此,處於此狀態之群體成員便可殺戮、搶掠和虐待一個陌生人而不經儀式,①同時其他成員懼怕他、恭敬他,視他為具有超強力的生靈,或施用巫術一宗教之法以防禦他。
陌生人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是神聖的,具備巫術-宗教性力量,並擁有超自然之仁慈或邪惡力。這一事實已被反覆提及過,特別是在弗雷澤②和克勞利③的著述中。他們都認為這種禮儀的起因是陌生人因其出現而受制於巫術-宗教性之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