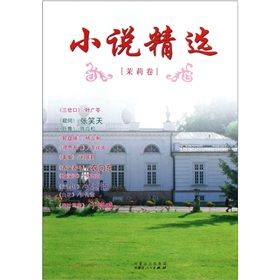目錄
三岔口窺伺
巨獸
輪盤賭
尋死無門
美發
養父養母
夜深沉
逆時針
白花
羽葉蔦蘿
精彩書摘
1少年時對革命嚮往異常,至今尚未疲憊,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與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著打仗,想的是若能趕上紅軍長征,趕上八路打日本,趕上三大戰役解放全中國,我一定是紅軍,是八路,是解放軍。只可惜,生不逢時,解放軍們在東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區浴血奮戰的時候我還在穿開襠褲,沒有參戰的資格。我讀國小二年級時,暑假學校組織讀書會,每人發一本小冊子,讓大家在樹底下圍成一圈,輪流朗讀。冊子上說的是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女英雄劉胡蘭的故事,冊子封面的劉胡蘭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緊緊地抿著,短頭髮被風吹得揚起,英俊而瀟灑。扉頁里有毛主席的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那字寫得比我們終日描紅的字型漂亮多了,流暢而舒朗,跟劉胡蘭的頭髮一樣,高高地飛揚著。畫面上劉胡蘭的脖子硬硬地梗著,很長,很美。我想,敵人用鍘刀把這個美麗的脖子切斷了,劉胡蘭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還在堅持,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若換了我大概不會如此鎮定,至少我不會把脖子亮得這樣開,因為那是“數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敬佩劉胡蘭,認為她是天下最堅強最偉大當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離我們很遙遠,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特點是喜歡把我崇拜的人隨時向人介紹推薦,比如花木蘭,比如諸葛亮,比如孫悟空和武松,但他們都不能和劉胡蘭比,因為他們都不是被敵人殺害的,劉胡蘭是被“勾子軍”當眾殺死在村口的,臨死還怒斥敵人,所以劉胡蘭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體表現是將封面的劉胡蘭在圖畫紙上臨摹放大,然後拿到老七那兒去上顏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畫家,他有這個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絕,老七說這是版畫,版畫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顏料往畫上塗的。道理說了不少,反正是不給上色。他不給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誰差,我們家裡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時候還沒有“彩照”一說,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館有專門上色的師傅,也賣塗抹照片的專用顏料。我曾經用那些顏料將父親工作證上的照片塗成了藍臉,父親看了說他成了《西遊記》里的妖怪“奔波兒霸”了。我也將穿著婚紗的老二媳婦照片做了塗抹,給新娘子塗上了紅嘴唇,使新媳婦像剛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種顏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婦再也不跟我說話了。那天我拿著畫像到母親那兒去告老七的狀,母親看著劉胡蘭的畫像說,這不是你三姐么!
我說這是劉胡蘭。母親說,我以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這個模樣。
我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動派殺害的,與劉胡蘭不同,不是鍘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勝門外的城牆根底下。敵人沒用鍘刀,連子彈也省了,挖個淺坑,讓人躺在裡頭,蓋上土就完了。後來聽說行刑的時?是在黎明,天將亮,非常的秘密,不像電影裡演的,周圍有鄉親,還有大狼狗,他們四周什麼也沒有,只有黑沉沉的城牆和寒冷的北風,他們也沒喊口號,連點兒聲息也沒有,靜悄悄地死了。殺了他們沒幾個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書上的話說是他們“已經見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後政府通知我們家去收屍,是母親和老七去的,兩人回來一身土,兩腳泥,眼睛通紅,連廚子給熬的小米粥也沒喝一口。母親對父親說,三、頭的屍骨已經腐爛,無法辨認,地上三排亮著幾十具遺骸,都用草席蓋著,鼻子眼睛爛成了黑窟窿。
後來母親是從一隻沒?爛完的鞋上認出三姐的。那是一隻千層底的黑布鞋,鞋上繡了一朵小梅花,是我們故去的第二個母親的手工,三姐離家的日寸候穿的,走的時候跟母親說是上西山郊遊,特意脫下皮鞋換了布鞋,一走就再沒有回來……
烈士們的遺體由國家統一安葬了,三姐沒有埋在烈士陵園,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墳地里,小小的一個土堆,連墓碑也沒有。除了門框上掛著的“革命烈屬”那塊藍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沒有給這個家庭留下任何痕跡。父母親在處理三姐的後事上相當低調,他們退回了那一筆相當可觀的撫恤金,說汶錢?閨女用命換來的,花著傷心……不要。
我跟同學們說我的三姐跟劉胡蘭一樣,也是為革命犧牲了的,同學們不以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後代”們,他們認為劉胡蘭就是劉胡蘭,誰與劉胡蘭比誰就是不自量!我心裡不禁暗暗為我的姐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沒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給我的三姐題字呢?
國小校的隔壁是某機關大院,同學中不乏幹部子弟,他們自成圈子,玩的遊戲,談論的事情也和我們不一樣。他們視我們玩的“跳間”、“拽包”、“抓子兒”為不屑,稱我們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幹部子弟相提並論的,子弟們的優越感顯而易見,連老師跟他們說話也特別的輕柔,特別的小心。胡同串子們動輒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請家長”。我們的家長也很不值錢,老師一叫,趕緊屁顛兒屁顛兒地來了,孫子一樣地聽訓,回家對“串子們”便是一頓臭揍。老師不敢請幹部子弟的家長,他們的父母都是如雷貫耳的人物,我敢說,哪一個都比校長級別高,更別說我們那個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過隊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參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參加女兒的隊日,本身有點兒怪,這事擱“胡同串子”身上是絕無可能的,甭說我們的爸爸想不起參加我們的隊日,就是想起來了也不會跟著一群孩子瞎起鬨,白耽誤工夫。對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師竟然答應了,還有點兒受寵若驚,還給校長匯報,這讓我很看不起她,因為她對“子弟們”的要求從來不敢拒絕。第二天我們舉著中隊隊旗步行到北海後門,雷小蕾的爸爸已經在門口等著了。雷小蕾的爸爸隔著馬路向我們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說她爸爸是坐專車來的。我說我父親過去也有專車,大馬拉的專車,帶絲絨座玻璃窗,是從外國進口的。雷小蕾想也沒想就說,你爸爸原來是趕大車的呀!
正巧,過來一輛騾子拉的大車,車上裝滿煤炭,趕車的人和拉車的騾子都是眉目不清,黑頭黑腦的,“子弟們”便指著車說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聲喊:是趕車的還是拉車的呀?
眾人一陣鬨笑。
掬盡三江水,難洗一面羞。其實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討沒趣。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幾次以後,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眾中屬於另類,得隨時收斂著,蜷縮著,不能逞強。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鴨店的師傅叫到家裡做烤鴨子,也得說“壓根沒見過熟鴨子是什麼模樣”;明明老張是看門的,莫姜是做飯的,劉媽是打掃屋子的,跟同學們也要把他們說成是“院裡鄰居”。在性格和心靈上都有些扭曲。這種扭曲一直延續了我的大半生,鑄就了我內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獨處時往往覺出難耐的惆倀,混跡人群,談笑風生中,內心深處也常常泛起難堪的孤獨,由不得自己,是小時候坐下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