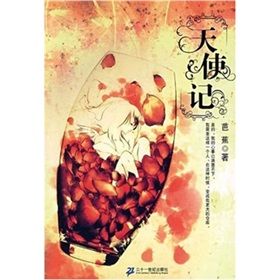內容簡介
我希望他們沒有。那樣他們才會變得很簡單容易,他們才能穿上白色的衣裳而不去弄髒,他們不會在乎太多東西於是長生不老。最後他們都因為活得太久而選在某一時辰去氣絕身亡。
我想我多多少少遇見過一些這樣的東西,在我好的時候,也有在我很糟糕的時候。
只是在最近,在這樣一篇小說過程中,我卻是萬念俱灰的。我原以為我是一種無論何時都可以徹底放棄的人,但現在卻開始有點不同了。
這樣的一篇文字是用來告別的,將我的生活告一段落,只是我不想用生命去嘗試什麼,無論怎樣,我在此絕望過,死亡或歡樂天使都曾經落於我的身側,我希望我以後會記得,起碼要記住當我牽上他的手那一瞬間的感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當時我所感受到的溫暖,並與我一同記住。
誰讓我的記性是如此之差呢。
作者簡介
芭蕉,“可能在我血液中與生就附帶著那些暴力的鮮紅色彩,但作為女人。我有一張無辜又善良的臉遮掩著那部分邪惡。”——我有志做一個忠實並且傳神的文藝女青年。做一個熱愛生活卻又神思恍惚的美人兒……這是全人類(女)的志向啊!而且我堅信,越無法實現的夢想越高貴。哪怕再沒有人期待我的未來。我也希望能看見自己的下一本小說。曾出版小說:《水妖》《初纏戀後》、《天使記》、《迷幻主義和戀愛猜想》媒體評論
——告訴你,天空一定會為你準備一位天使,只要你在絕望以前,耐心等待……《映色·風向標01:天使記》是《花溪》雜誌原主編芭蕉的《天使記》,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佳作,沉寂已久的芭蕉,再現現實中的非現實!告訴你,天空一定會為你準備一位天使,只要你在絕望以前,耐心等待……
目錄
天使記楔子
第六感惡作劇
下雨天
有關對煜和小井的補充說明
天使是誰
有關生活的另一篇
偶然
切膚之痛
災難的發生
別人的童話
兩極光
醉生夢死酒
紅塵遺事
尾聲壹·杜秋&杜生
尾聲貳·天使
精彩書摘
1.楔子有天晚上,極想找回寂寞的那種感覺,這樣的念頭一旦被排山倒海地撲過來,我終於知道:那將再不可能,再也不回來了。
我吃了幾天減肥藥,常常都心不甘情不願地坐在馬桶上愁腸百轉,像個苦命的孩子。媽媽看似睡下,但黑暗中卻瞪視著我箭步飛竄在電腦與廁所之間,廁所的燈都壞了,我大開著門,一邊拉屎一邊回瞪著整個世界,整整一個世界呵,都在這樣面面相覷么?
鳳凰發了半截小說給我看,當讀到“我在上海極好的月光下,或是輕風細雨中,或是在淡淡的夜霧裡,自南京西路走到茂名北路,回一家叫做海港賓館的酒店去;後來搬了處住,於是又在這樣或那樣的夜色里自南京西路向北京西路走,在那裡有我的公寓。”時,我被深深打動,仿佛她正在我面前行走,有起點到終點,甚至可以聯想到所有當時擦身而過的行人,我忌恨這樣對一段路程始終倒背如流的方式,連每個路牌都能在腦袋裡紮根,慢慢長成一棵雷打不動的回憶樹。
而如果這時我從勁松西街走到南街,我只能告訴你,我什麼也沒有做,天氣是天氣的事,馬路是馬路的事,賓館是賓館的事,我也有我的事:只不過是走走而已。可這些東西就無法長成樹,縱使今天被記錄下來,它仍然不會是樹,因為我不能讓自己的大腦變成森林,我不能讓自己的心中有春風秋雨,因為會很容易被我聯想成“血肉橫飛”或“腥風血雨”。
我只是想一個人,一直都是一個人,存在於某地,只生長一棵樹,用來靠著乘涼,只下一場雨,不會被渴死。我還想是個天使,這樣就會變得很傳神,但又無人敢惹。
我打電話問鳳凰:什麼時候你會認為自己是天使。
鳳凰說:生病的時候。
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她變瘦了,就會模仿飄浮狀。於是我又想到上廁所,什麼時候可以上廁所上到很High,那就人人都可以當成天使了。
好了,我可以告訴你關於寂寞的緣起了,我的寂寞啟蒙於兩歲那年,我還住在爺爺家的大院裡,四周空曠,奶奶買菜前把我牽到院子門口的板凳上,說:小易,你乖乖坐在這裡,奶奶沒有回來你千萬不能動。
我一聲不吱地坐了三個小時,忘我地沉浸在一個人的等待過程中,連褲子都尿濕了,最後得到嘉獎和訓斥摻半。這樣的事其實早在我腦海里蕩然無存,但卻在長輩那裡長成大樹,當他們偶爾津津樂道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自己在那么早以前,那么早以前就讓自己執著於寂寞。
這並不是什麼悲哀的事。悲哀在於,人們都在玩味它、解剖它,幾經審視之後對我說:小易,別難過,我們一直都在你身邊。
更悲哀在於,我曾經對另一個人說:別難過,我一直都在你身邊。
而他掀起那張小木桌對我怒吼:滾,你滾,我最討厭的就是你一直在我身邊,真他媽噁心。
看,他把我歷年來最想說的話沖我吼了出來,我的喉管上下幾次沒能咽下氣急敗壞的口水,被噎了住,接著便附帶著連陳年食物和肝臟吐了一地,還吐在了他那雙半乾不淨的球鞋上。
之後我們就分手了。我和小井戀愛花了兩年,分手只用兩分鐘,我自己走路回家都需要半個小時,這樣一計算起來,愛情就顯得格外驚險,在我孤單而空蕩蕩的心裡便想:如果發明比光速快的東西就可以回到過去的話,那么用愛情飛走的速度也可以讓時光倒流吧。
而如果時光真的會倒流的話,就讓現在的我去和過去的我作伴,讓倆個我相親相愛的生活,生活在一個混淆不堪的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別人。
離開小井之後我還是很為他那句決絕的話而激動,就仿佛自己也從中發泄了一遍,我在腦海里假想了一大堆人物讓他們並列在那兒,而那句話便藉由小井的口中向他們吼出。一想到此,我失戀的心情立即為之振奮。
但難過在於反思,反思的時候我便想:我為什麼要對他說那誓言般的話,我真的就想陪在他的身邊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諾諾才會提醒我,她認為我有時太成全他人,因而讓自己年復一年的被動又沮喪。但沒人會領情。她說。
她說:雖然你誠懇,可是並非真心,沒有人會傻到相信你。
我就真的那么不值得相信?
她肯定地點頭:但你還是個好人。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對她說。
這世上的確沒有人會知道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對我說。我堅信這點,並把它當作砝碼任性的為所欲為。
沒過多久就聽說小井因為倒賣汽車入獄的訊息,那段日子我暴飲暴食胖了八斤,接著又忙著張羅起減肥,媽媽也選在這樣的時候搬來和我同住,而另一間房也同時借給一個叫諾諾的女孩。這一切都接替了小井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不得不分給它們一席之地,在我媽初來乍到的第一天我就對她說:你住在這裡沒關係,但要是想妨礙打擾我的生活遲早會被我趕走。
我媽說:除非你不是我女兒。
我也想不是,但這話我沒敢說出口,如果要說真話我可不希望自己是任何人的女兒,我想我本就該是一介天使,閉月羞花的長在某個地方,不用吃喝拉撒睡,不用背叛或遭人背叛,不用遺棄或遭人遺棄,甚至一句話都不用說就能生生不息。
顯然這一切都不可能。於是我媽心安理得的在我身邊住下了,她先是把這套房子改造成她所希望的那樣,不到一周的時間,屋子裡便鋥亮可鑑窗幾明淨,所以想要的東西都伸手可及,她讓這個破舊地方變得熱氣騰騰美滿和樂。諾諾的房間更是一派德國式的宜家風格,她和我媽勢不兩立,而我只好退居到最後一片領土上去,那就是我的電腦桌——只有我的電腦桌還和從前一樣的髒亂,因為媽媽怕這些糾纏不清的線頭,怕被當中的某一根突如其來地擊中。
我上網遇到鳳凰,她仍在為她的新小說忍受批評,痛苦得不得了。我也說:我看不懂你寫了什麼,你要玩深沉了,可我還在表面呢。
她悻悻地說:你退步了。
為了避開這個話題,我問她:你看見Renee沒有?
她說沒有。Renee在美國,用她的白天上網,在我媽沒來的時候我把自己過成美國的鐘點,有時和Renee可以聊上兩個小時的天,她是個非常有趣的人,對某些觀點百折不撓,但又顯出很困惑的樣子,一直到對方變得比她還困惑的時候她就樂不可支地下線了。所以我一般不參與她的爭論,我從一開頭就對她持讚賞態度,讓她樂不可支又心懷遺憾地下線。
可我最近已無力遇見她了,因為我媽到了更年期,因此我必須每天晚上十一點以前就上床,早上七點按時睜開甦醒的眼皮,九點步行去上班。我在規規矩矩地做人,認認真真養家。
第二天清晨我又坐在馬桶上,腹如刀絞四肢冰冷,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知自己這是怎么了。僅僅只是拉個肚子,其它器官也值得這么隆重嗎。媽媽猛然間探進腦袋好奇又擔心地問:怎么這么半天出不來?
我的肚子立刻好了,傻傻地坐在原地,不知是穿上褲子呢還是不穿的好。
大概就是在這一天,因為是周末,我被媽媽拉到表舅家裡做客,他們為我介紹新的男朋友,那么,出於禮貌與尊敬與被鎮壓後的卑恭,我又要開始談戀愛了。
2.第六感惡作劇
我和莊同相親的那一面,他認為我是瘋子,我認為他是傻子。
這沒什麼,我觀察了一番覺得正是天作之合,可他從開頭就避我惟恐不及。吃過晚飯後奉長輩命他帶著我去玩,聽聽看吧——“去玩”,我今天二十七歲,莊同據說二十八了,他們還能大言不慚地拋下這樣的話來,於是在餐廳的門口烈烈風中,莊同戰兢地問我:去哪玩?
我說:遊樂園啊。
他渾身一哆嗦,指著夜幕驚叫起來:遊樂園?
我說: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玩的?
玩哪……他側頭開始想。
床上。我又提醒他。他又被嚇了一跳,我不禁哈哈大笑,決定泡上他,他那么可愛又好玩,不管是遊樂園還是床上,我一定都會喜歡上他。不過後來我們去了三里屯北街的“JazzYa”喝酒,裡面充斥著日本人、韓國人和若干歐美帥哥。莊同很不自在地挑了一個角落坐下,問我:你經常來這裡?
我說:很少,是朋友介紹的。
JazzYa是鳳凰推崇的地方,她喜歡外國人多的地方,簡而言之,她喜歡歐洲帥哥,而我長年以來都希望能偶爾生出個混血娃娃,一時間就志同道合起來。
不過至今為止我倆皆未遂。
我們叫了兩紮啤酒,在我的斜對面坐了三個老外,有一個看上去很英俊,我瞪著他看了一會兒,等他隱隱發現並把視線也投向我時,我便感到有點厭煩,因為這樣下去他會向我走過來,自我介紹說他叫Jeff,我們碰碰杯開始搭訕把莊同完全甩在一邊,我們又因為語言的障礙而重新拾回莊同,然後大家互相忘記,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很厭煩,這樣的相遇很厭煩,就像沒人會愛聽這樣的故事一樣,主角都不願意這樣開場。此時一道黑影飛一般從我身邊掠過把這番調情之舉一分為二,我調過頭不去看那個可能叫作“Jeff”的男人,讓他的視線落空悻悻而回,結果我發現眼睜得溜圓的莊同,他望到我的身後,我回頭時也正好看見一隻匕首利落地插進一個男人的腰部。
人們都涌了過去,一波一波的,莊同很英勇地跳到傷者身邊叫道:報警報警,趕緊呀。手握匕首的年輕人正和兩個架住他的服務生扭打成團。我看到保全正要衝了過來。在人群中我握住了鋒刃,那隻手鬆開,刀無聲地落到地上。快跑啊。我說,便拉著他自一片擁擠中滑脫:快!
逃上計程車後我發現背包忘了帶出來,這時方才看到肇事者的模樣——秀氣的、恍惚遲疑的、驚魂未定的男孩,這樣的他居然能跟著我衝出圍困。司機問我:上哪兒?
勁松西口。我說。我轉頭問這個男孩:有錢沒?
他看我半天,開始在衣兜里摸索,最後把整個錢包都遞給了我。
我媽惺忪地替我開門,我讓他躲在樓梯口,等媽媽重新睡下後才又開門讓他進來,媽媽還在裡屋喊:你又要出去?
丟垃圾。我邊說邊從廚房拎出一包垃圾放在樓道邊,把門重重地帶上。
諾諾有半件啤酒放在客廳的桌子下面,他看見了問我:你很喜歡喝酒啊?
不是,不過可以給你喝一瓶。我幫他開了酒,一邊咀嚼著這些問題,像莊同問我酒吧,他問我的酒,我都沒法說是完全屬於我的一種樂趣提供給他們,在我的生活里永遠是他人介入的成分在匯集。是鳳凰帶著莊同入了酒吧,是諾諾請這個男孩喝了一瓶燕京啤酒,那么我呢,我在這個晚上,為這個人或那個人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你帶我來你家了啊,沒有人告訴你要這樣做是你自己拉我來的。男孩對我說:你蠻有個性的。
後來我意識到這是我自己告訴自己的話,這一切都是我的假想,莊同還是傻乎乎地坐在我跟前,徒勞地看著我那色迷迷的目光飄來飄去。我借用了適才和我擦身而過的男孩的五官,因為沒看清所以在想像中也顯得異常混亂,然而他也正在我背後喝著酒,渾身上下連匕首的影子都找不著,他和我認為他要殺的人一塊兒高聲談笑親密無間。我的潛意識和我開了場玩笑,好讓我在這樣無法施展個性的地方不會顯得無聊。
莊同問我:在幹嘛呢?
我說:看電影。
從這時起,對面這個男人便放棄了我,他發現我不只是一點點的瘋。
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在諾諾的屋裡讀到晚報。她有買報紙的習慣,每天從中搜尋一堆可以竊取的專題或信息,用到她的雜誌上去。我讀到晚報上的一則訊息——“三里屯酒吧街又出傷人案,十九歲男孩行刺同伴未遂”。
地點:“JazzYa”南側的三里屯小商品街。
看到這裡我就想一定是那個人,只有他,他可以一出門就趁黑行兇。嗐,我就知道,他看上去那么像要殺人的樣子。
我敲著報紙對諾諾說:昨天我去的酒吧後來出事了,有人殺人。
她在看另一個版,眼皮都不抬就說:太好了。
於是我決定獨享這個事件,在心中一個人竊喜,寂寞,竊喜,刺激,我又找到一段可以獨自過濾的方式,不依靠他人之手,不用聽他人之言。因為這件事是假的,在我看來的確是假的,但它和我有牽聯——那個男孩,或那件事——我甚至能清晰地告訴自己,有點什麼會因此而徹底被改變。可莫非連晚報的記者也做了個相同的夢?
現在我也不得不告訴你,有關我的一點點異常的地方。那便是我好奇怪的第六感,它雖然並不總是準確的,可出現的頻率之高,莫名程度之深真是教我束手無策。大部分時候我倒是希望自己能預見一些關於未來的我的模樣,可第六感從來不這么做,有時我的確就像在看一幕電影一樣看到很多實際並沒有發生的事。比如我曾經看到熱水壺被姐姐摔碎了,但其實這件事是在我看到的一周后才發生的。
煜送我小狗時我看到它死的樣子。
在外公尚健在的時候我看到他臨終前流淚的樣子。
可這些影響不了我什麼,我最想看的是我死的時候誰在我床邊。可事實上我只能從別人的事件中去發現自己的影子,在這種預見功能中我永遠是個旁觀者,在我出生的時候誰能想到我會有這樣一個完全不忠於自己的功能呢。想想心都碎了。
對於這樣所謂的特異功能,我真是恨透了。
同樣,三里屯事件的發生照舊是與我無關的,這回更離奇,出現了陌生人。
不過對於它,我不用告訴鳳凰,告訴Renee或諾諾,不用告訴我媽,天,告訴我媽,她一定是會見血就暈的。
我找北青報的一個朋友借了記者證,拔腿就到三里屯的派出所,但一個威猛警察拒絕了我,說要採訪的早採訪完了,你們報也登了,這點小破事有什麼可說的。
這事原來微不足道,人沒死,在北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身臨險境但還僥倖活著,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被趕了出來,看見馬路對面楊樹下站著一個女孩向這邊遙遙望來,這是個骨瘦如柴的女孩,披到腰節的長髮,身上啷啷地掛著一大堆時尚卻風塵的器具,雖然隔得很遠但還是可以看出她那冰涼的眼神,感到整個漠然的世界都裝在她的瞳孔里。我朝她走過去,她就對我扯嘴一笑,我問她:你是不是認識那個男孩?
你怎么知道?
我見過他一次,本來都忘了他長什麼樣子,不過剛才看到你,就完全想起來了。
她徹底笑了起來,說:真有意思。
然後她告訴我,她是他的姐姐,叫杜秋。
我脫口而出:他要殺的人是你男朋友嗎?
是啊,你想見他嗎?杜秋一點也不覺得驚訝,這事仿佛普天盡知,也許她不知道該為哪一方來傷神,也許一時間失去了兩頭至愛她的自由被騰了出來,她的人就是空蕩蕩的,身輕如燕,她也對我說:真的,這樣剩我安安靜靜的一個人,就好像到了世界盡頭一樣,挺好的。
她的神態使我覺得,似我今天這般輕微的出現都吵到了她,打擾了她。不過她說:沒事,我也正要去醫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