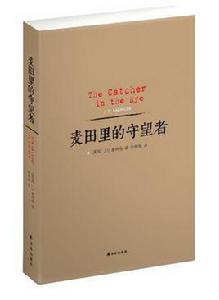內容簡介
 相關版本封面
相關版本封面該書的主人公霍爾頓是箇中學生,出生於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他雖只有16歲,但比常人高一頭,整日穿著風衣,戴著獵帽,游遊蕩盪,不願讀書。他對學校里的一切——老師、同學、功課、球賽等等,全都膩煩透了,曾是學校擊劍隊隊長,3次被學校開除。
又一個學期結束了,他又因5門功課中4門不及格被校方開除。他絲毫不感到難受。在和同房間的同學打了一架後,他深夜離開學校,回到紐約城,但他不敢貿然回家。當天深夜住進了一家小旅館。他在旅館裡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裝的男人,有相互噴水、噴酒的男女,他們尋歡作樂,忸怩作態,使霍爾頓感到噁心和驚訝。他無聊之極,便去夜總會廝混了一陣。回旅館時,心裡仍覺得十分煩悶,糊裡糊塗答應電梯工毛里斯,讓他叫來了一個妓女(十五塊錢到第二天,五塊錢一次)。 他一看到妓女又緊張害怕,給了妓女五塊錢打發她走了,可妓女要十塊錢。後來妓女找毛里斯來找事,毛里斯把霍爾頓打了一頓,拿走了他們要的另外五塊錢。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爾頓上街遊蕩,遇見兩個修女,捐了10塊錢。後來他和女友薩麗去看了場戲,又去溜冰。看到薩麗那假情假義的樣子,霍爾頓很不痛快,兩人吵了一場,分了手。接著霍爾頓獨自去看了場電影,又到酒吧里和一個老同學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進廁所,把頭伸進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陣,才清醒過來。可是走出酒吧後,被冷風一吹,他的頭髮都結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許會因此患肺炎死去,永遠見不著妹妹菲苾了,決定冒險回家和她訣別。
霍爾頓偷偷回到家裡,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苾,向她訴說了自己的苦悶和理想。他對妹妹說,他將來要當一名“麥田裡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裡做遊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幹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後來父母回來了,霍爾頓嚇得躲進壁櫥。等父母去臥室,他急忙溜出家門,到一個他尊敬的老師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發覺這個老師有可能是個同性戀者,於是只好偷偷逃出來,到車站候車室過夜。
霍爾頓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書了,決定去西部謀生,裝做一個又聾又啞的人,但他想在臨走前再見妹妹一面,於是托人給她帶去一張便條,約她到博物館的藝術館門邊見面。過了約定時間好一陣,菲苾終於來了,可是拖著一隻裝滿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後,因對妹妹勸說無效,霍爾頓只好放棄西部之行,帶她去動物園和公園玩了一陣。菲苾騎上旋轉木馬,高興起來。這時下起了大雨,霍爾頓淋著雨坐在長椅上,看菲苾一圈圈轉個不停,心裡快樂極了,險些大叫大嚷起來,霍爾頓決定不出走了。
回家後不久,霍爾頓就生了場大病,又被送到一家療養院裡。出院後將被送到哪所學校,是不是想好好用功學習?霍爾頓對這一切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創作背景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剛剛贏得了二戰的勝利,成為了一個政治、經濟和軍事大國。在這樣的時期,“紐約”就是美國實利主義社會的一個代表。它象徵著最“假模假式”的一切,人們的精神生活是一片荒原,沒有人在意別人的感受。
人物介紹
| 人名 | 簡介 |
| 霍爾頓 | 主人公 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想作一個麥田守望者,看護兒童;想離家出走,遠離塵囂,過田園般的純樸生活。但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理想卻被一一擊破。 |
| D.B. | 霍爾頓最喜歡的作者,霍爾頓的哥哥,也是他的朋友,去了好萊塢,霍爾頓認為他變得虛偽。 |
| 菲比 | 霍爾頓的妹妹,天真可愛,十分喜歡和依賴霍爾頓,喜歡當小大人。最後,改變了霍爾頓的主意。 |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麥》的故事情節時間跨度很小,對於社會現實的批判力度卻很大。異化是現代社會的重大問題,是現代社會中人類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現代哲學的重要概念。在現代工業文明及後工業文明里,技術擠壓著人的原始生活空間,提高了人的感官的自由係數,卻降低了人的精神的自由係數。人迷失了自我,泯滅了自我,向著“非人”的異化狀態淪落,而社會也向著物化的異化狀態跌落。異化問題的核心維度是價值的維度,人是目的、人是價值的尺度這樣的古典哲學命題受到了挑戰。然而,道德作為考量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標尺,關係著人學目的論中終極價值的內部結構與內部機制,也應該成為異化問題的重要操作性維度。
《麥》表現的社會是一個異化的社會,也是一個道德墮落的社會。在這種社會範圍內的整體性的墮落中,個體的墮落有可能在表層的墮落之下蘊含著深層的反墮落和道德的信息,有可能具有積極的內涵。霍爾頓以其自身的墮落揭示和反抗著異化社會中道德的墮落。在其墮落中可以窺見某種道德性,他所展示的是墮落行為里的道德,一種墮落的道德。
《麥》所表現的社會現實是商業社會的社會現實。在商業社會中,利益關係在社會意識中得到了空前的強調而實現了影響的最大化。由於利益關係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強調,思想關係與情感關係退居幕後,思想感情連結所需要的真誠淡漠了,往往可以促進個體利益的虛偽則大行其道。虛偽的作風愈演愈烈,成為商業社會人際關係的重要特徵。在麥田中奔跑的孩子隨時可能不慎跌落懸崖,這象徵著純真者時刻面臨社會性道德墮落的威脅,他們有可能陷於異化的道德泥潭中不能自拔,他們有可能受到當時物慾橫流的商業社會的腐蝕而迷失本真的自我,在道德異化的危機中走向身份的異化。而霍爾頓夢想著成為一名麥田裡的守望者,他要拯救那些處於危險之境的純真者,使他們免受精神的傷害,使他們永遠純真,使他們堅守道德的陣地,不受墮落之苦。在這裡,霍爾頓將自己定位為一位道德上的救世者,表達了他不滿於當時社會中道德的墮落。
藝術特色
這部小說的藝術魅力在於作者把重心放在對人物心理的深度剖析上,他以細膩而探析的筆法,細緻入微地刻畫了主人公霍爾頓的矛盾心態,描繪出霍爾頓複雜的精神病態。國內外分析霍爾頓精神病態的文章很多。德國學者漢斯·彭納特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著力剖析了霍爾頓的孤獨。他認為霍爾頓心中有兩個世界:——個是由阿克萊、斯特拉德萊塔以及妓女孫妮等人所代表的醜陋世界。另一個則是由弟弟艾里、妹妹菲比以及修女等人所代表的純潔、美好世界。霍爾頓因為發現後一種世界的日漸消失而感到孤獨。國內評論家羅世平認為霍爾頓在紐約遊蕩的三天中企圖消除他與同胞、社會之間的隔膜,試圖達到一種超越自我中心的境地。但事與願違,霍爾頓所去之處似乎都有一種無形的牆將他與別人隔離開,使他始終只能在社會的圍牆外遊蕩而不能與社會合為一體。羅世平寫到:“霍爾頓為克服隔離感而產生的痛苦,又試圖退化的知覺尚未產生的合一狀態,即人誕生前的狀態。他渴望能返回象徵自然、黑暗的子宮。然而,霍爾頓似乎只能在幻想中尋求這種退化性的合一狀態。他幻想當一個麥田裡的守望者。”
有關小說的結尾也是評論家爭論較多的部分。一些評論家們認為霍爾頓歷經矛盾、抗爭,最終回到社會。儘管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精神崩潰,但他最終認清了人生成長的歷程,適應了社會。評論家波爾曼指出:“霍爾頓知道事物將不再和從前一樣……,他知道他的周圍發生了雪崩似的變化。”在小說的最後一幕場景中,在中央公園裡,當霍爾頓看到菲比騎著木馬玩耍時,他的內心得到了安慰,我們也知道他長大了。”
而另外一些評論家則對小說的結尾持悲觀態度,他們認為故事在霍爾頓精神崩潰的悲哀中結束,因為霍爾頓無法解決他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所以只能以這種方式逃避。國內評論家方成在其文章“逃避·探親·反抗·絕望——論美國文學中兒童形象”中指出:“霍爾頓是自覺的逃避者,其反抗充滿著失望和無奈……。霍爾頓的結局是徹底的人生絕望,以致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
塞林格在這本書中採用了第一人稱限制視角,故事的講述只限於霍爾頓的心理活動或感覺範圍之內,而霍爾頓卻是一個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17歲的青少年,是一個對周圍世界沒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書中第一章,他面臨失學的危險,可他照樣觀看橄欖球比賽,甚至想到“我還是擊劍隊的領隊,真了不起”。其實,他這個領隊只是一個專管雜務的小跑腿兒,因不謹慎弄丟了比賽用的所有裝備,不但害得大家不能比賽,而且他自己也遭到眾人的白眼,他本應感到自責,但他的反應卻是“說起來,倒也挺好玩呢。”他離開學校在外遊蕩,沒有任何目標和方向,不知道自己想於什麼。
塞林格獨具匠心地以這樣一個人物作為說者,極大地否定了傳統形上學的美學觀念。傳統的美學觀念認為美是文藝作品固有的屬性,是人的審美體驗凝聚的表現形式。藝術作品作為美的形式的創造既包含藝術形象對現實的再現,也包含藝術家對現實的審美意向和審美評價。藝術生產的目的在於以升華了的審美體驗去陶冶靈魂,給人以純粹的審美享受。藝術作品應創造美的氛圍,美的形象,美的理想,使其具有感人的魅力、永恆的價值以及一種和諧、統一的整體形態。而塞林格筆下的霍爾頓卻與這樣的審美對象相去甚遠,他是一個患有輕微精神分裂的青少年,價值觀念尚未完全形成,理性世界一片混亂。
讀者通過霍爾頓的視線看世界,不自覺地被他的態度所牽引,正如華萊士·馬丁曾指出的:無論我們決定將敘述者所寫的東西如何分類,我們都依靠敘述者的肯定加以判斷,敘述者代表判斷事物的準則。在霍爾頓的眼中,成人的世界是虛偽、骯髒、“假模假式”的,他希望能做一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去保護孩子,不讓他們受到污染。在他看來,“人們就是不把真正的東西當東西看待。”這“真正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霍爾頓自己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覺得和妹妹聊聊天、懷念死去的弟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這對他來說是“真正的東西”。這一方面反映了霍爾頓害怕長大,討厭成人世界,希望保護比他更小的孩子,使他們不要受到成人世界的玷污;另一方面可見霍爾頓並沒有給讀者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在此布了一個未定點,留下了一個“空缺”以待讀者的填補,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人生體驗對這“真正的東西”作出自己的評判。這打破了過去那種和諧、有機、意義單一明晰的封閉的文本結構,文本不再是某種確定意義與價值的載體,需要讀者也參與到作品無限延續的遊戲中,充分調動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為文本設計一種意義,完成向“所指”的不斷趨近。
關於小說的主人公兼敘述者霍爾頓的語言,評論家們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有些意見還是針鋒相對、截然相反的。小說一面世就引來眾怒,一些評論家認為其語言“猥褻”、“瀆神”。但也不乏有人高度讚賞霍爾頓的語言,國外某些評論家把霍爾頓的語言與馬克·吐溫筆下人物哈克的語言相提並論,加以讚美。他們認為這兩個流浪少年的方言口語,會在文學天地里流芳百世、永放光彩。
作品影響
麥田裡的守望者從1951年出版以來給全世界無數彷徨的年輕人心靈的慰藉。小說一問世,霍爾頓這個對虛偽的周圍環境深惡痛絕的少年形象竟然被千萬讀者看成是迷人的新英雄,文中的崇尚自由的親切語言受到熱烈歡迎。並且這本小說反映了二戰後美國青少年矛盾混亂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處境。主人公霍爾頓那種沒有清楚目的的反抗,是當時學生和青少年的典型病症。《麥田裡的守望者》發表後,大中學學生爭相閱讀,家長和教師也視小說為“必讀教材”,把它當作理解當代青少年的鑰匙。
《麥田裡的守望者》領導了美國文學創作的新潮流,它使得思想貧乏、感情冷淡的五十年代的美國人為之傾倒,這個時期完全可以稱作超於文學定義的“塞林格時代”。本文剖析了小說主人公霍爾頓從憎惡虛偽、追求純真到最終屈從社會現實的心路歷程,揭示二戰後美國青少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內心世界。
這部小說最初得到二戰後那一代美國大學生的歡迎。然後,不管家長或圖書館長怎么看待這本書,大量的中學生也開始想搞到這部小說來讀——因為閱讀過它成了一些學校幫派的入門通行證。這種風氣儘管說起來已相當遙遠了,不過仍有人會回憶起來,《新共和》的作者John B. Judis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曾在關燈之後打著手電筒讀《麥田裡的守望者》”。這是一個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資格身份——關燈之後讀書並非意味著好學,而是代表對就寢制度的反叛;而且,塞林格本人就曾在軍事學校里冒著違反軍紀的危險,在被子裡打著手電筒寫作的。所以,“用手電筒讀《麥田裡的守望者》”也許就是塞林格的真正冬粉紀念他的最好辦法。
雖然塞林格寫這本小說的本意是只限於展現成人的虛偽與青少年的無辜與叛逆情懷。但憤世嫉俗的追隨者比革命導師更激進。1980年,馬克·大衛·查普曼在紐約殺害了“甲殼蟲”樂隊主唱約翰·列儂。他對外界說,他殺列儂的原因都寫在《麥田裡的守望者》里了。另一種傳說是,記者探監時曾聽到他喃喃自語:“我是麥田裡的守望者”。他認為他殺的並不是偶像列儂,而是雜誌封面人物。也許他認為,任何偶像都必須像塞林格那樣遠距離啟示大眾,頻頻出現在雜誌封面未免太庸俗了(像塞林格那樣登上一次《時代》封面也許是可以讓革命青年接受的)。幾個月後,約翰·大衛·欣克利向里根總統開槍,事後在他的旅館房間裡發現了一本《麥田裡的守望者》。記者再次將小說與謀殺聯繫起來,但後來總算有傳說表明殺手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影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睞。
出版信息
該書最初是1951年由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社出版的。
這部長篇的創作源於他的短篇小說《衝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衝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是他1941年投給《紐約客》雜誌的稿件。 《紐約客》的編輯當時就喜歡上這篇小說,但擔心這部作品會鼓勵青年學生逃課,所以壓了5年,直到1946年才正式發表。此後,塞林格在《紐約客》上發表了多個短篇小說,包括引起文學界關注的《香蕉魚的好日子》(1948)。從1949年開始,塞林格只在《紐約客》上發表作品。
《The Catcher in the Rye》(《麥田裡的守望者》)這部於1983年被引入中國,譯林出版社和灕江出版社均於該年出版了中譯本,譯者為施鹹榮,譯名為《麥田裡的守望者》。“Catcher”,原意是棒球隊的“捕手”,由於1983年時,棒球運動在中國內地不為大眾所熟悉,“Catcher”被譯作“守望者”。此後中國內地的絕大部分譯本均沿用了《麥田裡的守望者》一名,並因為“守望者”一詞的中文含義,經常在表達終極關懷的主題時被引用,產生了廣泛的衍生傳播。
作者簡介
 麥田裡的守望者(紀念版)
麥田裡的守望者(紀念版)塞林格全名傑羅姆·大衛·塞林格(1919/1/1——2010/1/27)享年91歲,1919年生於美國紐約城,父親是做乳酪和火腿進口生意的猶太商人,家境相當富裕。
塞林格十五歲的時候,被父母送到賓夕法尼亞州一個軍事學校里住讀,據說《麥田裡的守望者》中關於寄宿學校的描寫,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學校為背景的。1936年,塞林格在軍事學校畢業,取得了他畢生唯一的一張文憑。從1940年在《小說》雜誌上發表他的頭一個短篇小說起,到1951年出版他的長篇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止,在十餘年中他共發表了二十多個短篇,有些短篇還在《老爺》、《紐約人》等著名刊物上發表,使他在文學界有了一點點名氣。而《麥田裡的守望者》則使他一舉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