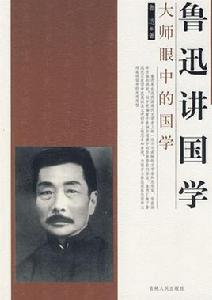內容簡介
魯迅先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在國學方面的研究,似乎更偏重於在獨自咀嚼中對自身存在的求證。《魯迅講國學》匯集了魯迅先生在國學發展以及文學創作上的思考和著述,為讀者立體展現這位國學大師在徘徊中的反思歷程。
媒體推薦
徘徊中反思的國學大師
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套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
——魯迅國學雜談
而中國人不大喜歡麻煩和煩悶,倘在小說里敘了人生底缺陷,便要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里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騙騙。——這實在是關於國民性底問題。
——魯迅國學史研究
作者簡介
魯迅(1881-1936),幼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學醫,後轉而從事文藝工作,曾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
圖書目錄
門外文談——魯迅國學雜談
中國語文的新生
關於新文字
論新文字
古書與白話
漢字和拉丁化
儒術
門外文談
一 開頭
二 字是什麼人造的?
三 字是怎么來的?
四 寫字就是畫畫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么?
六 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七 不識字的作家
八 怎么交代?
九 專化呢,普遍化呢?
十 不必恐慌
十一 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十二 煞尾
談金聖歎
小品文的危機
雜談小品文
摩羅詩力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學界的三魂
所謂“國學”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辯章學術——魯迅文學史研究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中國小說史略
題記
序言
第一篇 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
第二篇 神話與傳說
第三篇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
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說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
第七篇 《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傳奇文(下)
第十篇 唐之傳奇集及雜俎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
第十二篇 宋之話本
第十三篇 宋元之擬話本
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第十五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下)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說(上)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說(下)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說(上)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下)
第二十一篇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吸後來選本
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第二十三篇 清之諷刺小說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說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狹邪小說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譴責小說
後記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第一講 從神話到神仙傳
第二講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第三講 唐之傳奇文
第四講 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
第五講 明小說之兩大主潮
第六講 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
漢文學史綱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書》與《詩》
第三篇 老莊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第七篇 賈誼與晁錯
第八篇 藩國之文術
第九篇 武帝時文術之蠱
第十篇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序言
讀經與讀史(代序)
魯迅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麼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么,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裡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么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精彩書摘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么?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倖,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
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裡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關於新文字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與五筆字的快;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意字母和羅馬字拼法,更難以判斷行楷與楷書的韻味與意味,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便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很。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手搖,竟將古文的句子也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也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裝作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但橫平豎直撇捺交集也是難以臨摹。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並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以及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需有學者的氣息。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於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正在中國試驗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懂的。香港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民的;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拼,待將來再圖溝通。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將這當作一個大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他卻抹殺了方塊漢字本為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然而他們卻深知道新文字對於勞苦大眾有利,所以在瀰漫著白色恐怖的地方,這新文字是一定要摧殘的。現在連並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語的”大眾語“,也在受著苛酷的壓迫和摧殘。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並不識字,但特權階級卻還嫌他們太聰明了,正竭力地弄麻木他們的思索機關呢,例如用飛機擲下炸彈去,用機關槍送過子彈去,用刀斧將他們的頸子砍斷,就都是的。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只有羅馬字拼音。這拼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拼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蝀”之分,羅馬字拼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的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只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裡,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胡,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拼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藉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畫,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繫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里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繫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穫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而且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