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39年12月生於河北省蠡縣西滑村,1960年至1965年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曾受教於季羨林和金克木兩位大師的韓廷傑是一位知名梵文及佛學研究專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生活中的韓教授樸素溫和,70多 歲的人了,和他的老師一樣謙虛斯文,講唯識,講佛學因明,談起佛學問題,溫和如常,行坐飲食,都極有禮。
主要著作
1.《三論玄義校釋》,北京中華書局,台灣文津出版社;
2.《印度佛教史》,台灣文津出版社;
3.《唯識學概論》,台灣文津出版社;
4.《三論宗通論》,台灣文津出版社;
5.《中論譯註》,台灣佛光出版社;
6.《成唯識論譯註》,台灣佛光出版社;
7.《大史》(譯自巴利文),台灣佛光出版社;
8.《島史》(譯自巴利文)台灣慧炬出版社;
9.《新譯大乘起信論》,台灣三民書局;
10.《佛經知識寶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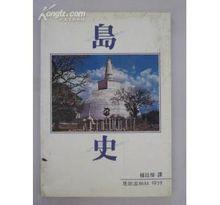 《導史》
《導史》11.《唯識宗簡史簡論》,上海佛學書局;
12.《妙法蓮華經譯註》,吉林聯合文藝出版社;
13.《驚夢記》(譯自梵文),中國戲劇出版社。
14.《成唯識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5.《南傳上座部佛教概論》,台灣文津出版社
16.《梵文佛典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在權威、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採訪問答
1960-65年
我於 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梵文和巴利文,當時的校長是陸平,他剛上任不久。他的前任是馬寅初校長,我剛進北大時,看到牆上貼著很多大字報,批判馬校長的“人口論”。馬校長認為:中國人太多了,應當控制人口增長,要搞計畫生育。這種觀點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毛主席說:馬寅初只看到人有張嘴,要吃飯;他沒看到人還有兩隻手,能幹活。周總理做馬寅初的思想工作,讓他承認錯誤,寫個檢討。沒想到馬校長很強硬,決不認錯,只好下課。於是調鐵道部付部長陸平接任北大校長。
在北大時
我在北大學習期間,感到北大的學術氣氛很濃,經常請國外知名學者來校做學術報告。學生學習很刻苦,每天背著書包在宿舍食堂圖書館教室四個地方來回跑。書包里除裝書以外,還裝著碗筷,當時,有個謎語:北大同學的書包。打一個人名。標準答案是:里(李)盛(承)碗(晚)。李承晚是當時南韓的總統。
談季羨林先生
認真負責
我在北大學習期間,教我們專業課的是季羨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兩位老師輪流上課,一年級時季先生講語法,金先生講例句。語法講完以後,開始選讀梵文名著。季先生講梵語文學名著,包括民間故事、小說、戲劇、詩歌等。金先生除講梵語文學史以外,還講印度古典哲學和文藝理論方面的名著。到五年級,金先生繼續講梵文課,季先生開講巴利文。因為巴利文和梵文類似,略微一講就懂了。
我們班十七個同學,專業課每天都有,可見兩位老師為我們這班學生付出很多心血。兩位老師講課風格很不一樣,季先生的梵文是從德國學來的,他講的語法經過德國人的整理加工,簡明扼要,條理很清楚。金先生的梵文是從印度學來的,所以,他講的課是走印度的傳統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詩歌,得意時還能像我國老先生唱古詩一樣,他能搖頭晃腦唱梵文詩歌。一個梵文問題,讓季先生講很簡單,讓金先生講可就複雜了。季先生五分鐘就能講清的問題,讓金先生講起碼要半個小時。
因為兩個人講課風格很不一樣,時常鬧點小矛盾,金先生說季先生的講課方式是“資本主義”的,季先生很不服氣,說:“我這資本主義總比封建主義好吧?”金先生在印度學習期間,印度的社會性質是封建主義。金先生是九三學社的宣傳部長,季先生是共產黨員。北大黨委統戰部得知二人的關係後,曾經勸告季先生:“金先生是我們的統戰對象,您應當和他搞好團結。”
季先生長期擔任東語系主任,他實際教的學生只有我們這個班。60年以前他沒講過課,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只是輔導研究生,梵文課由我的同學張保勝等去講。季先生給我們上課時,通常是在東語系後邊的平房,樓內教學室讓給外教使用,季先生長久以來患有皮炎,給我們講課時常用手在胳膊上抓癢。看了他的《病榻雜記》才知道他的皮炎已經發展為皮癌。
季先生授課認真負責,他把梵語文章發給我們,讓我們預習,上課時讓我們先講。如果我們講錯了,他給糾正,搞得我們很緊張。因為經過自己思考,印象很深。
生活簡樸
季先生生活儉樸,經常穿很舊的中山裝、布鞋,在這方面鬧出很多笑話。傳說有個學生帶著很多行李外出,見到季先生,以為他是老工人,很不客氣地說:“老頭兒,幫個忙兒,給我拎包兒。”季先生真的為他拎包兒,送他出校門。又傳說他去辦公樓參加校務會議,把門的人以為他是工人,不許進門。得知他是副校長後,才放他進去。吃飯也不講究,我在他家吃過飯,師母(已過世)給我一碗麵條,一個雞蛋。我的師母很慈祥,是個文盲。季先生這樣一個大學者,和一個文盲夫人白頭到老,應當成為當代青年男女的學習榜樣。
季先生最崇拜的前輩學者是陳寅恪和湯用彤,和我們聊天時經常讚美這兩位學者,過年過節時,他只看望湯用彤副校長,還把我們的作業本拿給湯先生看,湯先生讚美我們學得好。就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孩子的幼稚動作,使父母很開心。季先生在我們面前經常提到他的同學胡喬木和喬冠華,說:“我們同學當中,我是最沒出息的,胡喬木是中央領導,政治局委員。喬冠華是外交部副部長,出頭露面。”
畢業後,我們同學有的留在北大,有的分配到中國社科學院。“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的兩位老師都被“打倒”了。北大東語系又把我們叫回來,對兩位老師進行批鬥。主持會議的人說:“他們是殺人不見血的儈子手”,當我們上台發言念“最高指示”時,兩位老師都鞠躬認罪,像往常一樣,季先生穿著褪色的中山裝,金先生穿著很舊的對襟小褂,他們面黃肌瘦,深度駝背,很顯然,他們受了不少苦。我想他們肯定痛恨我們這些忘恩負義的不孝子孫。其實不然,文化大革命剛過,季先生把我們召集到一起,給我們講治學方法:當您要研究某個問題時,先要了解國內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現狀,確定自己的突破目標。還召集我們同學開會,交流國內外印度學研究信息。還為我翻譯的《驚夢記》寫序。師生之情,一言難盡。
籌辦南亞研究所
文化大革命後,季先生曾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看望他九十多歲的老師,把他翻譯的八冊《羅摩衍那》送給他的老師。他的老師沒有讚揚他,反而說他沒出息:“翻譯《羅摩衍那》有什麼了不起?會梵文的人只要下工夫都能翻譯出來。你是中國人,你應當研究吐火羅。你們中國保留大量吐火羅文資料,我們外國人想看都看不到。”回國後,季先生經常對人說,在老師面前挨罵比受表揚還親切。
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兩派對立情緒很重,季先生曾想離開北大,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建南亞研究所。北大領導獲悉後,堅決不同意,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挖北大的牆角,並於1978年提任季先生為副校長,北大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南亞所,由季先生等籌辦。他作好規劃後,要向社科院院長鬍喬木匯報。胡院長獲此訊息後,親自到季老師家。南亞所就在兩位老同學策劃下誕生了,季先生任所長。

